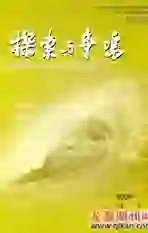新中国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典范
2009-07-22朱昭华
内容摘要中缅划界问题属于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1960年中缅两国签订边界条约,结束了长这半个多世纪中缅划界问题的争论。对于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我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从中缅边界纠纷发展的全过程来看,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两国在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新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对这片地区的领土要求,但这一让步是在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决断,它并不涉及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认可。
关键词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英国麦克马洪线
作者朱昭华,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江苏苏州:215009)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边界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除去边境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的客观环境外,中国周边小国居多,历史渊源悠久,许多地区存在跨境民族,近代西方殖民侵略所带来的边界矛盾与悬案,使得建国后中国边界划定的任务异常艰巨。中国边界问题得到解决的一个主要时期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中缅边界的划定首开其端,为这一时期中国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典范,使新中国获得了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
学术界在论及1960年中缅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解决争论多年的边界纠纷时,大都认为,中缅边界纠纷完全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1949年后中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不难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给予解决。另外,由于两国政府的政治远见,中缅双方对这一问题共同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力求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最终使中缅边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然而,这些理由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就中缅两国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来说,中缅两国获得独立后开始成为平等、友好的邻邦,但在边界问题上,两国仍从各自前政府那里继承了完全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缅甸独立后,把英国政府凭借强权获得的中缅边界领土视为其合法遗产,要求继续拥有。而中国政府则把这些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要求签订新约,做出修正。我们都知道,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交往中,起作用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而边界问题涉及的正是有关国家领土主权的最敏感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解决起来更加困难。其次,就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正确态度来说,不可否认,中缅双方以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态度解决边界争端是谈判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所谓“互谅互让”、“公平合理”毕竟都是些抽象的概念、原则。在缅甸政府看来,继承英国在中缅未定界地区的经营是合理的;而对中国来说,这些土地是英国通过武力割占的,缅甸继续占领是不合理的。要把这些抽象的原则真正落实到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并非一件易事。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重新探讨。
19世纪中叶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受到西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强烈冲击,琉球、越南、缅甸等中国藩属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中缅划界问题,属于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
从中缅两国边境历史的发展来看,中缅交界地区多为中央王朝力量难以到达的边疆土司地,享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两国国力的变化,边界土司常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时而臣服于中国,时而臣服于缅甸,或对中国、缅甸同修贡职。中缅之间也为争夺这些边境土司地爆发过战争,中缅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一条近代意义上的国界线,更多的时候,两国的边界界定只是一些点和面,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一条“线”。到明清之际,中缅之间的疆界大致稳定在了云南八关一带。
1886年英国侵占上缅甸后,中英通过1894年、1897年两个边界条约,划定了北纬25度35分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走向。1900年4月,中英两国完成实地勘界(镇边厅阿佤山区一小段由于条约文本内容的缺陷,双方当时没能划定,直至i941年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划定,称为“1941年线”)。尖高山以北地区,因地理知识的局限,条约仅规定“俟将来查明情形再作划分”。1905年中英两国曾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尖高山以北部分地区进行调查,随后双方提出各自的划界要求,分歧较大,尖高山以北的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便遗留了下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独立的缅甸联邦政府很快给予了承认,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双方关系进入友好发展的新时期。为了解决英国殖民主义遗留的中缅边界问题,避免边界冲突发生,两国领导人开始交换意见,最终在1960年1月签订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使迁延60多年的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通过中缅边界划定的结果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政府在北段未定界部分做了让步:自尖高山以北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划归中国外,基本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作为中缅边界界线。这意味着新中国政府放弃了清政府及国民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对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领土要求,使缅甸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
20世纪初以来,中英在尖高山以北中缅划界问题上,立场十分鲜明而坚定。英政府从印度帝国的战略安全出发,套用所谓的自然边界说观点,要求以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之分水岭高黎贡山为两国边界,因为根据勘查报告,此分水岭是一列非常显著的连绵山脉,分水岭两侧10公里区域内,都是浓密的森林,无人居住。虽然从自然地理条件上说,高黎贡山分水岭是一条很好的自然边界线,但这条界线与历史上形成的中缅边界传统习惯线并不相吻合,所以长期得不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清政府力争以高黎贡山以西的高良工山一扒拉大山一线为界,并以扒拉大山山脊北端为界线终点,从此往北的地方“划人华境固占优势”,否则亦应为瓯脱。清政府对中缅北段未定界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是把划界的得失与西藏、川边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早在薛福成任驻英公使与英国谈判划界时,就认为:“英人所注意经营者,欲由滇西野人山通入西藏”,现若划定,“万一受彼朦混分入藏地,将来彼必执约为据,关系非轻”。云贵总督锡良也密陈指出:“奴才在蜀,即闻滇缅界图波及西藏,卸乎有忧之,而犹幸其未详实也。莅任后,详细句稽,乃知外务部及前督臣丁振铎与英人相持不下者,诚追于无可如何。”锡良继而提出“不可许者七,可争者六”的意见,要求中央政府坚持力争。1909年继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曾致电四川总督赵尔巽表示:“案查滇缅界务,系属中英国界,英缅目的注重打通印缅穿插藏地,关系至巨,非仅滇边。”
后来的民国政府基本继承了这一立场,甚至出现一些更向西划的中缅边界线提案。如云南旅京同乡会推代表向国民政府呼吁应推翻前清政府的划界要求,另向西拟适合之线,将江心坡野人山地包括在内。193i年,外交部滇缅界务研究委员会的尹明德在对北段未定界地区进行勘察后,提出了更为靠西的巴特开山一线。
这样看起来,新中国政府确实是在中缅北段未定界地
区做出了清政府、民国政府都不愿做出的让步,但正如周恩来总理指出的,这个划界办法并不是割地求和,不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安排,也不影响我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而是中国政府基于历史和现实状况做出的合理决断。其实,国民政府那些不断往西划的分界线,无论对中国多么有利,都只是纸上谈兵,它不仅与中缅边界的现实状况脱节,也与历史上中国西南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不尽吻合。
从历史上看,中英之间长期争论的中缅北段未定界,主要包括了尖高山以北,西藏边界的担当力卡山以南,印度阿萨密以东和高黎贡山以西的地方。在1886年英国吞并上缅甸以前,这些地方主要是一些独立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在历史上有的部落未同中国发生过往来,有的则通过土司制度发生某些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就恩梅开江下游以东的小江流域来说,这里曾分别归属于保山县和腾越厅所属的土司管辖。由于土司制度的弊端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到清末,小江上游地区已不同程度,脱离了土司管辖,一些村寨只成为名义上的土司辖地,清政府官员也不加过问,俨然“视同化外”。小江流域以外的江心坡、户拱等地,明朝曾在这里设置里麻长官司进行治理,万历末年,里麻以西、孟养宣慰司辖境内的野人进入里麻,赶走当地的土司,到清朝没有恢复设置,原里麻长官司的辖地即不再属于中国。光绪年间受薛福成之托考察滇缅边界的姚文栋曾指出,野人山之北有瓯脱之地千七八百里,相传为明时茶山、里麻两土司之故地,野人居住其间,既未属华,亦不属缅。
至于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上游支流独龙江、狄子江、狄不勒江、脱落江地带,也主要是由一些独立的少数民族部落占据,在历史上曾为中国政权管辖的一部分,但到清王朝时,这些地区已成为了“瓯脱地”。清朝丽江府分驻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在其所作的,《怒俅边隘详情》中,叙述这片地区的状况是:狄子江流域的东西两岸地带的“狄子”民族“无人管束”,当时不属中国,也不属缅甸;再往西的狄不勒江流域,“人民一如狄子,向在化外,无人管束”,亦非中国或缅甸所有;狄不勒江西南的脱落江流域情况较为复杂,其地有自俅江流域即今云南贡山县境内迁来的独龙族,也有从木王地迁来的傣族,但就这片地方来说,仍然既不属中,也不属缅。
可见,从历史上看,中国对这片地区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并不充分。大金沙江、恩梅开江上游一些地区曾隶属过中国,但该地部落民族仍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时常摆脱中国管辖,尤其在清朝国势呈现衰退趋向后,丽江府的西部辖境范围由西向东发生了明显收缩,到光绪年间时,只达到今贡山、福贡、碧江三县边境地带。在中国周边邻国不能对这片地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清政府也无意积极经营,这些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逐渐成了姚文栋等所说的“瓯脱地”。模糊的国家疆界,羁縻式的行政管理都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概念发生了冲突,正好成为英政府指称“不能视之为中国领土”的依据。
从中缅边界的现实状况来看,民国初年,英政府中断边界问题交涉,趁着中国国内局势的混乱,将其边界要求付诸于实践,对北段争议地区进行了逐步占领与经营:1912年英军直达坎底;1913年占领片马;1914年在坎底设置葡萄府及厅治,辖区东达高黎贡山,北与察隅毗连,南接江心坡、密支那,西至枯门岭;1926年再行进占户拱、江心坡。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国通过多年的实际行动,已基本占据了整个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恩梅开江一萨尔温江分水岭事实上已成了中英两国在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而且经过多年经营,英政府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区扎下了根。据1947年11月30日碧江设治局函称,“滇缅北段虽未定界,然人民心理深倾向密支那态度,应请设法补救,以固边圉。”英人撤离之后,独立的缅甸政府继续接管治理,一切行政设施均与英人统治时代相同。这种单方面的武力占领,尽管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无疑会对以后的中缅边界谈判产生影响。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正是基于上述中缅边界的历史、现实状况,在听取了广大参与中缅边界调查研究人员的意见后,对中缅北段边界问题做出了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外,基本接受中缅两国实际控制线的重大决断。
对于这些“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国内一些人士最初也难以接受。因为尽管中国对尖高山以北某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并不充分,但缅甸的势力历史上更是从未到达过此,只是继承了英国的非法占领。周恩来总理在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时曾指出,中缅举行边界谈判是依据我国的国策,即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缓和;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新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缅划界问题时没有过于拘泥于领土的得失,除了受上述边境历史、现实状况的制约外,也有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缓和、稳定中国周边关系,以冲破美国对华战略包围的考虑。
从1955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并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将这一方针概括为“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确认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此,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建国初,中国与周边邻国大都没有签订正式界约,边境地方只大致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而且即使是条约划定过的边界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对于这些尚未划定或存在争议的边界,中国政府采取了保持现状、避免边界冲突的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应对国内残敌、朝鲜战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与经济禁运等紧张局势。中国周边国家,尽管都有各自的领土要求,但出于自身战略安全的考虑,也没有立刻提出进行边界谈判的要求,以等待时机成熟。由于国际形势的改变和边界线的模糊,1950年代中后期,中印、中缅的边界问题凸显出来。
1955年中缅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边界冲突,印度政府也开始宣称,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属于印度的版图。在1958年10月18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印度政府对阿克赛钦地区首次提出了正式领土要求,抗议中国修建穿越阿克赛钦高原的新疆一西藏公路,同时否认中印东段边界存有争议。1959年下半年,中印两国军队接连在中印东段与西段边界发生冲突。中国政府需要拿出对策尽快处理这些边界问题,以避免周边国际形势的恶化。
当时中缅两国关系较为友好,缅甸国家领导人采取承认中缅北段边界为未定界的态度,愿意通过协商、谈判的外交途径解决划界问题,也符合当时中国政府对边界领土争端所采取的政策:对过去条约划定的边界不要求改变,而以旧条约为基础进行互谅互让的必要调整,然后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这使中缅两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成为可能。
为了顺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中国政府放弃了争议最大的北段未定界地区,中缅边界划定的结果“与当时边界上两国国力不平衡的状态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宽宏大量
的。”1960年中缅双方达成的边界协定,表明中国对于周边邻国并不存在领土野心,中国政府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划定,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考虑边境现状的务实做法,也为后来的中外边界谈判乃至其他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提供了良好范例。以这样的谈判精神,中国政府相继又与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划定边界,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1960年中缅边界的划定也涉及到了当时存有争议的中印东段边界,因为根据条约附图的标示,中缅边界终点划到了底富山口,中缅边界最西北段的走向,即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中缅印交界的底富山口一段,刚好与历史上的“麦克马洪线”趋于一致。
“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政府为了印度所谓的战略安全,在中印东段边界私自划定的一条边界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分水岭的伊索拉希山口,将传统的中印东段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向北推移至了喜马拉雅山山顶。已有大量论著指出了这条“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因此它也从未得到中国历届政府的认可。事实上,至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直到1943年春,英印政府才利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机,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领土。1947年印度独立,英政府将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移交给了印度政府,为中印两国留下了至今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
中缅边界最西北段做出这样的划定,就牵涉到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西方一些学者推测这是中国政府向印度做出的一个妥协,希望以中印东段边界的让步,换取印度在中印西段边界承认中国的要求。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如上所述,中缅北段边界之所以如此划定,是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考虑,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一段的中缅边界线,虽然刚好与“麦克马洪线”一致,但它事实上也符合传统的中缅边界习惯线。这与英印通过欺诈和武力强行划出的中印东段“麦克马洪线”有着根本不同。所以,中缅北段边界的划定并不表明中国政府接受了“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仍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印边界的划定需要中印两国借鉴历史的经验,在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考虑边境现状的原则下,相互协商、相互妥协,以共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