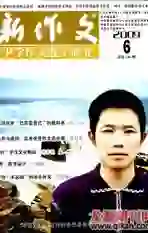灌满人家的油瓶
2009-07-16沈永生
沈永生
记得叔总叮嘱二堂姐:灌满人家的油瓶。
灌满?该灌多少是多少啊,为什么要多灌些,灌得满满的呢?能不像有些奸商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就不错了吧,还做赔本生意?可总没听叔正面解释过,多问的话叔也问你:“便宜得痛,多就多滴(多点)嗒,折么什(什么)?”
那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还有许多乡下人没用上电灯,点煤油照明。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也用煤油烧炉子(炭炉到现在的火锅的过渡品)。所以,一般人家就算再没事,也常上街打煤油。用打点滴的盐水瓶,后来也用啤酒瓶什么的,灌个三瓶五瓶。这原本不是什么贵重物资,也不紧俏,一街上下一个价,不赚钱不说,本钱还死大,又笨重又邋遢,想赚钱又爱干净的街市人还真懒得卖这破货。叔为什么一直坚持这样做傻事,死要强调灌满人家的油瓶呢?虽不吃几七几八的亏。而人家也没捡大不了的便宜呀,真是搞不懂。
一日,几位上街回来的老人,坐在路边树阴下纳凉,就曾闲聊遭:
“耶,看老瘪的油瓶呐。”真是一夫“耶”呼,乱者四应。
“一下(全部)灌满哆嗒。”
“是嘞。”
“高恁多!”有人上前比划。
“哪人家打的哝?”有人拦腰挖根脚。
“哪里哝,熟人家店里。”一向性缓的老瘪,今儿个被人羡慕更加自豪起来,却不直说,关子卖得人心揸肺掣。
“到底哪人家哝?”
“鬼老儿,讲嗒。”
“北街口,”老瘪实在催不过,瘪出三个字,瘪瘪的嘴巴掣了掣,又悠悠地咂吧一口烟,再浅浅一笑,“食品站的沈老儿。”
“哦……沈主任。”似乎全明白了。
“沈家。”
“都讲地道。”
“二日(下次)也去。”
不就是高一点吗?能多多少?瓶颈多细,多灌一点点水位就上到顶。但到顶就叫人看出多来,眼能见手能量的绝对优惠,心里就塌实,嘴里就念叨。原来这是一个形象工程。
人不会只打油吧,因油上门还怕不买其他货!薄利多销,生意做开了,就是油上吃苦受累些,甚至折点小本,还怕其他货上赚不回来!(也不包没有人心太狠,其他东西就狠宰一把,那就真要不得)不得不佩服叔,进退有道。
叔打小就背井离乡,到人生地不熟的当时的区上混学徒。毛泽东时代在区上很得领导赏识,做到区上食品站主任。可别小瞧这几乎够不上品的正宗芝麻官,当时任他选,他还不做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头呢,这个吃香。文革中多少人受冲击,而他一点没事,一直做到退休。退下来还帮二堂姐打理小店,八十多岁上因癌而逝。真有一套。
人生也需要经营,我们不妨先把一件事,一件小事,甚至明摆着自己吃亏的傻事做好,就像叔一直坚持做傻事,然后才有大事上手,才谈得上顺手。那些求财心切而精明过度、滴水不露、粒米不出锅沿的人,恐怕真的做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