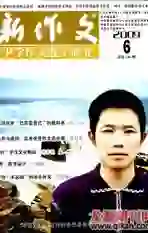高考作文三“垢”
2009-07-16孙文辉
孙文辉
谢有顺先生在自己的博客里无限感慨地说:“我已经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此言虽别有所指,却也在无意间触到了当前高考作文的某处痛点。不少专家一直对中学生只长于文学性写作而短于应用性写作的状况颇有微词,其实目前“文体不限”的作文考试导向不但没有增进作文的文学性,反而因应用性思维的杂糅削弱了文学性。大凡有高考阅卷经历的老师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感觉,高考作文看似文体自由,实则是一个大杂烩,议论、抒情破空而来,叙述、描写虚而化之,文学致力于表现的感官世界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垢。
一、理性之垢
孙绍振先生在对照了近几年法国、美国以理性思辨为考核重点的高考作文题之后,委婉地批评道:“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具有明显的抒情的、诗意的、审美的倾向,基本不涉及理性的抽象,即使蕴含着某种智性的内涵,也总是竭力以感性语言和生活现象为题干。”(《语文学习》2008年7~8期)且不论理性与感性在写作能力考查中孰优孰劣的问题,孙先生对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特征的把握是值得商榷的。
不妨以2008年湖南高考作文题为例: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意思是说,在滋润如酥的初春细雨中,春草发芽,远远望去,一片淡淡的绿色,可是走近后。却只见到极为稀疏的草芽,绿色反而感觉不到了。
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远离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与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
然后命题者要求考生根据阅读诗句所体会到的意境与哲理,联系现实生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孙先生认为这个作文题“把智性的思考隐含在感性的话语材料之中”,“回避直接以抽象观念来命题”,“降低了对考生抽象理性的挑战”。诚然,我国的高考作文题在理性的纯度上不及欧美,类似于人生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但这种不充分的理性思维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感性思维,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生机勃勃的感性世界。就上述材料而言,命题的大部分篇幅并非在提示意境,恰恰在阐释哲理。即使在描述意境时,一句“可是走近后,却只见到极为稀疏的草芽。绿色反而感觉不到了”,还是隐隐透露了若干理性元素。本来,韩愈的诗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新可人的感官世界,命题者却有意无意地把它降格为阐释意义的材料。于是题目所提供的议论文或记叙文的文体选择不知不觉沦为一种摆设,大部分考生只能在理性力量的挟持下去高淡阔论生活或事物的意义。
比如: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行七言,无尽意味。远看草色欣然,近看却是一片惘然。这不就是人生世事吗?跳出者欣然,纠缠者惘然。人生在世,应该讲点跳出的智慧。(2008年湖南高考优秀作文《跳出》)
又如:
清醒总附丽于距离,美感也就出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莲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启示我们不仅要跳出苦难,乐观地面对一切,更要超脱美好。感恩地面对你拥有的一切。春色迷人,走近它却害羞消失;海水蔚蓝,亲抚一泉,它只是纯净无色。(2008年湖南商考优秀作文《远近焦距》)
也许不少人还会以为,这样的文字不是很有文学味吗?殊不知文学是感而不是知,是言意思而不是言意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则沦为理了。目前的高考作文在文辞上似乎如诗如画,感性十足,但细寻其行文思路,恰恰是理性思维在横行霸道。无论是列叙人物、虚构故事,还是引用诗句、构设场景,许多考生的写作意图并不在于表现这些活生生的人、事、景、物本身,而在于借助它们去演绎作文话题所蕴含的哲理。面对丰富的表象,考生们只知道用头脑去思考,却忘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用舌头去舔,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可以说,在当前中国高考作文中盛行不衰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了一个怪物,它一方面不能像欧美高考作文题中的理性思维那样抽象、纯粹,以从事逻辑的思辨活动,另一方面却对作文中感官世界的表现构成了极大的干扰。
二、隐喻之垢
2008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触摸城市”或“感受乡村”)获得了不少好评,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命题有利于扼制这几年泛滥成灾的靠堆积历史人物或唐诗宋词敷衍成篇的写作恶习,激发学生的现有经验,引导他们关注现实,关心生活。命题设想固然不错,但我始终觉得高考作文没有真切感和现实感,不是因为写了历史不写现实,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写作活动中唯隐喻思维的盛行。当然,我所谓的隐喻,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它泛指写作活动中那些把陌生的东西变换成熟悉的术语进行传播的方式,既包括事物之间形象上的比拟,也包括事物与意义中的诠释。本来,语言利用隐喻使人们感知事物,但是过度的隐喻往往会使事物符号化,遮蔽事物自身的丰富性,甚至出现只见隐喻不见事物的怪现象。从当年的考场作文,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考生不敢或不屑用最基本、最直观的方式去触摸“城市”或感受“乡村”。
譬如:
都市无疑是美丽的。然而它却并不完美,透过灯红酒绿、华灯彩照的外表,我们也时常可以见到都市人浮躁而空虚的内心。快节奏的生活压弯了城市人的脊背,扭曲了城市人的心灵,人们习惯于将自己束缚在钢筋水泥的狭小空间里,抑或是沉湎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夜生活中。(2008年浙江高考优秀作文《触摸城市》)
“城市”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存在,有形状,有声音,有色彩,有味道,但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居然很难感受到这一切。城市固然具有诸如“灯红酒绿”、“浮躁而空虚”、“快节奏”、“纸醉金迷”等特征,然而这些词由于无数次的使用早已被高度固化,用它们来描写都市无异于为商品贴标签,特定观察者眼里的都市血肉及其细碎微妙的感受都被彻底格式化了。因此,我们要想真正触摸城市,首先必须跳出现成的城市隐喻,像孩子第一次看见城市那样去描述城市的表象。
比如:
“太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
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蓝色骑士派画家康定斯基说:“随便一个物件,都具有一种不从属于它的外表意义的内在音乐。如果在实用生活里压制它的物象的外表意义被排除开了的话,这内在音响将增强。”(《欧洲现代画派画论》)与“都市=灯红酒绿+浮躁空虚”的对应性表述相比,穆时英的文字较好地解除了附着于都市身上的僵硬的隐喻之垢,“灯红酒绿”的固化概念被化散为生动活泼、扑面而来的视觉感受,让人目眩神迷,心潮起伏,在城市隐喻之外为我们奏响了城市自身无比丰富的“内在音乐”。遗憾的是,不少阅卷老师对意义化、本质化的文字的兴趣大大超过了这样充分现象化的文字,由此造成的事物意义高于事物本身的等级观念,几乎成了我们日常写作教学活动的金科玉律。然而,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由隐喻积淀起来的事物意义系统是现成的,熟悉的,凝固的,进入它的世界远比触摸事物本身容易得多。而学生一旦用理性和记忆掌握了事物的意义系统,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相关文章。我们目前看到的貌似有思想,实则毫无创造性的考场作文,就是在这样的事物意义生产线上批量生产的。
三、虚泛之垢
有多年高考阅卷经验的老师说,读现在的高考作文,仿佛坐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眼边飞过许多东西,却无法捕捉到具体的一件;又像站在山巅看远处的风景,左看右看,总是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这个感受也是颇堪玩味的。2008年浙江省的一篇题为《感受乡村》的高考优秀作文用这样一些语句来结构全文:乡村中,总会矗立着那样一幢幢老屋/乡村中,总是有那么一个院子/乡村中,总会躺着那么一口古井/乡村中,总是有那么一两堵篱笆墙/乡村中,总是有那么一条小溪。然后在每一句后面作一些概念化的演绎。本来,老屋、院子、古井、篱笆墙和小溪完全可以构成一个非常物质化的乡村世界,让人可感可触。但作者并没有采用相应的参差不齐的叙述与描写,而是不恰当地运用重章叠句的叙述模式,把一个个独立自足、极富泥土气息的物件作了统一、规范的罗列,取消了物与物之间的特定感和差异感,使原本有根有须、具体实在的“这一个”乡村世界被连根拔起。
当然,高考作文中人、事、景、物的虚泛化不仅源于这种规范化的形式暴力,更来自考生对所表现对象的情感过滤与姿态悬离。试比较下列两段文字:
(甲)石库门的深处有叮咚的泉响,江南的小姑娘抱着琵琶哼唱不已。她的指尖像这门前的流水,灵动而不留痕迹,只留下几缕清音。这清音,究竟从哪里来?隔壁的老太太梳了光亮的发髻,提着篮子出来,一口吴侬软语:“张家姆妈,走啊,今朝端午买粽叶去喽!”于是,一个清秀而又和气的中年女子出来。笑着嗔怪:“大清早呢!”随即两人消失于石板街的尽头。她们往哪儿去了呢?(2008年江苏高考优秀作文《好奇心》)
(乙)奶奶八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还能眯着眼在屋里做针线。大她三岁的爷爷便不行了,不愿走动,总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相隔不过几米,奶奶过几分钟,便会放下活儿,“老头子!”奶奶这么叫。
爷爷不应,奶奶便急,迈着碎碎的步子到跟前。爷爷好好的呢,在藤椅上睡熟了。于是奶奶孩子般地笑嗔:“这个死老头子。人家喊了也不睬。”(2008年江苏高考优秀作文《好奇心》)
平心而论,十几岁的高中生能在考场上写出这样朴素、亲切的文字,实在不容易。但求全责备的话,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两段文字中发现值得深思的写作立场差异。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 of irrtmediacv)。”细细品味甲乙两段文字,似乎都给人一种温馨、悠扬的感觉,但两者的“临场感”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甲文的人物“小姑娘”“老太太”“中年女子”其实都是虚拟的符号,与作者的生命体验没有多大的关联,显然不及乙文的“爷爷”“奶奶”来得清晰、确定、真切。甲文创设的“小姑娘抱着琵琶哼唱”和“老太太与中年女子相约去买粽叶”两个情境,完全是从中国古典诗词的江南意境中过滤出来的,虚构的是彼时彼地彼人的生活幻想。乙文的情境虽然普通、琐细,却尺水微澜,在奶奶对爷爷单调而频繁的呼喊声中散发出此时此地此人的生活气息。从写作视角看,甲文是俯视的,犹如隔岸观火,有美的形式,却缺乏美的真切感;乙文则是平视的,表现对象已深深地烙上作者此时的生命体验,读“他们”也能读到作者本人的心灵世界。在中小学写作教学阶段,我们一贯提倡写此时此地的真人真事,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真人真事易于唤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文章即使绝少修饰也不大会产生人与世界的虚泛感。
行文至此,我不禁又想起了俄国形式主义论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自从中学写作教学“向内转”之后,我们似乎一直在观念世界打转,只注重无限制地开掘人的内心风景,却忘了时时刻刻环绕我们周身的无比丰富、无比生动的感官世界。在当前理性、隐喻、虚泛之垢陈陈相因的写作生态中,我们的作文教学大概已经到了用艺术的力量返回生活和世界本身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