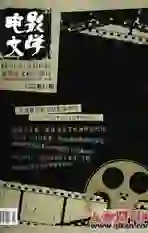逃离男性的樊篱
2009-07-14欧阳伟
欧阳伟
[摘要]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辛格在小说中所着力表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犹太妇女无知、虔诚与无奈的处境,她们试图逃离男性的樊篱,寻找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辛格,女性;樊篱
根据犹太教传统,妇女被排除在与神的直接联系之外,除了在特殊节日或亲人患重病的情况下,妇女不允许进犹太会堂,在传统犹太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犹太法典《塔木德》对犹太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地位就是这样规定和解说的:
上帝为什么偏偏要用肋骨造女性呢?犹太人的解释是这样的:上帝斟酌了一下该用男人的哪一部分创造女人。他说,我不能用头来造女人,以免她傲慢;不能用眼睛来造她,以免她过于好奇;不能用耳朵来造她,以免她偷听,不能用嘴巴来造她,以免她滔滔不绝;不能用心脏来造她,以免她太嫉妒,不能用手来造她,以免她占有欲过强;也不能用脚来造她,以免她四处闲逛;而应该用身体上隐藏的一部分造她,以便让她谦恭。
原来“上帝”在创造“女人”之时,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这是“上帝”的本意。因而,犹太女人生来便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能聆听、学习事物和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走出家庭和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她们惟一可学可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烧饭,打扫卫生、生儿育女。辛格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母亲或是女儿,妻子或是情妇、女仆或是妓女;亦无论其性格特征如何,善良淳朴或邪恶奸诈,逆来顺受或恣肆放纵,她们大多都是受害者和牺牲者。
一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是美国著名的犹太作家。他在作品中曾成功地塑造出一批性格多样,命运多舛的犹太女子,如莉切尔(satan in Coray,1955)、彦陶(Yentl the Yeshiva Boy,1962)、塔玛拉、玛莎,娅德玮伽(Enemies,A Love Story,1972)、旺达(The Slave,1973)、肖霞(shosha,1979)等。这些女性人物或固守犹太传统,忠贞坚定,深受犹太男主人公喜爱;或因遭受犹太宗教压抑,抑郁自杀身亡;或由于在二战中深受创伤,导致精神迷失,不知所终。在某种程度上,透过辛格在作品中对各式各样女性人物的刻画,一方面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犹太女性在犹太历史上长期以来所处的地位——即在对犹太男人精神成长、事业成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为了维系犹太社区的生存与稳定做出的自我牺牲;另一方面,通过小说文本对犹太女子的展示方式,也可以看出犹太宗教和传统文化对辛格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影响。
辛格是一位很会写故事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变迁。然而由于辛格经常把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事件编写进小说,故而也时常引起一些读者的误解,以为他所写下的“人”和“事”都是现实社会中所实有的,或至少代表了他的立场。譬如在处理女性人物的问题上,因为辛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半都处于压抑、封闭、抑郁的状态,所以一些女性读者便批评、谴责辛格患有“厌女症”(Misogynist),辛格对此表示难以接受。1978年秋天,在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理查德·伯金谈话时,他曾涉及这一话题。他说:
有些女人谴责我,说我恨女人,你知道,就像有些把所有非犹太人都看成反犹分子的犹太人一样,解放了的女人几乎怀疑所有的男人都是反女性主义者,她们想要作家把每一个女人都写成圣者和智者,而把每一个男人都写成野兽和剥削者。但是,当一件事情变成一种‘主义时,这件事情就已经是虚假的了,而且常常是荒唐的。
如果我们了解传统犹太宗教文化和辛格作品中所表现的时代场景,就会发现并不是辛格本人具有什么“厌女症”,他不过是通过其作品,艺术地反映和再现特定时期犹太宗教伦理和传统文化对女性持有的偏见、忽视以至歧视而已。同时,辛格对女性的矛盾态度,也暴露出他思想中传统保守的一面,即在对犹太女性(包括非犹太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和背离那些对女性的不公平看法。
辛格在小说中所着力表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犹太妇女无知、虔诚与无奈的处境,但是,这并不是辛格创作的终极目的,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描写,来揭露和批判某些犹太宗教极端分子歪曲教义、摧残女性的罪恶行径。
二
《卢布林的魔术师》被西方评论家认为是辛格最佳的长篇小说,其中主要的女性形象有埃斯特、马格达、泽佛特尔与艾米丽亚。
埃斯特作为男主人公雅夏的妻子,终日在家劳作,她怨恨丈夫每天不在自己身边,却又不背叛雅夏。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如小说中写到:“埃斯特不能生育,除了这件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她都是个好妻子。她会编结,会做结婚礼服,会烤姜什面包和果馅饼,会给小鸡治病,会给病人拔火罐和用水蛭吸血,甚至还会放血哪。”埃斯特最害怕跟丈夫分别,“节日过去了,雅夏套上大车,准备离家出发,他带上猴子,乌鸦和鹦鹉。埃斯特号啕大哭,眼皮都哭肿了。埃斯特偏头痛,左边胸脯上像是押着一块铁似的,埃斯特不喜欢喝酒,但是同他分手以后那最初的几天里,她总是喝几口樱桃白兰地提提精神。”
但是雅夏同别的丈夫不一样,不会一直待在她眼皮底下,他出门的日子比待在家的日子多,能遇到形形色色的女人,比吉普赛人更飘忽不定。雅夏在外面与三个女人同时有暧昧关系,但是埃斯特容忍他,埃斯特一边吃一边望着她的丈夫。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她干吗爱他呢?她知道他生活放荡。他并不吐露他知道的一切,只有上帝知道他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她一点也不怨他,人人骂他,同情她,但是她把他看得比哪一个都高,不管那个人有多么高的地位——哪怕是一个拉比。埃斯特是作家笔下理想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雅夏悔过自新,把自己关在一间只有一扇小窗户的小屋中忏悔自己的罪恶时,埃斯特依然守着他给他送饭。虽然小说中叙述埃斯特的篇幅不长,但是她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一个默默无声的、心甘情愿忍受丈夫不忠的女人。在犹太传统社会里,许多像埃斯特一样的女性,一直就这样默认自己的地位。她们习惯于男人对她们的支配,并且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命运,因此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心生怨尤。
马格达是《卢布林的魔术师》中被描写的最多的女性,她是雅夏事业上的间伴,同时也是雅夏的情人。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胸脯平坦,简直是皮包骨头。马格达继承了世世代代庄稼人的吃苦耐劳、百依百顺的习惯。对于马格达来说,雅夏就是她生命的全部,但她同样对雅夏在外面另有女人感到十分厌恶和痛苦。小说中有着这么一段对话:
“我肚子里藏着的事情可多哪。”
“她是要来,不划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她的男人撇下了她,她在挨饿,她去找个女佣人的活,或是当个厨娘。”
“你跟她睡觉?”
“没那回事。”
“你在华沙也有一个女人嘛。”
马格达用小心但含质问的口气来宣泄心中的不满。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马格达越来越不能忍受雅夏在爱情上的背叛,她变得暴躁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每一次雅夏从另一个情妇艾米丽亚那里回来,马格达总是异常愤怒,但是只通过自残来发泄愤怒。她开始出岔子,盆子从手里掉下来,烫伤自己的脚,扎烂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差一点把一只眼睛也弄瞎。她开始痛骂:“用打夯洗去你的罪孽重重,你这头猪,你这条狗,你的身子已经给浑身痂癣的公爵夫人淘空。”即便这样,她还是不由自主地为雅夏服务,为他洗澡、按摩。马格达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她会宣泄自己痛苦的情绪,但是她始终没法从失去男主人公爱情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失去了爱情,马格达的生命就毁掉了,最后她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折磨而上吊自杀,死得异常的孤苦和悲哀。
三
辛格没有让他笔下的女性获得自我言说(即话语权)的机会,作品中的女性都把男主人公视为生命的全部。他讲述了犹太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以及传统宗教文化对妇女的压制和扭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犹太社会的历史真实及作家的男权主义。她们没有发出充分表达内心需要的声音,作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女性着想,让女性鸣不平,小说中没有来自女性的、或是模拟女性而发出的声音。在想象女性和进行叙述时,辛格无形中暴露出男权主义思想。
泽佛特尔是雅夏的第二位情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小偷,被警察抓走后,泽佛特尔成了被抛弃了的女人,并因此受到歧视。小偷坐了牢,他们的妻子通常是规规矩矩的,但是泽佛特尔被人认为行为可疑。哪怕不是安息日的日子,她也插金戴翠,不裹头巾,还在安息日生火煮饭。泽佛特尔像一个庄稼姑娘依顺地主老爷那样依顺雅夏,时常流露出辛酸的微笑,即使是受了委屈还感到乐趣,几分麻木又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她不是那种爱妒忌的女人,虽然希望雅夏能常来陪她,但是从不勉强他,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她对雅夏说:“泽佛特尔,全是白搭——干吗要打哆嗦呢。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懂得不多,不过我肩膀上长着一个脑袋,我想的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听到风在烟囱里呼呼的打呼哨,我就非常忧伤,你不会相信我的话,雅夏,不过近来我甚至想到过自杀。”当她走投无路到华沙来找雅夏时,雅夏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把她交给人贩子赫尔曼,泽佛特尔的命运就如海面上飘浮的一根草,汹涌的海水不知会无情地把她送到哪一个角落。雅夏最后一次去看她时,泽佛特尔就如死人般面对着墙壁躺着,露出一个乳房,头发乱蓬蓬,好像被赫尔曼那庞大的身躯给压垮了。
艾米丽亚是小说中惟一一位没有委身于雅夏的女性,但是她也被欺骗了。她一直希望跟雅夏在教堂里结婚,在纯洁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夫妻生活,一直期待雅夏实现他的承诺——带着她和她的女儿海里娜到意大利去过平静的生活,但是雅夏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当她知道雅夏最终会一走了之、丢下一切不管时,“艾米丽亚双手蒙住了脸。雅夏看见她的脸相变了,不禁大吃一惊,短短几秒钟工夫,艾米丽亚变了样,眼睛下面出现了眼袋,活像一个从沉睡中刚醒过来的人,连她的头发都散乱了。”“她疲劳地微笑,这是人们在面临悲剧时候往往会流露出来的那种微笑。”
在小说中,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的过程中隐约会感受到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实际上物质的补偿并不能抚平马格达和埃斯特受伤的心灵,作家想象通过金钱来弥补给两位女性带来的伤害也不能把雅夏的罪恶一笔勾销。相反,这一想象表明在作家的思想中,女人可以被支配,被金钱支配,被男人支配!
作为一个资深的犹太作家,辛格良知未泯。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4让辛格笔下的人物都染上了受苦受难的色彩,而作为女性更是无法摆脱现实的和传统的两难境地。辛格在他的小说中对女性已有初步的同情,但还没有解决她们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辛格对女性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这暴露出他思想中传统保守的一面,即在对犹太女性(包括非犹太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背离其传统宗教和文化灌输给他的一些对女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