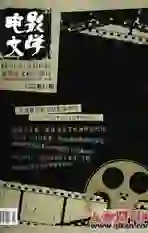奥康纳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分析
2009-07-14孙丽丽
孙丽丽
[摘要]奥康纳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从来都不是主角,他们飘忽不定、善恶难分似乎代表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同时,他们又总是将伤害带到女性人物的身上,将其肉体摧毁,甚至将她们推上死亡之旅。针对这一奇怪现象,本文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剖析奥康纳作品中男性角色的神秘含义后发现,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是作者的恋父情结在其对上帝的信仰中得以释放、升华的外在表现。
[关键词]男性;精神分析;信仰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一向以离奇怪诞著称。貌似平静的田园式生活之下常常涌动着一股危险的暗流,它会在瞬间将宁静的现实冲毁并带来肉体的伤害与死亡。这股暗流就是奥康纳作品中的男性角色。长期以来,作为作品有机组成部分的男性人物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他们一直被看做是女性人物的陪衬。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发现:奥康纳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及其遭遇完全是作者的恋父情结在其信仰中得以释放、升华的外在表现。
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在3岁左右开始把父亲看做性对象,把母亲看做竞争的对手。从而更加爱父亲,敌视母亲并与之争夺父亲的爱。成年后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憎恨母亲,希望独占父亲,代替母亲的地位。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恋父情结。恋父情结普遍地存在于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并且持续时间长,不易升华。弗洛伊德还认为,艺术家都是“白日梦”者。他们通过艺术的手法将自己的愿望与幻想堂而皇之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不会感到难为情,也不必害怕受到谴责。因此,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作家内心世界的反映。同时,他指出“情结”是受压抑的欲望曲折的表现形式。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奥康纳及其作品,那么其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带给读者的困惑就可以迎刃而解。
奥康纳的父亲对她一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毋庸置疑,奥康纳夫妇对独生女疼爱有加。但奥康纳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父亲的宠爱。他一有时间就陪伴在女儿身边而且常常将女儿的涂鸦和零散的诗歌揣在大衣口袋里,见到朋友就拿出来给人看。奥康纳两岁时,父亲还特意花钱在市电话号码簿上为她单独申请了一个电话。奥康纳独自享有这个专线直到6岁。与父亲相比,母亲的性格要更坚强,对奥康纳的要求与管束也更严格。尽管学校离家很近,奥康纳的母亲每天亲自接送女儿并且列出名单,从中选出可以和女儿玩的孩子。对“不受欢迎”的孩子,则断然将其拒之门外。弗洛伊德认为,女儿会自然地将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并渴望取代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以便独享父亲的爱。由此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对母亲的敌视。因此,强硬的母亲无形中成了奥康纳效仿和竞争的对象,对培养奥康纳的坚强性格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和蔼的父亲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奥康纳爱恋的对象。对父亲深深的爱继而转化为对他作为一家之长可以庇护依靠的信赖。
然而,奥康纳的父亲几乎从未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从她记事起,不断目睹的是父亲事业上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后来染上的绝症狼疮。事实上,从父亲生病开始直到以后母女俩相依为命的岁月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在承担着家庭的全部责任。紧接着她又经历了父亲健康的迅速衰退与突然病逝。更可怕的是,10年后奥康纳查出遗传了父亲的不治之症。为此,已经在写作上崭露头角的奥康纳被迫回到母亲经营的农场居住。恋父情结却没有因为父亲的死亡而终结。恰恰相反,奥康纳下意识地守护着对父亲的爱,排斥一切正常的男女社交活动。因此,“奥康纳虽以才女著称,却从不参加中学及后来大学的各种社交活动和舞会。她觉得自己在舞场上是个没有舞伴只坐着看的女子……”在潜意识中将父亲看作伴侣的奥康纳固执地持守着自己的感情而浑然不觉,她几乎没有与男性有过任何牵连,并且终生未嫁。
奥康纳对父亲的爱越深对他死亡的反应就越强烈。这种爱的渴望与缺失经过岁月的沉淀又转向其对立的一面:对父亲的痛恨。因为是他的死让奥康纳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剥夺了她的父爱。况且,奥康纳所承受的病痛以及死亡的威胁都来自父亲遗传的狼疮。奥康纳虽然闭口不谈父亲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但是她对父亲的恨却在其作品中以独特的形式发泄了出来。奥康纳塑造的男性人物可谓形形色色、善恶难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懦弱而且没有责任感。这正是奥康纳对父亲的感受。与母亲相比,父亲无论是在身体上、性格上还是事业上都是懦弱的。他不但不能保护家庭,他的死亡也是自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意味着奥康纳与母亲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在作品中,奥康纳将对父亲的感受幻化为各种男性形象。这些形象代表着父亲的各个方面:他幼稚而懦弱不能保护家庭;自负并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自私又冷漠不顾别人的感受;像暴徒一样残忍地将死的痛苦带给别人。奥康纳对父亲的复杂感情集中反映在丈夫与暴徒这两种人物形象的身上。
《启示》中的克劳德·特平的一举一动都听从妻子的安排。在候诊室当着众人的面,特平太太就大声命令丈夫去坐一把空闲的椅子。特平先生“果然坐下来,好像一向惯于听从她的指挥似的。”妻子与别人谈话时,特平先生像个应声虫似的不时地随声附和。特平太太的高谈阔论、引起一个丑姑娘的反感并被打翻在地时,特平先生呆若木鸡、束手无策。受伤后的特平太太“明白自己得跳起来去找他”,而此时的特平先生却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一般“抱着一条大腿,蜷缩在墙角的地上,脸色苍白如纸。”到家后,特平先生倒头就睡而在妻子推醒他并要求吻她时,他马上照办。但是特平先生的亲吻丝毫不带有安慰的成分,只是对妻子命令绝对服从的表现。从头至尾,特平先生始终对妻子言听计从。
《背井离乡的人》中的肖特利先生用假装吞下烟头的方式来取悦于妻子,而这样的示爱方式发生在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身上自然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肖特利太太忧心忡忡地与他商谈另一雇工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秘密酿酒场并报告农场主麦金太尔太太从而带给他们麻烦时,肖特利先生却在一旁假装死尸玩。在这关系着家庭前途与命运的谈话结束前,作为一家之主的肖特利先生竟然平静地睡着了。实际上,这种平静却是对家庭以及家人安危的漠不关心。随后,肖特利先生不但遵照妻子的决定在被解雇前离开农场而且在途中一再地询问妻子要到哪里去。由此看来,他对将来没作丝毫打算,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一切都由妻子一人规划、掌握。妻子去世后,肖特利先生变得更加无能。“有肖特利太太约束住他的时候,他本人始终就不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如今没有她,他更为迟钝,更容易忘事。”由此可见,肖特利先生只不过是其妻子的影子,失去了妻子的引导他也就失去了行动的方向。
奥康纳笔下的丈夫形象从来都不是家庭的核心。他们既然不愿意承担责任也就乐于听从妻子的安排。这正是奥康纳对其父亲的印象。但是,这种对父亲的贬低是从恨衍生出来的,而恨又是由爱转化来的。由于恋父情结的作用,奥康纳将父亲的懦弱与死亡归结为母亲强势的结果。因此,奥康纳对母亲的态度中始终暗含着一丝怨恨。其作品中母亲和妻子的形象是丑陋、愚蠢而又可悲的。她们辛
勤劳作却只能勉强支撑着家庭并常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启示》中的特平太太身躯庞大,有着两个乌黑的小眼睛与一身的肥肉,她被一个丑姑娘扔来的厚书打中额头并被掐住喉咙差点窒息;《背井离乡的人》中的肖特利太太是个有两条极粗的腿被黑人称为“大肚子”的女人,在路上中风而死;《好人难寻》中的祖母身材矮小干瘪,被暴徒连击三枪而死;《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梅太太是个有着一对浅灰色近视眼与一头乱蓬蓬的灰发的矮小女人,被公牛顶死;《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朱利安的母亲矮得像个侏儒却长着一双孩子般的蓝眼睛,被人打倒后中凤死亡。总之,在奥康纳的笔下找不到一个美丽的母亲形象,而且作品总是向着将这些女人引向死亡的方向发展。同时,奥康纳似乎在暗示她们所苦心经营的只不过是个畸形、残破的家庭,失去了父亲或丈夫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
奥康纳塑造的暴徒形象反映出其恋父情结在信仰中得到释放、升华的最终结果。弗洛伊德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一文中谈论到神经病时曾指出“对神经病的预防——宗教把这种预防赐予那些相信宗教的人——很容易得到解释:这种预防清除了他们的父母情结,个人的和整个人类的罪恶感都依赖于这个情结,又通过这情结去掉了罪恶感,而不信教的人则不得不自己来处理问题”。由此可见,信仰可以化解恋父情结,并使之升华。而“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学上说,就是一位崇高的父亲”。对从小笃信上帝的奥康纳来说,积累已久的对父亲的爱与恨很自然地转化为对上帝的体验。基督教认为,肉体是无益的,是必朽坏的,也是灵魂救赎之路上的障碍。所以,要借着苦难去除肉体的力量。因为“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从小生长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南方,奥康纳已经习惯于从其信仰的角度看待一切。她所经历的苦难在其信仰中转化为对上帝安排的欣然接受,她所爱慕的对象也从父亲转化为天父上帝。奥康纳的信仰使其恋父情结得以释放、升华。因此,在其作品中,暴徒摧毁人的家庭、夺去人的生命正如父亲使家庭残缺不全、使奥康纳身染绝症一样。但是伴随着暴力、死亡而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预示着永恒幸福的灵魂救赎与新生命的曙光。由此可以看出,恋父情结带给奥康纳的痛苦已经完全在其信仰中得到释放。在其患病的14年中,奥康纳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而且能够从乐观的角度看待苦难并将之视为上帝的恩惠。
《启示》中的特平太太遭受暴力后看到幻景,幡然醒悟。《背井离乡的人》《好人难寻》中的祖母被打死后,“半躺半坐在一摊鲜血里,像孩子那样盘着腿,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仰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这象征着“不合时宜的人”迫使祖母用流血的代价来效法被钉死的基督,以使其回到人类堕落前孩子般天真、纯洁的初始状态。《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梅太太被公牛顶死的一瞬间看见了亮得叫人无法忍受的亮光,回到了代表圣洁的光明之中得以与上帝融合。《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朱利安的母亲死前喃喃地呼唤着小时候照顾她的黑人保姆的名字并且要“回家”。这表示她已经恢复了小孩子需要依靠别人的卑微身份,可以返回人类失落的精神家园。
由此可见,在奥康纳的作品中作为父亲形象的男性在雄浑激越的交响乐般的暴力中,打破所谓的田园生活平静表面之下人们行尸走肉的麻木现状,将灵魂的救赎带给象征着母亲的女性。而奥康纳对父母亲的复杂情结也在此得以释放,并将其化解为对人类与上帝关系的关切。因此,可以说是信仰救了奥康纳,使她脱离恋父情结的束缚,并将它升华为对上帝的爱。同时,信仰使她摆脱了个人情结的纠缠,促使她以更宏大的视角审视人类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