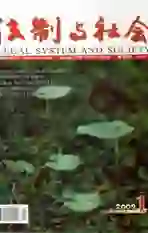从情理和无讼中追求和谐
2009-07-05娄晓玲
娄晓玲
摘要在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天理、国法、人情”是传统诉讼的价值选择,古人从“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的关系中更好地把握了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无讼”的诉讼理念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与“天理、国法、人情”相互交错,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讼”和传统诉讼中的情理因素的实质都是古人追求“和谐”理想在法律领域的反映。
关键词传统诉讼文化情理无讼和谐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028-02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说过:“如果没有一种对于过去的重新整合,既不能回溯我们过去的足迹,也不能找到未来的指导路线。”同样,在探讨我国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也不可能抛掉历史,摒弃传统,如何看待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纵观我国的传统诉讼文化历史,明显看到三条主线:“天理、国法、人情”一体的法价值观、无讼的诉讼理念及追求和谐的理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诉讼理念和运行机制。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传统诉讼文化进行解读。
一、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基石:天理、人情、国法
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天理、人情与国法的交缠互动格局。古代诉讼中,很难见到三者被分开使用的情形。从传统诉讼文化的角度看,天理一是指天道,或者说人与社会共同应该遵循的一些自然规律,二是指公理,即一些习惯、传统和公认的共同规则。人情则是指在诉讼中晓以人之常情,讲人性,重民情,看情节,某种情况下也有我们今天所讲贬义的人情涵义。国法,自不用讳言,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
我国传统法律诉求的理想模式是“天理、国法、人情”的三位一体。这也是传统诉讼中的判案依据,在中国古代,法官办案的时候往往援引礼义道德进行判案,这与今天只唯“法”的“法律至上”的法律理念有所不同。古人选择“天理、国法、人情”的法价值模式与古代和谐思想所蕴涵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一定关系。从实质上讲,古人从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的关系中更好地把握了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国法”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所体现的是形式正义;“天理”、“人情”以内心感受为尺度,所体现的是实质正义。在古人看来,实质正义更重要,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符合道德教化的天理、人情始终是最高的价值追求,而法律却处于次要地位。单靠法律是实现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因为法律作为人为的规范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与天理、人情相吻合,但法律不可能完全体现情理,可能出现法律禁止的,情理却予褒扬,情理反对的,法律却予保护的悖反现象。为克服这些矛盾,和谐思想支配着人们将法律和情理视为对立统一的“和合”体的最佳拍档,进而两者兼顾,既要体现形式正义,又要照顾实质正义,从而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当法律与情理相一致时,则“任法”以求,通过形式去展现实质;当法律不能囊括情理或与情理相冲突时,则舍法而“任情”,直取实质。”豍施政执法,都要做到“上应天理,下顺人情”。聪明的官员更是能将天理人情发挥到极致,显露出先人在判案中的独特智慧。用现在的话来讲,正是天理人情赋予了古代的官员在判案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了机械的照搬律条,以保持法适用的灵活性。古代的判官在诉讼中往往以父母官的身份给弱者以人性关爱,在判决中也融入人本因素来追求他们认为的实质正义,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古代统治者认为法官作为道德人,“以人类感情,对社会的广泛理解和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为基础,能够做出最佳决策”。豎在唐代,统治者主张“情法并立,互为轻重”的原则,即“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并重情法,以共同为治”。豏古代统治者一直在“国法、天理、人情”三者之间寻找契合点来建立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天理国法人情相互交织,贯穿着整个传统诉讼过程,成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基石。
二、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核心:无讼
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诉讼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诉讼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无讼观”,不管是在“天理、人情、国法”的互动格局中,还是统治者听讼过程中都弥漫着无讼的思想。至今,也在多多少少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无讼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
“无讼”一词发端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所谓“无讼”,即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但也并不是不让人去讼。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会有纠纷和争端,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秩序必要时是要出面解决问题的,即“听讼”,然而诉讼的终极目标或根本出发点却在于消灭争讼,追求和谐,所谓“礼为用,和为贵”,其隐含的观念基础在于,争诉是社会的一种恶和不道德行为,理应越少越好。如《周易·讼卦》就说:“讼,终凶”,因此“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无讼”的社会才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听讼”只不过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
从社会认识方面看,老百姓也是厌讼的,他们认为诉讼多为财为利而争,乃为君子所不齿,因此争讼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且讼起来对双方都不利。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其《劝谕榜》中这样写道:“劝谕士民乡党族姻所宜亲睦,或有小忿,宜启深思,更且委曲调和,未可容易论诉。盖得理亦须伤财废业,况无理不免坐罪遭刑,终必有凶,且当痛戒。”豐挖掘无讼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关键的还在于统治阶级对诉讼所持的态度,而且正是统治者积极对诉讼的劝讼、止讼、息讼的倾向使中国古代的“无讼”观念一直绵延至今。统治者认为诉讼的增多说明社会秩序不好,对管辖一方的官员来讲,诉讼增多则被看作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力图以此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即便是明代的清官海瑞,尽管因断案而出名并因此深受百姓拥戴,但内心深处仍洋溢着“化有讼为无讼”的理想,其在《兴革条例·吏属》中就写道:“各衙门日日听讼,迄不能止讼者何?失其本也。……今日风俗健讼,若圣贤当于其间,当必须止讼之方,而不徒听讼之为尚也。”
那么古人是如何实现“无讼”这一目的呢?其途径是通过道德教化,动之以情,晓之谕理,通过劝民息讼止讼,来建立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谐、乡邻相亲的和谐美好社会。“无讼”观的思想根基是“礼教”,当然包含了道德、天理、人情的价值追求。欲民无讼,先要教民,是遵行礼义,忍让谦和。因此古代官员往往秉承了无讼的理念,常常靠道德教化化有讼于无讼中,力图调和矛盾,消灭纷争。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清代康熙年间,陆陇其任某地知县,有兄弟二人因财产争讼状告县衙。这位陆知县开庭时根本不按正常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既“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也不作判决,“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豒。司法官之所以让兄弟二人依礼互唤对方称谓,意在唤醒二人固有的礼义廉耻,体会各自所负的道德义务,使其明白兄长应该爱护弟弟,而弟弟应当敬重兄长的道德伦理;至于争讼双方的是非曲直和财产分割,陆知县认为已经没必要去管,因为他们已自愿息诉,纷争自然会化与无形。所以有人说,古时法官办案的第一原则就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止。”豓古人认为,靠道德教化使“争讼化为无讼 ”更有利于维护秩序的和谐稳定。事实上,无讼还不是古代统治阶级的终极目的,它是古人在追求和谐的必然选择,无讼不过是和谐延伸到司法上的一个转借词而已。豔在今天看来,尽管无讼观念通常被认为与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容, 使得“法律的适用变成了教化加儆戒”,但是无讼观念之存在,反映了古人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古代社会人际关系中和谐观的真实反映。
无讼带给我们许多思考,一方面,无讼以扼杀个人的权利为代价换取统治者所认为的稳定和谐,用道德代替法律,使法律丧失了个性和权威。另一方面,无讼使人们通过道德教化和自我反省,改变自身想法,从根本上消除纷争,靠礼治去平复争端,靠教化去消除纠纷产生的萌芽,尽量使人民不起争端,从某种意义上尊重人的本性,相信每个人心中的善与良知。无讼的礼法互补、注重社会效果、解决纠纷的调解模式等值得借鉴。再者,无讼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不单单是意识层面上的问题,不能仅把它理解为一种思想意识,就像现在不能以老百姓打官司的频繁程度来衡量其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因此也就不能通过填鸭式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法律不是解决纠纷唯一的手段,也不是最好的手段,道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三、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终极目标:和谐
古人认为,人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其生存和发展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规律,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李约瑟先生说:“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中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
“自然和谐”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和依据,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对诉讼的观念。诉讼中的和谐源自天道和谐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就是无讼”。豖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把法律看成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但在古人看来,法律的作用不是要协调纠纷,而是要彻底消灭争端,建立一个无讼的理想和谐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无讼”观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天理、国法、人情”所包含的公平、正义、和谐与秩序得到尽可能的体现。古代诉讼中讲究和谐,在于天理、人情、国法俱在其中,是对律条的灵活运用,是基于礼和理对争讼者的息讼和劝导,化有讼为无讼中,使家庭,亲戚,邻里之间尽量保持和谐的关系。古代官员在诉讼中更担当了维护和谐的重要使命,他们要反复向两造说明“道理”,以此唤醒争讼者心中固有的“天道情理”观念,使其明白其破坏了自然秩序的和谐与平和。
在和谐理想的影响下,诸如守法与任情、告奸与容隐、平等与差序等种种看似对立的法律原则,不是被割裂开来对待,而是被放置在同一法律制度中进行调合,从而形成“天理、国法、人情”和谐一体的法文化传统。从诉讼的解决方式上看,调解和和解制度之所以成为古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更多地是基于追求和谐的目的。从古代一些诉讼制度和原则上看,如“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唐宋时期的务限制度,也是为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从诉讼目的来看,在诉讼中追求和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法律的作用,但就定分止争的终极意义上来说,则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法律的目标,维护了社会秩序总体上的稳定与和谐,而且避免了法律强制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破坏。诉讼中的情理因素和无讼观念,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追求都是寻求“和谐”。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今天,传统诉讼文化所蕴藏的和谐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传统诉讼中的“天理、人情、国法”和“无讼”观念相互交错,都围绕着“和谐”这个中心在诉讼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无讼是和谐理想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而“天理、人情、国法”却成为追求和谐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和情理因素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