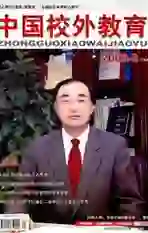内在的寻觅与外在的寻找
2009-06-17鞠赫男
鞠赫男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技术革命狂热兴起,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摄影、电话、留声机、电影等。电影的出现使文化的表现形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被重新诠释。电影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电影中。本文以2部中西方电影作比较,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浅谈一下电影是如何表现这种差异的。
[关键词] 电影 文化比较 文化差异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含义很广的词,包含的元素很多。当代对文化的分类大体有三种:农耕文化、航海文化、游牧文化。其中游牧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影响力逐渐衰退,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和西方的航海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技术革命狂热兴起,出现了时下相当流行的电影业。电影是文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方电影的不同主题和表现内容。西方电影注重对人的本性的探索以及对历史的反思,而中国电影多喜欢反映家庭伦理以及个人对集体的奉献。
二、《七宗罪》与《寻枪》之比较
《七宗罪》和《寻枪》都是罪案题材的影片,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下面我们对两部影片进行细节比较,从中看看相同题材的影片在反映不同文化时的细节和主题表现。
1.家庭的比较
美国影片《七宗罪》中对家庭的描写只是出现了由布拉德•皮特饰演的米尔斯警官的妻子,而对另一位由摩根•弗里曼饰演的沙曼塞警官根本没有家庭描写,这其中原因有二:(1)米尔斯的妻子是作为一个故事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存在的,她直接导致了七宗罪中最后一罪的发生;(2)沙曼塞的家庭对影片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影片不刻意安排另外一个家庭的出现;但是中国影片《寻枪》一开始就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由姜文饰演的马山的家庭—妻子和儿子,马山的家庭其实对影片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它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影片中。这就表现出西方历史理性主义文化和中国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理性主义文化的对立,其实这种对立是从古代就形成并衍传下来的。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起源,古希腊国家15%为岛屿,盛产橄榄但粮食匮乏,因此,航海成为他们进行商品贸易的重要手段。航海风险性很大,船员们需要的是有能力带领他们抵御风险的人当船长,而不是自己的亲属当船长,因此这种生产劳动协作的社会关系就逐渐打破了血缘宗亲的自然关系,人们之间不再是任人唯亲,而是以能力见长,慢慢地古希腊就形成了代表西方的航海文化。中国是东亚文化的发源地,地大物博,盛产各种农作物,可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因此,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人们之间的劳动协作关系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宗亲为中心的自然关系,家庭,亲属,父母,兄弟等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核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两种文化各自发展互不干扰,一直延续至今,而影片就忠实地反映出这种文化差异。
2.警察的比较
《寻枪》中的马山在发现自己的枪丢失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全,枪是警察的生命,警察丢枪其实是丢了社会的安定,丢了对人民的安全保障,这就塑造出中国警察为国家,为人民的形象;可是对个体人的内心却没有深刻的描写,人物仅仅只是浅层次的着急和担心,个人内心深层次的情感没有体现。《七宗罪》中塑造了两个警察形象,米尔斯和沙曼塞。米尔斯热情冲动,沙曼塞沉着冷静,这两个人其实代表着人性的两面—米尔斯代表人类意识中的情感,沙曼塞则代表了人类的理智,这种对人性的探索一直贯穿于整部影片的始终。在《七宗罪》中,当警察们找到了罪犯约翰并与之发生枪战,米尔斯被约翰打倒在地,当约翰用枪指着米尔斯的头时—与中国警察形象完全相反—米尔斯请求约翰不要杀他,这里就表现出西方不注重集体意义上的人,而更在乎个体体验与个体生存状态的联系,更关心个人的烦恼和焦虑。与之有着巨大反差的是,《寻枪》中马山为了引出罪犯,独自一人乔装成罪犯想要杀的人来到火车站,结果被罪犯打伤,但马山不畏罪犯的恐吓,最终找回了手枪并成功抓捕了罪犯。这突出了马山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和为国家为人民身先士卒的警察形象。另外一个表现警察的不同之处就是:《七宗罪》中,约翰完成了前六个谋杀后,前去自首,把最后一罪留给米尔斯自己;这到了故事的结尾也是最精彩的地方,在第七天下午七点,快递货车司机把约翰交给他的米尔斯妻子的头颅准时送到,约翰亲口告诉米尔斯他因为嫉妒而杀死了米尔斯的妻子和腹中的孩子,米尔斯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情感冲破理智,引发了愤怒,举枪打死了约翰。米尔斯的内心情感经历了从抓捕罪犯的得意到极度痛苦和折磨的过程;而《寻枪》中的马山内心是从担心着急到找到枪之后的喜悦和高兴,内心更深处则没有更多的描写,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注重集体意义上的人,不太关心个体的感受和情感发展过程,对人性的探究很少。
3.罪犯的比较
《七宗罪》中的罪犯约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他以传教的名义进行杀人,代表着人类本性中的“恶”。电影塑造的罪犯表面上是一个心理变态精神疯狂的人,但是影片却写出了约翰的理智,并没有俗套的将其刻画成精神分裂的人。影片中,约翰是故事发展的中轴,在结尾他自称犯了嫉妒罪而杀死了米尔斯的妻儿,其实是为了引发米尔斯的愤怒罪,结果他成功了,他以一种完成整个上帝赋予他使命的方式欣慰的离开人世。约翰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清扫人世间一切丑陋的人和事,影片并没有明确说出约翰是错的,也没有正邪之分,只是把上帝作为一个审判者和旁观者引入了故事。正如沙曼塞警官说:“如果我们抓住了约翰,而他本人是魔鬼或撒旦的话,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他不是魔鬼,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其实还是对人本性的探索。《寻枪》中的罪犯是一个卖酸辣粉的小商贩,他偷马山的枪是想杀死自己的仇人,罪犯直接目的就是报仇,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但影片中罪犯却杀死了另外一个无辜的人,这时主题出现了。罪犯给社会带来了危害,正与邪明确的显现出来,影片用罪犯的邪恶来反衬出马山正义的人民警察形象,这才是影片想真正表现的东西。
4.故事背景的比较
《七宗罪》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故事围绕天主教教义——七宗罪(懒惰、暴食、贪婪、淫欲、骄傲、嫉妒、愤怒)展开了一系列谋杀、追捕以及人物的内心挣扎和痛苦。故事中处处暗合了“7”——七罪、故事发生时间七天、七次下雨以及结局在第七天的下午七时,这其实表现了天主教关于“7”的含义:7是一个周期,7是宿命的罪与罚。而《寻枪》没有任何宗教色彩,描写的场面都是一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和秀美的自然风光,给观众一种美好恬静的视觉享受。这两种鲜明的对比其实也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前面我们提到的西方航海文化后来受到东方希伯来文化的侵入,希伯来文化中的犹太教在西方独立的发展起来,受到很多人的推崇,慢慢发展就逐渐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基督教”。这样西方文化就形成了航海文化加基督教文化的双轮马车;在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宗教传入,典型的就是印度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没有独自发展起来,却被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就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轮庄子哲学和佛教文化为两个扶手的独轮小车,所以说中国文化是没有宗教的文化。在我们的影片当中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什么宗教背景或者传递教义的故事情节。
5.故事主题的比较
《寻枪》并不探究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性格矛盾,也不探讨人类情感与理智的二维背反,把正义和邪恶,错与对分得相当清楚,用邪恶衬托正义,强烈地表现出个人为集体为国家舍生忘死的警察形象,而这个形象也就是整个警察形象的缩影。影片意在弘扬正义,舍己救人,多为他人着想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七宗罪》是想说明作为渺小的人类逃脱不了宿命的安排。在情感,理智,邪恶这三个层面,并没有哪个层面征服哪个层面,它们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人们希望时时刻刻保持理智,但情感会永远向反方向拉动理智,当理智控制不住情感时,就激发出人性本“恶”。影片不是树立警察正义无谓的形象,也不是描写杀戮和恐怖,而只是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表现人类面对现实的无奈以及面对宿命时的无可奈何;在影片中沙曼塞警官说道:“在这里,人们把冷漠当成一种美德。”影片通过沙曼塞之口想激发人们“轻功利,薄算计”的审美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道德价值缺失,希望人们多一份对历史的内疚和反思。
6.其他方面的比较
在这两部影片中还有一些细小的差异,但也能体现出文化的差异。《七宗罪》中警察上司和两位警察说话是一种商量和建议的口吻,如果两位警察不同意上司的观点可以直接驳斥;而《寻枪》中上司是一种怒斥和下命令的口吻,下属警察不能表现出任何不敬和反驳的神情。这就表现出西方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理念和中国对等级制度的在意和重视。《七宗罪》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米尔斯的妻子单独和沙曼塞谈话,但是却不告诉米尔斯,这也体现出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和个人感受。这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发生也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例如,《寻枪》中马山单独和一个女的见面就被妻子认为是搞婚外恋,对马山而言,没有个人空间也没有保留个人隐私的权力。这正恰恰体现了中国对家庭的重视,家庭成员之间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其实还是集体意义上的人要重于个体意义上的人。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个体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这是中国文化中亘古不变的人生信条。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两部电影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电影作为反映社会的工具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西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电影会如实地反映出这种差异。我们今后看影片时,应该多一份思考,多一份比较,多一份对影片深层的探讨,从而比较出中西方文化渊源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电影这样一个渠道加大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中西文化的互动,从而达到文化的融汇互通,相互理解,同时也能够避免很多误会和争端,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