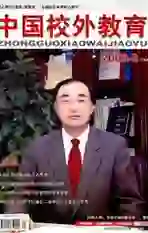“从中兴到末路”从阿Q的生存状况看阿Q形象的悲剧性塑造
2009-06-17方筱霞
方筱霞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先驱鲁迅的精神,激起了笔者对鲁迅先生认识的渴望,特别是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对愚弱国民灵魂的疗救苦心,更使笔者为之撼动。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阿Q正传》是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阿Q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关键词] 为人生 启蒙主义 精神胜利法
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先驱鲁迅的精神,激起了笔者对鲁迅先生认识的渴望,特别是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对愚弱国民灵魂的疗救苦心,更使笔者为之撼动。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阿Q正传》是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阿Q的生存状况是当时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写照,而阿Q的性格核心——精神胜利法,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统治积累的国民劣根性。阿Q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一、鲁迅塑造阿Q这类人物的思想渊源
鲁迅思想始终是把“为人生”作为第一要素。他的创作也始终围绕着这一人生命题进行实践,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始终在揭示当时下层民众精神世界的畸形和麻木。
1.鲁迅从事小说创作的起因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回顾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原因中写道:“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这段话中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鲁迅的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主义,那就是反对封建愚昧,唤醒民智。他的启蒙主义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处心积虑地推行的愚民政策。鲁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思想意识上还处于蒙昧状态,那就是“愚弱的国民”,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振兴的可能。
2.幻灯事件与弃医从文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生的幻灯事件使他弃医从文。这次事件使他认识到医治民众的精神要比医治民众的身体疾病要紧的多。他在《呐喊•自序》中写出了这次思想转变的经过:“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在课堂上常会看到有关战争的幻灯片:有一回竟在画片上忽然会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年轻的鲁迅。使他认识到“我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首推文艺。”
鲁迅小说中的启蒙思想非常突出,他想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阿Q正传》中的阿Q既是看客,又是示众材料,这不能不说与作者早年在异国的经历有关。
二、鲁迅笔下的阿Q
1.由阿Q的生存状况,反映阿Q精神胜利法的形成
小说序中说,阿Q无姓,无名,无籍贯,是给人做短工的流浪汉,所以,鲁迅从“小说家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
(1)阿Q的生存状况
第一,阿Q无姓,但可能姓赵。阿Q在赵太爷的儿子中秀才时说是赵太爷的本家,“比秀才长三辈。”结果挨了秀才的嘴巴,不许姓赵。第二,阿Q无名,不知道叫阿桂还是阿贵。所以用“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Q实际上就像当时中国人头上的小辫子,暗含讽刺。第三,阿Q没有籍贯。因为阿Q姓氏的不确定性,所以,籍贯就不可考证,“既多住未庄,也常住别处,所以,也“不能说是未庄人”。最后让作者“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因为‘阿字可以通用于任何人。
未庄社会的人们对阿Q,只是拿他开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阿Q没有家,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计。他很能干“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未庄社会的人们对于阿Q,也只是让他帮忙做工,其它的就再也记不起来了。
(2)阿Q的精神胜利法
①阿Q的“自尊”。阿Q无姓、无名、居无定所,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拉!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瞧不起未庄的人,甚至包括两位文童的爹——赵太爷和钱太爷。他会想“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阿Q也瞧不起城里人,因为城里人不用葱叶而用葱丝煎鱼;还把未庄的“长凳”叫“条凳”,这是可笑。但未庄人没有见过城里人煎鱼,所以也可笑。
阿Q觉得自己是“完人”,而阿Q式的“完人”实则是他意识狭隘,接触外界少,见识片面,产生出的一种狂妄自大和妄自尊大的必然结果。
②阿Q的癞疮疤。阿Q头上由于有癞疮疤,也就有了忌讳。又由于闲人的犯忌,阿Q就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可“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地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直至最后因为屡屡挨打,于是他又觉得自己癞得不平常,是一种高尚的标志。他想出了“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又心满意足了;于是在继续挨打,自己骂自己之后,他又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
③阿Q的“忘却”。阿Q的出名是由于挨了赵太爷的打才有了“面子”,阿Q没“面子”是由于没有王胡身上的虱子多,阿Q的不高兴是由于被“假洋鬼子”打,阿Q的痛苦是由于赌钱先赢后失,但“忘却”的法宝又起了作用,于是慢慢地他又高兴了。
所以,阿Q的“自尊”、“忌讳”是他不敢正视现实与自我的表现,阿Q的“忘却”更是他逃避现实的手段。
通过以上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深刻地揭示出早已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而又无人注意的东西,那就是精神胜利法。鲁迅曾在他的杂文《坟•论睁了眼看》中写道: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瞞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以光荣。”
2.由阿Q对女人的态度,看阿Q的“反抗”;由阿Q的恋爱,反映封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1)阿Q的“反抗”
阿Q在未庄社会里是弱者,比他更弱的,是妇女。妇女本是弱者,一旦做了尼姑失去家人的保护,那更是弱中之弱者。
阿Q把受了王胡的气,又挨了“假洋鬼子”的打,认定是碰见小尼姑得来的晦气。在众闲人的怂恿下阿Q对小尼姑极尽调戏之能使,气的小尼姑大骂“断子绝孙的啊Q!”
鲁迅在此后不无悲凉地写道:“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单单,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这也正是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所说的国人的劣根性: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了。”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由此可见,在小尼姑面前显着凶兽相的阿Q其实还是一个卑怯的人,整件事不过是一种欺软怕硬的过程罢了。
(2)阿Q的“恋爱”
阿Q在“假装正经”的小尼姑的引诱下,想到了不能“断子绝孙”。于是他想到了赵太爷家的吴妈。阿Q忘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竟然不正经地想和吴妈困觉,最终惹怒了未庄的圣贤赵太爷,阿Q的“恋爱”导致阿Q倾家荡产、断了生计。
从阿Q的恋爱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在阿Q身上和整个未庄人身上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刻骨入髓。阿Q本无文化却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男女有别,授受不清”。在传统观念中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发泄性欲的对象,阿Q对于吴妈的求爱也不过如此。而在未庄又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地方,赵太爷的话就是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必然全对,所以赵太爷可以讨小,阿Q只可以没老婆。
第二,阿Q对吴妈的求爱行动和其思想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在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禁锢下的人格分裂,在阿Q的思想里充满了封建正统观念,而在行为上却是一种赤裸裸的性的要求。作者在这里给予了相当的同情。
3.“从中兴到末路”,由阿Q的革命观,反映辛亥革命的悲剧性
(1)阿Q的“中兴”
“饥饿使人堕落”,由于恋爱事件,阿Q不能继续在未庄生存。连静修庵的老萝卜都吃不到的阿Q只好背景离乡进城谋生。
此后,阿Q走上了“中兴之路”——小偷小摸之路。无奈的是阿Q身上少有反抗的一面,所以连小偷也做不成的阿Q又回到了未庄。带着许多钱和旧衣物。又由于经济地位的暂时改变,阿Q暂时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当人们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偷儿时,又由于人们对于强盗的害怕,于是对他又“敬而远之”了。
上层社会的欺压,地保无赖的强行勒索,社会舆论的压迫,终于使得“真能做”的阿Q转入赤贫,继而沦为盗匪,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阿Q转入“大团圆”结局的开端。
(2)阿Q的“革命”
鲁迅曾经把阿Q的人格和精神素质及是否会参加革命这个问题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这样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恐怕并不是两个”。
在阿Q心中,开始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深恶而痛绝”。但是革命使得举人老爷害怕,所以继而“神往”,又因未庄众人的慌张神情,也使阿Q“快意”,于是阿Q就“革命”了。
阿Q的革命目的是:“元宝、洋钱、洋布衫!”……及“女人”。
阿Q革命的对象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再有就是王胡。”
阿Q的革命不外乎就是封建的改朝换代,他的革命充满了传统的封建观念,这样的革命使得鲁迅深感失望,革命并没有唤醒阿Q的灵魂——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沉睡的麻木的充满了封建积习的国人的灵魂。
就因为阿Q并不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识,在“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时,又有了另一种反应,即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要杀头。由此可见,阿Q的革命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机,他对革命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3)阿Q的悲剧
辛亥革命之时,社会极不稳定,以农民自发组织的抢劫时有发生,他们抢劫的对象一般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鲁迅笔下未庄的赵家也遭了抢。
阿Q从前做过小偷又喊过“造反了”,理应受到怀疑,睡梦中的阿Q被带进了县城的一所破衙门。
糊涂、麻木的农民阿Q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就被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封建势力送上了“大团圆”之路,老把总革命党主张要示众,主张要“惩一儆百”!阿Q成了老把总巩固自己新地位新权势的替罪羊。麻木的阿Q至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被砍头。
(4)辛亥革命的悲剧
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就是新政权换汤不换药,处于底层的百姓的生活和精神丝毫也没有改变,甚至成为巩固新政权的牺牲品。鲁迅不无悲哀地把自己的主人公送上“大团圆”之路。这是那个社会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更让鲁迅悲哀的是国民仍不觉醒,还在充当着戏剧的看客。鲁迅对于冷漠、愚昧、麻木不仁、浑浑噩噩度日的国人深感痛心,希望借阿Q之死刺他们一下,以激起民众的觉醒,“引起疗救的注意。”
三、由精神胜利法,分析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塑造
在小说中,鲁迅笔下的阿Q也不是生来就会精神胜利法的。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而逐渐生长出来的调整他心理平衡的特效药,但可悲的是阿Q有了这一剂良药以后再也不去愤怒、反抗,转而得意、知足,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严。
阿Q这样畸形人格的产生,既有当时所处生活环境的原因,也有所处时代的社会根源。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世界上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崛起,满清政府无力抵抗外敌,而对内又死要“面子”,只好不但自欺,欺人,且欺民,上至“真龙天子”,中至“文武百官”,下至“布衣百姓”,无一不是自欺欺人。而其后的辛亥革命又并没有真正唤醒民心,开启民智。可以说这种精神胜利法已经成了严重阻碍国家强盛,民族进步的社会通病。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悲剧又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悲剧。
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可悲又荒唐,在欺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不进行反抗,而是采取畸形的方式来麻醉自己,自欺且欺人,借此寻找逃路并求得精神上的自慰。他欺软怕硬,欺压比他更弱小者;他见识狭隘,而又妄自尊大;他满脑子封建正统观念,而又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他既麻木又愚昧而又充满奴性;他既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用虚幻的过去和未来来粉饰现实,最终无路可逃,走上了“大团圆”之路。阿Q式的胜利让我们谈来痛心,令人震颤。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出鲁迅想要改造国民性弱点的良苦用心。
参考文献:
[1]阿Q正传.
[2]陈漱渝.说不尽的阿Q——鲁迅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