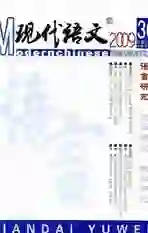吕叔湘主语观研析
2009-06-13施兵
施 兵
摘 要:从《中国文法要略》(1942)到《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吕叔湘多次论及主语问题,先后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话语功能、修辞特色等角度对主语进行了界定,并尝试了确定主语的一些操作原则,预见了主语隐现度等级序列的重要思想。除个别地方的表述外,吕叔湘对汉语主语有细致的观察、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吕叔湘对主语富有成效的探索是汉语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吕叔湘 主语 汉语语法
主语在英语里是subject,这个词源自拉丁语subjectus,本义是“投下”,引申义是“当下论说的事物”,在逻辑学中表示命题所判断的事物;在语言学中表示句子所断言的成分。传统上,在逻辑学和语言学里与subject对应的术语是predicat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praedicatus,意思是“宣称、断言、述谓”。据吕叔湘介绍(1979:565-6),最早将逻辑学subject和predicate这一对概念引进中国的是明末的李之藻,在他所译的《名理探》(1631)里subject被译为主,predicate被译为谓。在清末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1905)里,则分别被译为词主(括注“一曰句主”)和所谓,之后就被主词(辞)和宾词(辞)代替了。语法方面,清末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里则分别把其译为起词和语词,而严复在《英文汉诂》(1904)里则把其译为句主和谓语。到了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才分别用主格和宾辞,后者与逻辑用语一致,但仍然指的是谓语而不是后来的宾语。以后的语法著作如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和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4)用的都是主词和表词。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里把句子的两个主要成分分别命名为主语和述语,两个连带成分分别命名为宾语和补足语,附加成分命名为附加语。主语和宾语这两个术语被广泛接受,述语后来被严复的谓语取代。之后,诸多学者对主语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种种看法,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界所谓的主语难题(参见施兵2009)。本文综述吕叔湘对汉语主语的认识。
一、《中国文法要略》(1942)
吕叔湘(1942)将句子分成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和有无句四种。
“叙说事情的句子简单些称为叙事句,中心是一个动词,动作的起点称为‘起词,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像‘猫捉老鼠这类句子的格局是起词——动词——止词”(1942:28)。但是,“好些句子并不具备起、动、止这三个成分”:
(1)(甲)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了个大马猴。(同上:40)
(2)(乙)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同上)
“甲类动词后面的名词分明是起词,乙类分明是止词。所以甲类是‘处-动-起,乙类的词序是‘处-动-止。然而,我们感觉这两类句子是属于一个类型的。这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起词和止词以外另找一个观念来应用,这就是‘主语。我们可以说这两类句子的动词后成分对于动词虽有起词和止词的分别,对于句子则同为主语”。
由此可见,吕叔湘最先提出主语是为了应对起词和止词不足以精细描写句子的状况,这时主语似乎没有明确的内涵,也不与起词、止词冲突,相反还与它们共存。
“表态句记述事情的性质或状态,如‘天高,地厚;判断句解释事情的涵义或判辩事物的同异,如‘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它们通常不用动词,不适用‘起词‘止词这两个名称。这些句子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什么(如‘项脊轩‘天‘地),另一个‘什么或‘怎么样(如‘旧南阁子①‘高‘厚)。我们把前者称为‘主语,后者称为‘谓语”(同上:54)。
这里,主语有了新的定义,即表态句、判断句的主语“与谓语相对而且在它之前”、是“性质或状态的主体、被判断的对象”,这是同时从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的角度界定主语的。
有无句分两类:有起词的和没有起词的。无起词的有无句,如“岂有此理!”“有人于此”等。吕叔湘认为‘理‘人是句子的主语。有起词的有无句,如“一九三一年有一次大水灾”(时地性起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分母性起词),“我有一本书”(领属性起词),吕叔湘未明说哪个成分是主语。
吕叔湘(1942)对叙事句同时采用主语和起词、止词两套术语,表态句、判断句和有无句则使用主语,这对语言描写造成一定混乱。后来的著作,如吕叔湘(1953)、吕叔湘/朱德熙(1979)更正了这个说法。朱德熙(1985:41)评介说:“起词、止词是沿袭《马氏文通》的两个术语,这种说法对于分析汉语句法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所以《要略》以后没有人再这么讲,吕氏自己也早就放弃了这个说法”。
二、《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
吕叔湘(1946)详细分析了主语问题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印欧语言判别主语有五项标准:格变、语态、对立关系(指主语是陈述的对象)、位置(指主语位居谓语之前)、施受关系(指主语是施事)。但汉语的情况是:名词代词没有格变,动词没有语态,陈述的对象只是句空话,只剩下位置和施受关系两项标准,而这两项标准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吕叔湘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先依据施受关系和位置分出句子类型,然后再讨论各种可能的方法。
吕叔湘分出了四种句子类型、提出了确定主语的四种方案和一个关于方案的取舍标准。四种类型是:“甲V乙群”“甲乙V群”“甲V群”“V甲群”。四种方案是:“依施受关系”(将主语看成施事)、“依位置先后”(将主语看成谓词前唯一的实体词或谓词前多个实体词中的第一个)、“绝对主语主义”(认为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主语)和“相对主语主义”(一方面尽可能给每个汉语句子找个主语,另一方面也承认汉语里有无主句)。吕叔湘认为四种方案都有根据,都可以言之成理,但同时也各有自己的缺点。以绝对主语主义为例,其根据是将谓词与实体词的关系看成“系属关系”,分析谓词不再分析施受关系而是系属关系(1946:470)。如果一个具体行为系属于一个事物,该事物就是主语,“大狗叫、小狗跳”中的“大狗,小狗”就是主语;如果通常系属两个事物,只有一个事物出现,也不妨认它作主语,“下雨”“打钟”中的“雨”和“钟”是主语;至于有两个或三个重要实体词的句子,自然该把第一个当作主语,因为那是更“主脑的”位置,“他言也不答”“大树大皮裹”中的“他”和“大树”是主语。其缺点是,在“栽个跟头学个乖”中,“两个行为明明系属于一个人,把它们分别系属于后面的实体词就表示不出(这一点)”(同上:472)。因此,对于四种方案的优劣,吕叔湘说“并不想作什么肯定的论断”,只是提出一个取舍标准,那就是“必须简单、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点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同上:478)。
我们认为,《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时误解施受关系。吕叔湘认为“死马权当活马医”“酒要一口一口地吃”是受事主语句。其实,“死马”“酒”不是“医”“吃”的受事,而是“权当”(权且当作)和“要”(必须)广义的施事。
(二)有时误解句子结构。“只差三天就是整整两个月了”,吕叔湘将“三天”看成受事,认为谓词“差”之前原则上无施事,从而将该句认定为无主句。其实,该句构造是“主谓表”结构,“只差三天”是名词性谓词的非限定形式,担任主语,谓词不是“差”,而是“是”,“整整两个月”是表语。
(三)虽然区分及物谓词和不及物谓词,但没有从一个谓词所要求的必有成分来观察、分析语句,因此归纳出的句型有些是表面相似的不同语句。例如“大狗叫、小狗跳”和“先生讲,学生听”被吕叔湘先生认为是同一个句型,但谓词并不是同一类型,“叫”“跳”是非及物谓词,不能带宾语;而“讲”“听”首先是及物谓词,要求有宾语;只有当讲表示‘讲话、听表示‘听……讲话的意思时,由于‘话的意思隐含在谓词里面,这两个词才可以用作非及物谓词,不要求显性宾语。在“这篇课文,先生讲,学生听”里,“讲”和“听”都是及物谓词,而“叫”和“跳”无法进行这样的扩充。
三、《语法学习》(1953)
吕叔湘(1953:20)说:“‘我不认得他,这是一句话,‘我和‘不认得都是半截儿,可是这两个半截儿的性质不同。光说‘我,人家要问‘你怎么样,光说‘不认得他,人家要问‘谁不认得他。一句话,说明一件事情,上半截儿(谁?什么?)表明事情的主体,我们称它是主语;下半截儿(怎么样?)表明事情本身,我们称它是谓语。一般的句子都具备这两个部分。”
吕叔湘提出“主语是事情的主体”,这是从词汇语义的角度界定主语的;认为“主语是句子两部分中的一部分”则是二分法析句思想的产物,是从句法语义的角度看问题。
四、《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
吕叔湘(1979)再次坚持二分法析句思想,从句法语义的角度看问题,提出主语是与谓语相对的成分:“(在进行结构层次分析时),拿过来一个句子,先摘出两个词,说这是主语那是谓语,然后把这个那个连带成分,这个那个附加成分,一个一个加上去(1979:529)。”其实,这里的主语相当于某些研究者如刘月华(2001)提出的“主语部分”。
关于主语的性质,吕叔湘用“主题”“主题位置”“主脑位置”等术语来界定,这些都是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遗憾的是,某些术语的内涵缺乏深度挖掘。例如,“主语得像个主题……有些句子的‘主语就不像个主题,例如‘前天有人从太原来的‘前天”(1979:537-538)。“主语是最重要的成分,主语要位于句子最主脑的位置”上(1946:470)。从“主语的二重性”角度,吕叔湘提出主语是位居“主题位置”、谓词的两个支配成分中任何一个:“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不在一个平面上,不能相互对立和排斥,一个名词可以在入句之前作动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子的主语。在一定程度上,宾语和主语可以互相转化。例如“西昌通铁路了/铁路通西昌了;窗户已经糊了纸/纸已经糊了窗户”,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这种现象,汉语语法界称之为“主宾互换”。
吕叔湘预见了由于主语隐现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一个等级序列②:有主句>省主句>隐主句>假主句>无主句。其中,“省略是通例说出而此处不说出,隐藏是照例不说出”(1946:479)。“无主句指真正没有主语的句子,包括有字开头的句子(‘有没有人不同意‘还没有轮到你呢)和是字开头的句子(‘是谁告诉你的?)(1979:521),因为“主语得像个主题,那些‘望之不似的最好不承认它是主语。在没有主语的情况下,也许可以承认是一种‘假主语”(同上:538),“存现句有个假主语在头里”(同上:521)。吕叔湘未示例隐藏,但在谈到动词后续成分的差别时却暗示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答应另写一篇(后续动词,施事同于句子主语),‘他允许另写一篇(后续动词,施事异于句子主语),‘他同意另写一篇(后续动词,施事同于或异于句子主语)”(同上:548),这里的施事即隐藏的成分③。
吕叔湘讨论了宾语提前句、主谓谓语句的主语确定问题。“如果代表事物的‘宾语跑到原来的主语的前头,就得承认它是主语,原来的主语退居第二(这个句子变成主谓谓语句);不合乎这个条件的,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位置的变动不改变它的身份”(同上:539)。对于主谓谓语句,吕叔湘不同意动词前边的名词依次担任主语处理方法,以“这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为例,指出“这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依次担任主语,结果“大大扩大了主谓谓语句的范围,会不会把一些有用的分别弄模糊了?”(同上:545)吕叔湘提出主谓谓语句的确定标准:“只有不能用‘主—补—动句式来说明的才是主谓谓语句”(同上:545)。为了应对这个标准仍然无法处理的情况,吕叔湘还提出主语谓语句的两个特征:主谓谓语句的作用是说明性多于叙述性,主谓谓语句大主语后往往出现停顿(同上:546)。
最后,吕叔湘(同上:536)还对确定主语的施受标准和位置标准提出了批评,认为施受标准在分析具体句子时有时很难贯彻到底,位置标准则使得“主语”和“宾语”成了两个毫无意义的名称。
五、《语法修辞讲话》(1979)
吕叔湘、朱德熙(1979)主要从语言使用(修辞)的角度讨论了几个与主语使用有关的问题。
(一)由于说话人语言组织不当使得主语不在主语位置,例如“经过这个改变,带来了报纸的迅速而有生气的发展”(1979:131)应改为“这个改变带来了……”或“经过这个改变,报纸有了……”。
(二)主谓配合不当,例如“我国棉花的生产过去不能自给”(同上:132),主语应为“棉花”,“生产”与“自给”意义上不能配合。
(三)主语和动词之间有些别的词语,说话人忘了前面有了一个主语,又在后面再来一个,造成主语重复使用。例如,“郊区农民为了支援前线,他们天不亮就挑了粮食守候在区政府的门前,排着队抢缴公粮”(同上:134),“郊区农民”和“他们”就是重复使用。
(四)暗中更换主语,造成语言混乱,例如,“黄毛牛橘建议主任应该立即到医生那里去,但他被拒绝了,反而要他赶快去租滑竿”(同上:135),“他被拒绝了”应改为“主任拒绝了他的建议”。
吕叔湘、朱德熙(1979)并非从理论角度探索主语,更多地史从语言运用方面,对普及语言知识,提高人民群众语言运用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六、《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
吕叔湘(1980)对主语提出了如下看法:
(一)在某些情况下句子可以没有主语,如答问句“他收下没有?”“[他]收下了”祈使句“[咱们]走吧”表示任何人“活到老学到老”和自然现象“下雪了”等。这里,吕叔湘的表述不够严谨,因为《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曾严格区分主语的省略、隐含、缺失等几种情况,对照定义,答问句、祈使句的情况应该是主语省略,而并非没有主语。
(二)首次明确了小句谓语句(通称主谓谓语句)的几种类型。(a)小句的主语或宾语复指大句的主语,如“春生和小青,谁也没见过谁”;(b)大小主语有领属关系,如“你记性真坏”;(c)大主语前隐含“对于”“关于”“无论”等,如“无线电我是门外汉”;(d)大主语在意念上是谓语里的一个成分,如“这件事我没听说”(大主语担任宾语)、“这个消息知道的人还不多”(大主语担任主语的构词成分)、“这件事他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大主语担任宾语从句的主语)。
七、结语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吕叔湘对汉语主语有细致的观察、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只是,吕叔湘有时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提出看法,有时仅是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却未深入阐述,给人留下稍许遗憾。诚然,吕叔湘自己曾经说过:写作的目的主要是摆出问题,有时提几种看法,有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参考,同时促使读者进行观察和思考(1979:483)。尽管这样,我们依然认为,吕叔湘对主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是汉语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 释:
①原文是“南阁子”,疑为印刷错误。
②部分内容出现在吕叔湘(1946),出于比较的需要,本文将其放
在一起讨论。
③生成语言学称之为“空语类”(PRO)。
参考文献:
[1]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刘月华,潘文娱,故帏.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补本)[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3]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汉语语法论
文集(增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吕叔湘.语法学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6]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A].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8]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施兵.汉语的核心句型与主语:汉英对比的视角[D].北京:北京
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0]朱德熙. 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施兵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