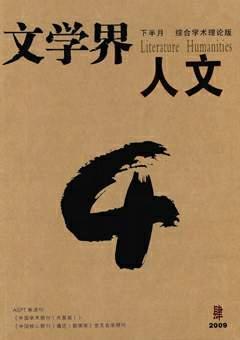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唯美
2009-06-02王玉宝
摘要:《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极端的女性主义的姿态。遮蔽了主人公颓废——唯美的生命态度。莎菲的“苦闷”及其对身体欲望的沉迷与启蒙叙事无关,而是与直面死亡的生命境遇相关。所以,它不是关于个性主义、也不是关于女性主义的叙事。而是关于个体生命感觉的自由伦理叙事。莎菲对感官美的沉湎,是其深陷颓废只能选择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她很快就顿悟了美的瞬间性和虚幻性,她真正需要的不是美,而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所以莎菲最终放弃了凌吉士。莎菲又是一种象征,她是经历了“五四”和大革命巨大社会动荡之后的知识女性“希望陨灭”、“意志瓦解”、精神绝望的象征。丁玲以莎菲与死神遭遇的人生困境,实施了这一象征。
关键词:莎菲女士的日记;生命虚无;唯美颓废;沉湎与执著;顿悟与拆解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4-001-05
作者:王玉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四川,绵阳,621000
唯美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其于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之后迅速波及到整个欧洲。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唯美主义对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生活及其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代表作《莎乐美》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一个显例,“对于五四文学作品而言,言说的主体以及他(她)借之得以言说的叙事模式,几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欧洲文学进行着对话。”丁玲早期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莎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问世之日,正是唯美主义在中国滥觞之时。在某种意义上,《莎菲》是对《莎乐美》的戏仿,也是对《莎乐美》的一种颠覆性的书写。虽然丁玲不是唯美主义者,但是《莎菲》却是具有鲜明唯美倾向的小说,它与唯美主义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
《莎菲》作于1927年,1928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当时五四文化高潮已经过去,“个性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文学开始关注社会革命。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强烈的个性主义的面目出现,与现实的思潮无关,却更像是五四的一个遥远的回声”。《莎菲》记述了莎菲女士的一段复杂而悖谬的情感历程。莎菲女士对于女性生命欲望的自我暴露。及其表现出的大胆叛逆精神,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但是,《莎菲》并不是关于启蒙叙事的文本,所以与“个性主义”没有本质的关联;莎菲也并非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者的艺术形象,而是中国社会文化启蒙之后,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带有极端唯美倾向的内心独自。小说向人们展示了莎菲深陷精神危机的苦闷之中,在死亡情结与身体欲望的风暴中挣扎、忏悔的心路历程。小说弥漫着一种浓郁的颓废、虚无的情绪。就小说的多种叙事元素来看,《莎菲》是道地的中国版的《莎乐美》。
《莎乐美》在中国的传播颇具戏剧性,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莎乐美的形象更多地是被当作反抗传统的启蒙者形象被接受的,他们更多地认同了莎乐美身上的叛逆性精神,从而对莎乐美这个文化符号的“所指”进行了巧妙的置换,使“莎乐美成为一个叛逆的形象,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传统的光辉艺术形象。”成为五四启蒙精神的象征。对于《莎菲》的接受,同样存在着这种错位的现象,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女性书写,都没有超越启蒙现代性语境的规定性。由于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启蒙现代性的产物来接受,所以遮蔽了小说文本唯美——颓废的价值取向。《莎菲》既不是关于启蒙的叙事,也不是关于女性的书写,而是关于个体生命感觉的自由伦理叙事。
一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观,但是首先是一种人生观和人生哲学。唯美和颓废是一体之两面,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同体共在的关系。所谓“颓废”是一种人生认识和生命感受,即认识到生命、人生乃至整个文明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耗竭,都在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和毁灭;所谓“唯美”是人在自觉到人生、历史、文明无可挽回的宿命之后,面对颓废人生所采取的一种苦中作乐的生命立场和人生态度。“如果说‘颓废意识是导发‘唯美立场的深层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唯美立场便是人们面对‘颓废人生而必趋的选择,而且是他们聊以自慰、聊以卒岁的唯一对策,舍此别无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颓废”是一种生命和文化的悲剧意识,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剧感,也就是生命的有限性和一次性的结果。万物皆流,一切都处于流逝之中,生命如沙漏,时时都在变化、刻刻都是消逝,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不断消逝的现在而已。关于生命的短暂,庄子有“白驹过隙”之感叹,雨果在《死囚之末日》中有更加使人焦虑的表述:我们都是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其实,生的开始,也就是死的开始,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走向生就是走向死”的哲学表述。既然颓废是人的不可抗拒的宿命,那么有情、有欲的人如何度过大限来临之前的一段颓废生命,如何面对存在的荒谬、生命的虚妄呢?唯美的价值观应运而生,这就是注重眼下、注重现在,注重刹那快感的唯美主义的人生哲学。这是一种重形式、重感官、重瞬间的“苦中作乐”的唯美人生观。
存在的荒诞、生命的虚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它首先是莎菲的问题。莎菲在小说中一出场,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等待执行的“罪人”,莎菲来北京是养病的,她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此刻的她不仅是被上帝判了死刑,而且是被医学判了死刑,也就是说,她的刑期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近在咫尺。《莎菲》记录了女大学生莎菲在北京养病几个月的心路历程,着重表现莎菲对生命、爱情、死亡等复杂而矛盾的生命体验。绝望与颓废是小说言说的起点,小说从一开始,莎菲即陷入了一种存在荒谬、人生虚无的迷惘与苦闷之中。她的生命已经笼罩在厚重的死亡阴影之中。对于生命的绝望和厌倦,使莎菲成为一个存在的询问者。内心的苦闷、愤懑和无聊是她的基本生存状态。“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喂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的法子。”(十二月二十四)她敏感、忧郁,常常“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她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一月三日)为了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独自从冷寂寂的公园里转来,我不知怎样的度过那些时间,我只想“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一月十六)
疾病的折磨,死神的召唤,使她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一种生的虚妄和死的恐惧。近在咫尺的死,使短暂的余生被悬置起来,生,还有意义吗?死亡如幽灵一样徘徊在整个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无论在白天、在夜晚,我都在梦想可以使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明明看到那吐出来的是比酒还红的血,但我的心却像有什么别的东西主宰一样,似乎这酒便可以在今晚致死我一样”。死亡是莎菲此刻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
“我的病却越来越深了。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么呢,什么也与我无益。难道我有所眷恋吗?一切又是多么的可笑,但死却不期然的会让我一想到便伤心。”(一月十五)
因了他们的沉默,因了他们脸上所显现出来的凄惨和暗淡,我似乎感到这便是我死的征兆。假使我便如此长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们也将是如此的沉默的围绕着我的尸体?他们看见我醒了,便都走拢来问我。这时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别!(一月十八)
死亡消解了生命的意义,对死亡的恐惧把生命推进了深渊。谁把我们无端的抛弃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忍受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莎菲的苦闷,莎菲的无聊,莎菲的厌倦都是由生命的虚无所催生的。相对于自然的永恒,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个体的生命是一种短暂的存在,莎菲也只有在此刻才能真正领会到生命的真谛;才会产生一种生命如朝露般的椎心之痛。在某种意义上,此刻莎菲拥有的生命,除了沙漏般的现在,就只有随时降临的死亡了。她的生存已经进入一种颓废——唯美的状态,带有浓重的虚无主义色彩。莎菲是颓废的,莎菲也是唯美的,一旦与美相遇,必然像莎乐美一样,采取唯美的人生姿态,一种推崇肉体、注重感官、视瞬间为永恒的生命价值观。
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使莎菲烦躁不安又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她说我不懂得我自己!如果不能接受必死的命运,就必须寻找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生命是需要意义来支撑的,在莎菲的意识深处,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和探求这个意义,她质疑生命、剖析自我。我还是我吗?我在等待什么?我在祈盼什么?她需要一种力量,一种永恒的力量,来抗拒死亡的威胁,慰藉走向死亡的生命,淡化乃至忘却死亡带来的痛苦。与凌吉士的偶然相遇,改变了莎菲因厌倦而萎缩的生命状态,凌吉士的惊人之美,点燃了她的生命欲望,唤醒了她的求生意识。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坠入爱河。这是她与凌吉士相遇后的生命存在的状态——颓废而唯美:既焦虑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虚无,又感受到生命不可抗拒的诱惑。她迷恋他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他的高贵,他的骑士风度:“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从来我是没有留心的。”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比如,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
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会也想到我在打量他,盘算他吗?后来我特意说我想请他替我补英文,云霖笑,他却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含含糊糊的问答,于是我向心里说,这还不是一个坏蛋呢,那样高大的一个男人还会红脸?因此我的狂热更炎炽了。
此刻,凌吉士的感官“美”就是一种意义,注入莎菲奄奄一息的生命,她怎能轻易放弃这如生命一般的意义?她爱得疯狂,爱得痛苦,“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的意义了。”即使在自己“认识到”凌吉士的“灵魂卑劣”之后,依然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因为这是她抗拒死亡、聊以自慰的唯一理由。这不仅仅是莎菲身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她生命意识的复活,是她人生最无趣、生命最虚无时的一个转机、一个所谓的希望。然而问题是凌吉士的美并没有使她彻底摆脱生命短暂、意义缺席的痛苦与恐惧感,而且使她陷入巨大的矛盾冲突中,她依然没有走出生命虚无的精神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加深重的虚无与痛苦之中。
“现代性尽管赋予了女性主体莎菲展现欲望的机遇,但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名叫凌吉士的男性形象抵消了这种欲望,而后者正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卓越代表”。“但是,我们说过,《莎菲》并不是纯粹的女性叙事,小说叙述的对凌吉士的放弃的理由,是一种道地的伪叙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莎菲选择放弃和退缩?真的如莎菲所说,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着如此一个卑劣灵魂?
其实,与凌吉士的相识,或者说凌吉士的“美”,并没有使莎菲摆脱心如死灰的精神危机,而仅仅使她的生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并陷入一种理性与情欲的巨大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莎菲认为凌吉士是一个“除了可鄙之浅薄的需要,别的一切都不知道”的“人类中最劣种的人”。但另一方面,只要“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我的心便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于是莎菲在灵与肉的搏斗中痛苦地挣扎着:“我既然认清他,我就应该这样说,教这个人类中最劣种的人儿滚开去。然而。…当他大胆地贸然伸开手臂来拥抱我时,我竟又忘了一切……我是完全被那一副好丰仪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紧些!多抱我一会儿吧,明早我便走了。”事过之后,莎菲又痛悔不已:“唉!我能用什么言语或心情来痛悔?他,凌吉士,这样一个可鄙的人,吻我了!”
使莎菲热恋并为之疯狂的凌吉士,灵魂如何卑劣?道德果真虚伪?只有撩开叙事者遮蔽在凌吉士脸上的面纱,才能真正揭开莎菲的情感之谜。《莎菲》的主要线索是莎菲对凌吉士由倾慕到失望、从相思到放弃的情感历程,她对凌吉士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才是小说文本的重心所在,要解开莎菲内心深处的隐秘情结也只能从凌吉士开始。凌吉士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莎菲来说,无论作为抗拒死亡、拯救生命的意义,还是作为放弃生命、走向虚无绝望,凌吉士都是唯一和直接的原因,所以对于凌吉士的认识和剖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谁是凌吉士?在中国文化符号的谱系中,凌“吉士”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能指。语出《诗经·召南》中的《野有死麇》:“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一首怀春的少女和年轻的猎人之间的充满性的暗示的爱情奏鸣曲。其中的“吉士?是一位年轻猎人,他体格健壮,容貌俊美,他大胆、粗犷,没有羞涩,没有萎缩,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在《诗经》的原文本中,对于怀春的女子,男人是主动者,也是诱惑者,他是一种征服与占有的象征。不论是远古的“吉士”,还是现代的“凌吉士”他们的“所指”作为一种性符号的暗示,并没有改变。
在男权话语的时代,男人是观看者,女人是被看者。但是在《莎菲》中,千年之前的吉士,摇身一变,成为被看者,成为被女人观看的对象,二者之间曾经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过来,《莎菲》中的吉士,完全被女性化了,作为叙事者的莎菲对凌吉士的观看与描述,采取了一种十足的男性化的视角,使用的是男权话语中男性对女性的称谓和表述:“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等等,“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莎菲用“嫩玫瑰”、“柔软”、“妩媚”等
特别女性化的词语来描述凌吉士,并且把称作“美人”。
“我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好像同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要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
这样疯狂的爱恋者,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恋人?这是一个谜,也是一个症候式的问题。在小说中,叙事者告诉我们,莎菲对凌吉士的失望与放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凌吉士为了金钱与人周旋、忙于应酬,追逐女人;二是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作为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凌吉士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比较深。他不只想赚钱,还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还想“留学哈佛,做外交官”。由此可见,凌吉士兴趣广泛、爱好多样,既务实上进又不乏洒脱精神。他和莎菲女士热恋时,亦彬彬有礼,不失绅士风度,并没有非份的举止行为,给人以尊重女性的印象。尽管作品对他缺少直接而具体的描写,但从莎菲带着浓郁的情感意绪的转述中,我们仍可触摸到一种成熟的现代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上的理性化,它预设了西方世界共认的现代人的模样。把凌吉士参与演讲会、网球比赛,想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当作资产阶级花花公子及钻营之徒的行为加以鄙弃(书中关于凌吉士性生活腐化的说法,近乎传闻和杜撰,而未见“事实”,故不予论列)。可见,莎菲并不信奉唯美主义的“瞬间即永恒”生命价值观,与莎乐美不同,莎乐美为了美奋不顾身,甚至以身赴死,她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美就是虚无生命的意义,而且是唯一的意义,必死的生命,只要拥有美就够了。莎乐美鄙视灵魂,但是,莎菲是渴望永生的,她希冀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不能永生,就从容等死。
还有当凌吉士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爱好、生活方式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莎菲,是其坦诚、率真的性格表现,但在莎菲眼里却成了道德的污点。之前的莎菲对凌吉士可是欣赏有加的,包括他的拘谨、天真、羞涩和诚实的品格,否则莎菲怎么能够故意说谎捉弄他。有人认为在二十年代中期,阶级话语、革命叙事已经成为一种话语资源,“20年代初——30年代中,中国知识分子将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予以拒斥。”《莎菲》的文本中隐藏着一种革命叙事的隐性结构,正是这种思想,使她在情感上拒斥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莎菲的一种托词,一种拆解唯美主义的托词,或者说是一种叙事策略。郁达夫曾经列举许多欧洲自传体写作实例论证道,第一人称叙述最适宜于完成“剖析自我”的任务。因此,这种叙述,不是可信赖的“事实”,而是叙事者有利于自己的一种伪叙事。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只是叙述者展示自己的某种欲望、情感心理的策略,而不是叙事情境中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像这篇小说文本,只不过是丁玲的一个白日梦一样。凌吉士的所有行为只是一种可能,是莎菲对于男性的一种不及物的欲望和想象(梦想)而已,且这种想象是为了服务于叙事者的叙事目的。所以我们透过凌吉士读出的只是莎菲的女性身体欲望的一次历险,第一人称赋予文本展示叙事者内心矛盾和困惑的便利。
三
凌吉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关于他的思想、性格、品质、行为,作品没有直接的描写,都是作为叙事者的莎菲叙述出来的。在这种特殊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中,叙事只对叙事者有利,因为她掌握着话语权,凌吉士无法辩解,莎菲也不给他辩解的机会。莎菲的叙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褊狭性。
其实莎菲失望、退缩当然有其至关重要的原因,莎菲说过,她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拒绝了卑琐的苇弟,也放弃了秀美的凌吉士:“你以为我希望的是‘家庭吗?我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不是家庭,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莎菲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社会启蒙理想的幻灭,以及时时袭来的“死”,都表明她需要的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使自己能够直面虚无的生命。凌吉士是作为一种填补生命虚无的价值而出现的,莎菲却拆解了“美”的虚幻,从而放弃了凌吉士。如果生命就是走向死亡,那么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凌吉士点燃了莎菲的生命之火,莎菲自己又熄灭了这意义之火,“吉士”的偶然出现,使莎菲萎缩的生命迎来瞬间的充盈和辉煌。但是,肉体欲望的满足仍然是一种浅层次的生命需要,与人对终极意义的需要不能同日而语,后者是生命的更高需要。认同“唯美”的人生观,获得的只是肉体瞬间的快感。这在一月十二日的莎菲日记中已经有所流露和显示:那天,莎菲拿着自己姐姐女儿的照片,为了捉弄凌吉士,谎称是自己的孩子,凌吉士信以为真。此时,日记写道: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诚实。这得意,似乎便能减少他的妩媚,他的英爽。要为什么当他显出那天真的诧愕时,我会忽略了他那眼睛,我会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则,这得意一定将冷淡下我的热情来。
当自己占据主动的位置,掌握话语权力时,当凌吉士表现出天真、稚拙和愚钝时,莎菲就会忽略他的眼睛,暂时忘却他的嘴唇,甚至减少他的妩媚和英爽。这是莎菲情感转变的一个契机,这一个瞬间顿悟,使莎菲与生命的“真相”相遇,从而识破了“唯美”的诡计,即美的有限性、瞬间性和变异性,它不是无限,也不是永恒,所以不能慰藉我生命的终极痛苦。作者在这里已经隐约暗示出她的根本的需要,以及对于美的失望和怀疑。美,作为人的一种感官的需要,在没有得到时充满渴望与期待,一旦得到时便会感到乏味和失望。当我感到我能够占有他、征服他时,他的魅力顿时消减,并且指向索然无味;当意识到他将成为我的俘虏时,我的热情已经冷却下来。这不仅是莎菲对凌吉士,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分析。这意味着,凌吉士的感官美在(莎菲心中的)变化,他的魅力在缩减、消解,同时意味着莎菲也不再有满足感,意味着凌吉士的眼睛、嘴唇及其所有的感官魅力,都在与时俱损。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凌吉士的错,凌吉士只是莎菲手中的一个玩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莎菲对感官美的追逐与沉湎,正是这种生命意识觉醒和重新建构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表征。不同的是莎菲因为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比其他人承担了更多的痛苦,陷入更加难以解脱的精神危机。死神的召唤,已经消解了存在的所有意义。“当人们意识到他的命如朝露,愈感到死的威胁,也愈尊重朝露般的一刹那。”因为死神已经逼近,所以莎菲比别人更加珍惜当前的“一刹那”。凌吉士的出现以及他的“美”,对她低迷生命的作用以及瞬间产生的美感,深深的撼动了她消沉、颓废的生命,因为在凌吉士出现之前,莎菲在精神上已经死了。与凌吉士的相遇,激活了莎菲生命中仅存的一点能量,使她的生命像一颗即将陨落的流星,在消逝的瞬间留下了一道令人目眩的璀璨光芒。她紧紧抓
住凌吉士的感官美,来拒斥生命的无意义,填补生命虚无,拒斥死亡的威胁。但是她深陷生命欲望中的挣扎以及最后的失望与放弃,是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对于走向死亡的生命,美的无用与无能,她感到“美”的易变与虚幻性,确切地说是“美”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变动不居的虚幻性。感官的美不是她要寻找的意义,并不能支撑自己濒临死亡的生命,甚至不能抵挡死亡时时袭来的恐惧感,她知道感官的美能够在刹那间照亮自己的生命,满足她瞬间的身体欲望,暂时忘却死亡的威胁。但是此时亢奋的生命也只能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回光返照而已,终究不能够取代至高无上的意义。所以即使在与凌吉士相遇的日子里,她一刻也没有摆脱死亡的威胁,而是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终结的惶恐,时时想到“死”。
一切是多么可笑,死却不期然的让我一想到便伤心。(一月十五)
我只想,“多么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一月十六)
我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艺,而灰心而又想到死;(三月十四夜)
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三月二十四)
假使我竟无声无息的死在那山上,谁是第一个发现我死尸的?我能担保我不会死在那里吗?也许别人会笑我担忧到这些小事,而我却真的哭过。(三月二十六)
我说:“不要乱想吧,说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三月二十八)
在某种意义上,美是事物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感觉,我们所谓的“美”,其实只是“美感”而已。莎菲觉察到自己美感的变异,认识到它的虚幻性,凌吉士的感官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失去了曾经的魅力。“美”对于生命之痛,仅仅是缓解一时的止痛剂,而不能改变人的终极命运。当她经过痛苦的挣扎,放弃了身体的欲望和感官的美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了。或许此刻她已经不惧怕死亡,在一个人不在场、神圣价值也不在场的文化中,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莎菲也只能“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陈庆桥曾以‘绝望的论述意欲来形容五四之后,写实主义在美学与意识形态上所面临的两难。这一‘绝望的论述通常突出深陷危机的‘新女性角色,体现‘(女性)希望之殒灭,论述意志之瓦解,还有个人对行动以及任何正面价值之怀疑一。”莎菲的经历和遭遇,真实地再现了五四之后的一代知识女性的虚无、绝望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莎菲是一种象征,她是经历了“五四”和大革命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的知识女性“希望陨灭”“意志瓦解”、精神绝望的象征。丁玲以莎菲的遭遇——死亡威胁、生命虚无和意义解构,实施了这一象征。莎菲的这种苦闷、无聊和厌倦生命的行为,正是当时一代知识女性共有的精神状态。对莎菲来说,造成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是启蒙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的普遍的幻灭情绪。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历经了五四时代的文化启蒙,却在大革命失败后颓废的社会情绪里陷入彷徨与迷茫,在女性的社会追求陷入混沌状态时,转而对自我生命意识的重新体认和感知。莎菲属于“五四”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等社会革命的大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她们从封建的旧家庭中出走,寻找启蒙现代性允诺的幸福和自由,然而她现在面对着启蒙世界却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启蒙的诺言成为谎言,曾经的坚信成为怀疑,希望成为虚妄,幸福成为迷茫,意义成为一种暧昧不明的混沌,生活成为直面死亡,在无边的痛苦中的煎熬与挣扎。自由解放的精神与无所期待的惶恐同时到来,但却找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依托。经过启蒙洗礼的莎菲女士,身陷生命虚无的绝望之中,她以极端的女性姿态、唯美的生命态度,抗拒死亡的威胁,最终却拆解了唯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颠覆了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认同了虚无主义的生命法则,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指认了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诡计和语言陷阱。
丁玲通过莎菲女士的心灵倾诉和生命絮语,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在一个终极意义缺席的文化中,个体生命面对人生荒诞、生命虚妄的困境时,无以慰藉的痛苦与忧伤。莎菲是唯美的,莎菲更是颓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个表达生命虚无、意义缺失的颓废——唯美——虚无的小说文本。小说对《莎乐美》的戏仿,表达了置身现代性语境之中女性内心的困惑与迷茫,并以一种彻底的生命虚无主义的立场,颠覆了唯美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