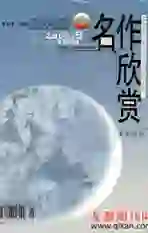从孔乙己话语看20世纪初汉语使用的分层与演进
2009-05-29崔晓飞
关键词:鲁迅 孔乙己 话语 双言制
摘 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理论出发,通过对鲁迅白话小说《孔乙己》语言运用的话语分析,剖析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分层语体现象以及向“标准语—方言”逐渐过渡的趋势。
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这是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用白话创作的又一篇杰作。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小说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意义方面,也就是孙伏园所讲的“《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①。在小说的语言运用方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各自的解构与阐释,如:冯明毅用《孔乙己》来佐证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是质朴精炼、不用华丽的词藻和冗长的描写②;刘玉凯是从“语言场”理论出发来论述丁举人、孔乙己以及短衣帮们背后隐含的名分与秩序③;而贺明华则从社会学的公共领域协调理论出发探询孔乙己与众人无法沟通的原因、进而思考当时作为“历史中间物”之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与话语权问题④。对此,蓝棣之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者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者没有明确觉察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觉察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而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考察、探索那些作家不明确但又确实左右他创作的那些心理过程,探寻他虚构人物的潜在动因,以及他的作品与读者的无意识联系。总之,考察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把作家没有明确察觉的东西阐发出来”⑤。本文就希望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演变理论出发,通过对孔乙己话语的重新回顾与分析,探寻潜藏在作品里的另一个“深意”,即作品人物话语所表现并记录下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语言演变进程。
初读起来,孔乙己尚未出场,小说便对其话语做了总结性的介绍:“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然而,作品中的孔乙己说话真的就叫人半懂不懂吗?让我们再来重新审读原文。文章中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一共出现过四次,每次都与人作了简短的对话,第一次是向喝酒的“短衣帮们”申辩窃书不能算偷。“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第二次是与温酒的小伙计之间的对话。“你读过书吗?”“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不能写吧?……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第三次的对话是对贪吃的小孩子说的。“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第四次是与酒店掌柜的对话。“温一碗酒。”“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不要取笑!”“跌断,跌、跌……”
从孔乙己这些简短的话语里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总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尽管他选择了说“污人清白”而不说“冤枉好人”,尽管他宁可承认文言的“窃”,而绝不认可白话的“偷”,甚至情急时刻不看话语对象、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论语·子罕》中的句子“多乎哉?不多也”,但是我们从整体上看的话,其话语主要还是当时在普通大众生活里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现代白话。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语言生活的一个缩影,即语言使用上文言与白话的混杂与纷争。对此,祝畹瑾曾这样写道:“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用文言讲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⑥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孔乙己说了什么话首先是自身的个人语码选择问题,不过可供他选择的社会语言环境也很值得思考。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先谈一下“双言制”现象,它是指在一个言语社区里存在着两种在功能上完全不同的语码,一种语码用于一套环境,而另一种语码则用于另一套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弗格森曾经对多个国家、地区的“双言制”现象进行过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引起了社会语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简单地说,“双言制”是指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语言环境,在这种社会中,除了主要的语言变体外(如标准语、地区方言等),还存在一种十分不同的、高度语码化的变体。后者是早期的或另一个语言社区的丰富历史文献的载体,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书面语和极其正式的场合,在一般的日常谈话中,这个言语共同体的人都不使用它,掌握这种语言变体一般都要通过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弗格森把这种语言变体称为“高层变体”,而与之相对的白话口语、地域方言等则被称为“低层变体”。两种变体在某一语言社区内同时并存,各自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及其特定的社会功能,它们的差别不仅表现在语言系统(如语音、词汇、语法)上,在使用场域、社会声望、文学遗产、语言习得等方面也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⑦。
而在中国社会中,文言与白话的并立与竞争不只是小说《孔乙己》所表现的五四时期,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汉语里这种文言与白话的并存状况是否属于“双言制”现象呢?
有的学者提出这只是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变中的过渡,而语言变化的渐变性、长期性使这一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呈现出分层的特点,与弗格森所说的“双言制”语言社会的特征虽有交集,但似乎也不能归为典型的“双言制”现象。不过,赵元任认为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语言状况基本上就是“双言制”的,对当时汉语的情况他指出:文言相当于高层变体,而口头说的官话则是标准的低层变体,此外还有各种地域性的底层变体,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甚至大到完全可以把它们视为“不同的语言”⑧。其实,不管我们是否用“双言制”理论来看待它,当时语言生活中文言与白话的分层与对立却是客观存在的。赵元任发现并描述了这种语言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比较成功地预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语言发展趋势。他认为20世纪初期的汉语好像正在从“双言制”状况向“标准语—方言”的状况发展,因为作为汉语低层语言的标准变体、抑或是它和高层变体即文言的混合体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各种书写中,也就是说,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标准语。而与之同时,文言的使用范围则日益狭小,其声誉也在不断下滑。20世纪中后期以来,汉语的发展进程最终验证了赵元任先生的预测,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因素,应该说这一因素极大地加快了汉语的这一演化进程。现在,让我们再把话题回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上,以往人们对孔乙己话语进行分析时,总关注于他“窃书、偷书”、“多乎哉?不多也”等“之乎者也”型的语句以及“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等表层语言形式,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其背后的语言演进过程。
在《〈孔乙己〉文末附记》中,鲁迅写了这样一句话:“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⑨那么,小说是否真的“没有别的深意”,“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呢。如果我们联系他在别处的言谈文字,或许会看得更为明白。例如他在1926年的演讲《无声的中国》里说:“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⑩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在文言和白话的论争中,鲁迅对当时社会语言使用的文白分层状况有着精准的判断,并已经初步预见到20世纪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向,而其作品《孔乙己》则具象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语言状况以及在汉语转型的大背景下普通百姓的话语选择。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崔晓飞,河南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教师,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应用学。
①孙伏园:《鲁迅回忆录》(上),《鲁迅先生二三事》,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②冯明毅:《质朴精练 含蓄深刻》,《理论月刊》,1999(7),第41页。
③刘玉凯:《“语言场”与〈孔乙己〉》,《名作欣赏》,2000(6),第24页。
④贺明华:《公共领域中的艰难对话》,《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1),第36页。
⑤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第4页。
⑥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⑦⑧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第238页。
⑨《新青年》,1919年4月15日,第六卷第四号。
⑩鲁迅:《鲁迅杂文经典全集》,《无声的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