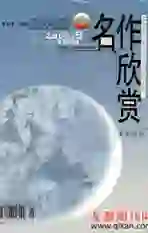漫游: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意生存”浪漫主义者的生命形迹
2009-05-29张保华
张保华
关键词:“诗意生存” 浪漫主义 漫游 生命价值
摘 要:“漫游”是一种人类对于生命诗意生存境界的追思过程,是不安于现实的灵魂的追寻存在意义的生命律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意生存浪漫主义者沈从文、徐訏、无名氏和冯至都表现出了富于个性的生命漫游特征。他们的精神漫游形迹和作为其载体的文学文本,一同成为奉献于读者的诗意风景。
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称精神上无所归属的现代知识分子为“自由漂泊”者,这种精神“漂泊”的文化背景就是西方近代以来无孔不入的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占领造成的异化现象,使人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无所归属感。这种“漂泊”或称之为“漫游”,其实是一种人类对于生命诗意生存境界的追思过程,是不安于现实的灵魂的追寻存在意义的生命律动。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追问生命本体价值——自由的实现途径的浪漫诗哲们几乎都有表现自己在自然中孤独漫游的作品。庄子“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精神获得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屈原在放逐的“远游”中对困惑人类存在等问题发出的“天问”;被罗素称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卢梭,反对任何社会文明、工具理性、规范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一生都处在孤独地漂泊之途上,晚年仍徜徉于湖光山色中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歌德不仅因为厌恶庸俗鄙陋的魏玛宫廷曾逃往富于人文主义气息的意大利,游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迹,他的《浮士德》也以主人公的上下追索“带给近代人生一个新的生命情绪。……就是‘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①。
显然,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对生存价值意义的沉思与追索方面,古今中外的“漫游者”是精神相通的,而这些浪漫诗哲的精神维度在本质上与后来的存在主义又有着同源性的联系。事实上,德国近代浪漫派的思想就直接地启发了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于人类“诗意地栖居”的思考。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如沈从文、徐訏、无名氏和冯至等汲取中外双向的思想营养,在以“漫游”的精神形态追问生命的诗意生存价值上展示了类似的气质与发展可能性。
一、沈从文:皈依自然时生命神性的启悟
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漂泊的状态下,成名后“乡下人”的自我价值标准定位又使他与城市工商文明格格不入,陷入了精神失乐园的深深孤独之中。从此“寻找精神家园”就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一大主题。
所谓“寻找精神家园”,即是沈从文对生命意义执著不移的追索。沈从文认为人生包括“生活”和“生命”两个层次,人如果只停留在衣食男女的“生活”层次上则是生物学上的一种“退化现象”(《黑魇》),人之为人的根本即在于“生命”。因此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就成了他文本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沈从文看来,现代社会的种种,即各种“事实”、“纲要”、“学说”、“禁律”均非出于“真实情感”的产物,“它完全建立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美术,背后都有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因此人们迷失于“具体”的委琐之中而忘记了“抽象的追寻”、“生命的庄严”。如同西方的诗意生存浪漫主义者一样,沈从文决心以自己的笔承担起挽救日益堕落的人灵的任务,立志在这“神之解体”的时代,为人类寻找美丽、光明的神迹。于是,他把自己比作不懈追求的浮士德,“无一日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长庚》),“为抽象而发疯”(《生命》)。在他“向虚空凝眸”、“为人类远景凝眸”(《从文自传》)的痛苦沉思中,“‘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烛虚》)的精神漫游者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之所: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的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不仅这些与“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水云》)
这里,沈从文以一种泛神论的情感去与自然静观对语的时候,他获得了所谓生命的神性在于美与爱的神圣的天启:神在生命中,而具有神性的生命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永恒的栖息之地。
二、徐訏:“迷途灵魂”流浪中的生命想象
徐訏也是在不停的形神漫游中追寻着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他声称“文学不是记忆或回忆而是想象”,他的凝结着浪漫主义想象的创作“只是一个迷途的灵魂,抒写它的体会与摸索”,“所表现的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灵魂在不同的环境里挣扎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与小我的自由与生存而已”②。显然,这是一种对诗意生存境界的不断追寻,那么,这种诗意生存的境界存在于何方呢?
对于徐訏而言,现实是残缺的,因此他只好在精神的漂流中寻找诗意的彼岸。他常以旅途中发生的浪漫爱情构架他的故事,这个爱情或是一次奇异的邂逅,或是一个荒诞的梦境,女主人公个个超凡脱俗,男主人公“我”也是雅量高致,他们的情感经历也都属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作家以生花妙笔把自我理想中的人性光辉尽情地涂抹在他们身上。作品中男主人公“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即漂泊者),从东方的上海到西方的马赛,从神秘的阿拉伯海到荒谬的英法海峡,从城市的赌窟到山林中的尼庵,其足迹无所不至。这里的女性既美丽多情,所生活的环境也是符合自我理想的“意念化”的世界:“我”在上海的荒郊野道上深夜与“鬼”结识,而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女鬼”所以钟情黑夜,是因为夜的宁静、朦胧、神秘能使她远离尘嚣,获得更多形体、特别是精神上的自由(《鬼恋》);吉卜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从神奇的马赛到南美大草原,“我”为了自由,宁愿家国不归,随吉卜赛女郎浪迹天涯(《吉卜赛的诱惑》);“我”被海盗“邀请”到英法海峡一个辽远小岛上,而这里的海盗营地竟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官吏、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荒谬的英法海峡》)等。奇人、奇地、奇遇,作者的确是编造故事的高手,但他制造传奇并不仅仅是一种赢取读者的策略,所要表达的更是主题学意义上与世俗世界的对立。只有在这些没有腐儒道德、远离功利尘嚣的地方,这“自然”的种种:黑夜、大海、荒岛、草原,进行灵魂冒险的人们才能追寻到真正的爱情、美好的人性、生命的平等和生存的自由。
比较而言,虽然在许多方面土生土长的沈从文和西式教育的洋博士徐訏都有很大不同,但无论是沈理想中的湘西社会,还是徐梦境中的天涯海角,都是一种非理性的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文化边地”,是生命获得自由、充满人性之美的精神家园。
三、无名氏:上下求索“生命的圆与全”的极限体验
与徐訏相比,同被称为“后期浪漫派”的无名氏的精神漫游更具现代色彩,其意志的表达也更具强度。他以其独特的强者气质执著地在毁灭与再造的反复运动中追寻个体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整个灵魂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去找,找,找!走遍地角天涯去找!——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清楚。正因不知道,我才必须去找。我只盲目地感觉,这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东西。”③正是这种潜意识深处原初神秘、不安分的生命冲动,引导他背离现存的自我和本然的处境,去追寻那深不可测的魔魅的生命存在。
这种“寻找”在被其视为“创作阶段”(即其成熟阶段)的宏伟巨著《无名氏书稿》中借主人公印蒂的生命运动逐步展现。印蒂是一个身体强健、思想纯朴,两面都“原始粗犷”,有“野兽性”,即自然性的人。应宇宙自然、雷雨风暴运动伟力的启示,他决定去“地角天涯”追寻“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东西”,追寻“生命的圆与全”。印蒂先是参加革命,灵与肉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被诬“托派”,心灰意冷逃向具有极致之美的爱情,当爱情达到巅峰时,他又感到了“过度满足后的疲倦”,于是他抛弃爱情,投奔东北义勇军,兵败溃散后,他堕入黑社会,要将灵魂“染上另一种颜色”,最终沉沦待救。印蒂整个的行为过程,大起大落,极限体验,以彻底的灵魂冒险从生活表象中印证生命的真谛,包括参加革命,因为“革命和政治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部门”。印蒂的这种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过程颇合“浮士德精神”的要旨,深合于歌德人生境界的精髓。无名氏也曾经特别声称:“在生命里,我只爱两样东西:‘自我和‘自由。”(《海艳》)坚守“自我”中心,将“自由”仰视为生命存在的本体地位,可以说从个人主义、个体生命价值的角度无名氏得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