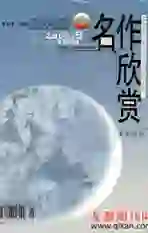坚守中的突破
2009-05-29刘凤芹
打开《路遥文集》,阅读他的每一篇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结晶。在文学创作繁花似锦、文学评论不断出新的多元化格局中路遥始终自有见解,不赶时髦。
作为一种方法,现实主义自有其质的规定性,但并不是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它同时还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洛蒂认为:“能达到现实主义要求的不仅只是一种手段或风格,而是有无数的手段或风格。因而现实主义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史业已证明,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现实主义从来都是一个不断丰富的美学体系。同样,中国当代开放的文化环境、多样的社会文学思潮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当时新潮迭起、趋新若鹜的文学形势不可能不对路遥造成一种“追赶”的压迫,没有什么能够比“落伍”“过时”更使作家感到难堪和尴尬的了。因此,路遥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要有勇气用新的手法来表现”。执意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甚至为自己规定了“无榜样意识”的创作原则。由此看出,路遥的突破意识是十分明确的。
“圆形人物”的塑造
英国文学批评家福斯特说过:人是具有多面性的,这样的人他称为“圆形人物”。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中所塑造的此类人物并不是很多,“扁平形象”却比比皆是。这些扁平形象多是一维构成,符合当时流行的二值判断(即黑白逻辑),非是即非,非善即恶,非白即黑。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似乎只有二值,排中律的使用使得那段时期的文学里只有两种人,要么好人要么坏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中间区域被人为地删除了。于是立体变为平面,复杂化为简单,内在化转为脸谱化,真实被扭曲、剥夺。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对人物的简单判断简直达到了极至——完全以阶级属性为标准进行二元判断。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甚至是“改革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延续着这种模式的判断。
路遥对于这种现象是颇为不满的,决心“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间分不清‘好人坏人的人”,《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这种有意识塑造的一个“圆形人物”。对于他,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他既不像梁生宝脚踏实地地为集体事业而贡献全部力量,也不像郭振山一味热衷于营建自己的安乐窝;既不是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之人,也不是不择手段的庸碌宵小之辈;他的追求目标正当且高远,追求方式却又下作而卑鄙;既有保尔的坚韧,又有于连的钻营;他不鄙视任何一个农民,却从来不打算一辈子务农;他抛弃巧珍的态度是决绝的,但内心却备受道德谴责的煎熬;他鄙视、痛恨利用权势牟取私利,却又坦然仰仗权势、不正之风牟取私利;他的灵魂光明又污秽,内心自卑又自亢。这些十分矛盾的性格汇聚其一身,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人生》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热烈的大讨论。对于习惯于二值判断的读者来说,高加林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他们的惯常思维,我们很难说他是英雄,却又不能说他是坏蛋,在这里采用非好即坏、非肯定即否定的简单化的判断是解析不清这个“圆形人物”的。但是,对于这种打破,读者不但不感到别扭,反而感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有着“感同身受”的震撼。这不能不说是路遥的巨大成功。
其实,任何一个典型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路遥总是注重挖掘、表现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其笔下的高加林、黄亚萍、高大年、高明楼、孙少安、田福堂、孙玉亭、刘丽英等莫不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完全突破了以往好人与坏人完全对峙的僵硬模式。如农民政治家田福堂,尽管也以权谋私,但并不横行乡里,没有彻底泯灭农民的传统美德与做人的良知,当他因私欲而告发了孙少安时,却好像“给自己的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得安宁”;他在村里有政治家的威风十足,在女儿的婚礼上却透露出乡下人的卑怯;虽有老谋深算、狡诈的一面,也有顺应乡风民俗温情的一面;他会为谋私利而绞尽脑汁,但是在牵涉到集体利益的时候,也会寸土必争。正是这些美丑并举、善恶融通的矛盾组合使田福堂成为具有多种特性而且富于变化的圆形人物形象。
浪漫主义色彩的呈现
路遥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也合理大胆地吸收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作品充蕴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司汤达曾言:“浪漫主义是为人提供对当代习惯与信仰给予应有的尊重的文学作品的艺术,它能够给人以最大的愉悦。”正是因为路遥所兼收的浪漫主义手法,使得其作品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大大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涵。
一、激情的倾注。在作家心灵固有的种种因素中,浪漫主义又把情感置于最高位,视情感为诗之精髓和本原。乔治·桑给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为:“感情,而非理智,相对于脑的心。”被视为浪漫主义重要特征的激情,在路遥这里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显示。
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的描写,忽视或淡漠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感情作用。路遥却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激情的倾注,勇于打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界限,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在路遥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到那颗充溢着真情的心灵的震颤和悸动,常常会觉得自己仿佛沉浸在一种由浓厚的感情氤氲所构成的氛围里。这种浓烈的情感色彩几乎贯穿于他全部的创作活动中,是沸腾在他作品中的血液。
当然,浓烈的情感之所以能震撼我们的心灵,主要不在于情感的有无,而在于情感的真诚与否。沈德潜曾说:“情真,语不雕琢而自工。”路遥的作品因感情的真诚而打动人。而这种真诚是源于他刻骨的生活体验,“生活要首先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路遥之所以要写《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因为梦魇般的生活冲击着他,些许的温情感动着他,以至于他不得不“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人生》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曾几次动笔都搁下来,但后来还是把它写出来,因为对路遥来说“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
二、理想的建构。席勒也明确地将“表现和显示理想”作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路遥虽然坚持以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之间尖锐的矛盾对立,但在心爱的主人公形象设计上尤其是在爱情模式设置上却充满了理想的色彩,从而完美地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
马建强,可以说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马建强始终在学习上独占鳌头,在精神上也保持高尚、清白、超常自尊的优势。当我们看到他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拾到了钱和钱包仍能够抵制强烈的生理欲望的诱惑,不能不说作者过分张扬了马建强的自尊与人格。孙少平更是作者审美理想的最佳体现,路遥几乎是竭尽全力地赋予其各种道德壮举:慷慨相助萍水相逢的打工妹小翠;婉拒漂亮大学生金秀的追求;抵制调往省城的诱惑等等。孙少平之所以获得年轻读者的喜欢,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是理想的化身,体现了许多青年人对于自身理想形象的追求。其他如孙少安、田晓霞、冯雪琴、田润叶等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同样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这些形象与其说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不如说是表现作家理想与激情的艺术符号。
路遥对于自己钟爱的农民之子马建强、高加林及孙少平三兄妹的爱情设计排列上,更具有理想色彩。他总是让城市的男女追求他钟爱的人物形象,并让具有强烈优越感和优势的竞争者一败涂地。这就是路遥所设置的:城乡结合(贵贱结合)+对比型的爱情模式。
郑大卫是郑副县长的公子,却为马建强的无意的介入而痛苦万分,张克南不但自己是副食部副主任,其父母也都是领导干部,但在爱情竞争中却一败涂地;高朗不但职业、单位远远优胜于孙少平,贵为省城副市长的父亲更让其头上笼罩着优越的光环,尽管如此,田晓霞的心里却没有他丝毫的位置。路遥为苦心孤诣地安排这些贫困的农家子弟都拥有如此浪漫、不同寻常的爱情奇遇,而且面对的强大对手均所向披靡。尤其是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可以说是完全是超越于世俗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很难做到完全无视爱情之外的附加因素,当黄亚萍虽然极其痛苦但仍不会为爱情而嫁给又沦为农民的高加林时,身为记者、地委书记千金的田晓霞却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无所有的煤矿工孙少平,这不能不说是超越现实的浪漫。但为了要显示农村青年的才情与人格魅力,路遥不惜采用这种理想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当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减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
尽管路遥大胆吸收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但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赤裸裸地表现作家的审美理想和情感,而是让理想和感情笼罩在理性的辉映下,在作品真实具体的描写中,通过生活本身的逻辑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田晓霞的悲壮死亡,结束了作者超越现实的梦想,孙少安对田润叶爱情追求的理智的拒绝,同样是作者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表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凤芹,山东菏泽学院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