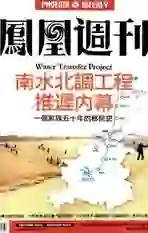龙应台:为亡魂上一炷文学的香
2009-05-11苏惠昭
苏惠昭
“因为香已上过,我现在感觉异常平静”。龙应台说。
采访她的那一天,龙应台把自己缩小在台北亚都丽致饭店巴赛丽厅一个昏黄角落,清瘦的脸庞发散出如母亲般的、温柔的光。
那一炷香,她说的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是龙应台2009年出版的新书,对她来说,这是一本非在2009年10月到来之前出版不可的书,也就是说,必须“压迫着自己”在2009年夏天结束之前完成,然后编辑、排版、付印。2009年,之于台湾,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60年;之于大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60年,从甲子至于癸亥,刚好是一个甲子的循环,错过了这个60年,龙应台心中一紧,她再没有第二个60年了“而上香,对中国人来说,就要在对的时候上,错过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炷香,她为那一段混乱残酷流离时代的千万战争亡魂而上,没有国籍,没有党派,飘飘荡荡于异度空间的亡魂。
乘着文学的翅膀
人类果然是活在各种条条框框中的动物啊。当龙应台宣布要写一九四九,她面对的是几种制式的反应。“你是不是冲着十一而来的?”香港记者问。“你要写外省老兵吗?”这是台湾的反应。台湾香港之外,她听到最多的是:“噢,你要写建国60年!”
都不是,龙应台惨然一笑。她不是写建国60年,不是写外省老兵,也无关十一。《大江大海》她已经酝酿20年,她想要写的是国家机器、战争机器下,“那些单单的、孤零零的个人”。
1989年她动心起念,1999年开始阅读数据,但才一开始,就接任了台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长,在“龙应台干不下去”的漫天猜疑中,一任3年做到底,为台湾示范了何为“由下而上的文化运动”。
1999年到2009年之间,父亲过世,母亲失忆。对龙应台来说,母亲失忆所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父亲的死。“父亲的过世是绝对的,你无法再去敲门,但母亲活生生地在你面前,还跟你说话,你却无门可敲。”一个是门关上了,一个是根本无可敲之门,而时间是没有商量的,在时间收去所有记忆之前,龙应台终于下定决心,非写不可。
在所有门都关上之前,消失之前,她非走进去不可,跨出的第一步就是“上天下地地读数据”。
《大江大海》写了400天,应该说,400天中约有80%的时间,中国大陆的、台湾的、日本的、德国的,还有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龙应台多在和庞大的资料搏斗以及作田野调查。虽然她受过学术训练,却不是历史学家,“我像个小学生进入历史的丛林”,这丛林生态多样缤纷,仰头看不到天际,一条岔路通向另外一条,还有埋藏在地底的未知,以及真伪难辨的拟态,彷佛成千上万个支离破碎的碎片撒落在一片海洋。“我希望下学者的工夫,像石头一样把所有数据绑在腿上,”龙应台说,“可是我也知道,到最后,我写出来的必须是一部文学作品而非学术著作。”
她期望她的书“像蜻蜓翅膀那样飞起来”,“如同把音符似的历史碎片串连成自己的音乐演奏”,能够“温柔地牵着年轻人的手走进来”,要那样飞,那样演奏,那样温柔地牵手,只有通过文学的翅膀。
历史的小学生进入了历史丛林,展开个人的大冒险,一开始龙应台并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换句话说,她对于将会写出一本怎样内容的书,全然无知。她要说的故事存在数据以及数据之外,树叶要拨开,石头要翻起来,并且得反复检验其真伪。她还必须要思考,写作者必须拔到怎样的高度和宽度,才能将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经纬度的人、事、物串连起来,让它们平行并陈,彼此互注……好比龙槐生(龙应台父亲)与朱甘亭(香港大学校长朱经武父亲)的交错。当上尉朱甘亭奉命押着一箱空军后勤补给的黄金上船,经过广州天河机场时,曾被驻守机场的宪兵连长龙槐生拦截;又好比,田村胜吉,一名派驻新几内亚的22岁日本士兵,他和23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以及四十几个来自台湾南投埔里的台籍日兵如柯景星,担任俘虏营监视员的,他们大约都在同一时间待在战俘营。
还有同样饿死数十万人的列宁格勒围城与长春围城。
“所以我是不是在做一件超过我能力的事?”有一度龙应台甚至软弱地自问,失去信心,而父亲母亲的面容浮起在面前。
龙应台起先在香港大学的“龙应台写作室”写,也以香港为基地大江南北去调查与采访。A00多天的最后两个月,她把数据搬到台北,为了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进入了一种寝食俱忘的状态,终于在8月初交出第一稿,9月初读者读到的热烫烫新书《大江大海》其实是第三稿。第一稿以1945年日本战败,44艘美国第七舰队船只堂堂驶入黄浦江揭开序幕。第二稿,开场是台北街道图,从摊开来正是一张中国历史地理地图的台北街道名写国共交火的四平之战、德惠之战、锦州之战,写长春围城。当第二稿进入最后一校时,几个负责校对的年轻朋友很诚实地告诉龙应台:“龙老师,这个开场载着太多的历史,很难进入。”龙应台望着这些连孙立人的名字都不会写,问过她黄百韬是国军还是解放军的青春面容,轻喟了一声:“好吧!”她狠心请出版社毁掉已排好的版,重新调整结构,把家族史调到第一章,这一章从“美君离家”写起。美君是她的母亲应美君,在1949年1月离开如今已沉在水底的淳安古城,到江苏常州寻找她的宪兵队长丈夫龙槐生。
那年龙槐生和应美君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3年后在这个南方之岛之南的高雄,为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龙应台”。
没有说完的故事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书发布会现场。
龙应台出生在高雄大寮,整个童年随着担任港口警察父亲的职务调动而迁移,是永远的插班生。插班生长大了,长成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飞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1984年以一本批判社会的《野火集》轰隆一下烧遍台湾;然后又飞到欧洲“漂流”713年,成为德国人的妻子和两个男孩的母亲,同时潜入研究纳粹历史、东德共党历史乃至柏林墙翻转史。“正是这段经历帮助我打掉了许多条条框框。”2000年,龙应台回到台北担任文化局长,卸任后转而接下香港大学聘书,教书并继续以华人为对象撰写评论,成立龙应台基金会。2007年以《亲爱的安德烈》,2008年以《目送》,成为重量级畅销作家,这两本书写的都是“人生基础课程”,譬如亲情,譬如生死,譬如对生活的细腻体会。但《目送》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记录我身为难民女儿的特殊人生际遇”,这使得《目送》到《大江大海》有了逻辑的关联。其间给龙应台带来最大震撼的,是她在追索家族史以及两百万撤台“外省人的漂流与伤痛过程中,所触及延伸到的20万台籍日本兵,“在地600万人隐藏的伤,我觉得恐怕比外省人更深,更寂寞。他们要处理的内心纠结,对或错,正义或不正义,究竟自己属于战败的—方还是战胜的一方,那种混淆和迷茫的程度,超过了外省人”。
那么完成后的《大江大海》是怎样的一本书?或者这样问,它将烧起怎样的一把火呢?在台湾,新的书腰以“一本书改变一个时代:上市10天,突破8万册”宣告它的势如破竹,太多人迫不及待想对龙应台诉说他们的感动与感谢。
台湾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龙应台心目中第一顺位读者。“老师,我小时候常看到祖父和他的朋友一块唱日本军歌,而且每人手上拿着一张认真抄写的歌词,”一个女孩泪眼汪汪地对龙应台说,“那时候我多么瞧不起他们啊。”
看完书,重新认识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了解祖父辈那一代的经历,他们的伤,女孩才知道自己有多么不了解祖父。
女孩当然不是个案。年轻人因为读完《大江大海》而去追问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历史,这在台湾几乎成了全民运动。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人,龙应台为1945年来台接收台湾的国军七十军,还给了他们一个被公平看待的机会。
几乎所有台湾孩子都听父祖辈说过一个故事:日本战败,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当时长达50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涌上台北街头相迎,结果咧,他们看到一群穿草鞋、背雨伞和铁锅的破铜烂铁……
这个经典画面经过60多年的传诵依然不移不易地定格在那里,但龙应台要进一步问的是:“为什么?七十军到底经历什么?”
是的,七十军确实历经过惨酷的风霜,这支队伍之前8年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从血河里爬出来”后,1945年受命千里行军赶到宁波,却又突然被告知要来接收台湾。好了,一支力气被榨干的队伍加上不适应的海上航程,个个晕吐到死去活来,这就是台湾人看到的七十军,“他们就这样踏入了历史的相框”。
这本书,龙应台也希望写给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看,给美国人看,给日本人看。日本和中华民国台湾一样,有一个战败创伤症候群,一个不愿去面对的1945,因此不断逃避对于它的殖民地,譬如台籍日本兵所受的磨难。
“无论如何也要有日本版!”一名会读中文的日本记者对龙应台说。
中国大陆呵,正在欢欣鼓舞、轰轰烈烈庆祝建国60年的中国大陆,龙应台认为,就像她为七十军破败褴褛形象找到理由这一段可能冲击台湾绿色选民,而给予日籍老兵的温柔对待可能会让深蓝阵营无法接受,在正面陈述力量更加强大的中国大陆,《大江大海》描述的某些历史,更有可能刺伤读者。
一个是长春围城,1948年3月到10月,这个城市被解放军滴水不漏地围了半年。半年,饿死的人估计在10万到65万,取其中数,就是30万,“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龙应台高声问。
还有淮海战役中“把俘来的民兵推上第一线当炮灰”,龙应台想,这在中国大陆的人民的感情上恐怕不能接受。
不过可能引起最大反弹的,不是长春围城和淮海战役,龙应台估计是关于中日战争的部分,她书写日本军的角度。
“照你这么说,龙应台,难道中国人日本人全部是受害者吗?那么谁又是加害者?”她猜想这样的质疑必然排山倒海而来。
龙应台清楚她将要面对一波接续一波涌上来的“不喜欢”、“不接受”,面对无数的嘴舌和手指指着她向她索求答案,“但我写这本书根本无意去做任何指控谴责,以及判断谁是谁非”。她要做什么7她要把侵略者被侵略者、正义与不正义、是与非“平等来看”,她要打开一个一个的盒子,把那个国家机器拆解开来,让人看到这里头“单单的个人”、“孤零零的个人”,看他们流血的地方。在相反的阵营里,无数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同村子的人帽徽一换就成了敌人,“但脱下军服,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国民”。每一个单单的个人都在流血,从这个流血的角度看进去,龙应台要让读者以此对照自己原有的正义不正义、是非与善恶的价值标准。
要看见伤口才能治疗,看见了对方的伤,你就不会再恨,龙应台相信,只是乱世中活下来的人,不管本省人外省人,“他们的伤60年来没有处理过,就这么将就地活着,隐忍着活着,放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但不是说人要忘记过去,把握今天迎向明天吗?不是说要族群融合向前走吗?为什么要回头去看彼此的伤口,再痛一次?为什么?其实太多人心里都明白,因为那个伤口一再被政治所利用,没有真正地、彻底地被抚慰、治疗。
“我唯一要说的是,你要思索,把我摊开来的东西看进去,然后拿来与既有的价值观对照。”龙应台知道,这中间必然存有巨大的矛盾,但《大江大海》不处理这个矛盾,它不告诉人什么是正义,不教人怎样解决矛盾,“我让你看到个人,看到你痛恨的人、不同族群的人,他的痛和他的伤,至于你要如何处理这个矛盾,那是你自己的事”。
故事当然没有说完,也不可能说完,龙应台甚至有些不敢相信她已经完成了书,但是香已上过,集体治疗也开始了,她的心异常平静。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样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大江大海》的最后一段话,龙应台如此写下。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