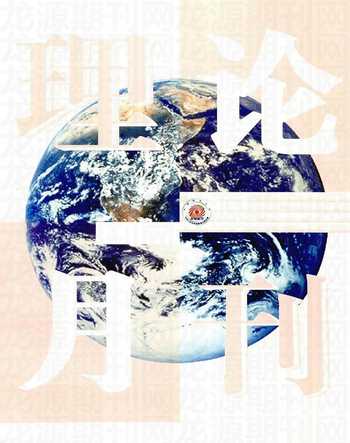日本古代教育的特点
2009-04-29李建钢
李建钢
摘要:日本古代教育根源于中国,而且儒学在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日两国在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教育方式、学习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古代教育的巨大差异,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可以看出日本古代教育的一些鲜明特点。
关键词:日本古代教育;儒学;实用实利;私学;僧侣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157-03
一、儒学思想是日本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上记载了日本应神天皇15年(据考证大约在公元5世纪),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先后有阿直歧和王仁来到日本,成为应神天皇儿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王仁由于撰带了《论语》和《千字文》,被日本人尊称为“书祖”,这个事件便是著名的“儒学东传”,此后众多的皇族和贵族子弟跟从王仁学习,日本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活动开始了,可以看到日本有组织、有规模的教育活动是与儒学传入日本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并颁布了著名的《宪法十七条》,这部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实际上是一篇教化文章,目的是以儒学思想中的道德规范约束各级官吏的行为,提高天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化改新前后随着许多到中国的留学生、留学僧受到重用,儒学思想不但成为日本的治国之策,而且以法令形式被规定为教育的中心内容。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的“学令”,参考了中国唐代学校设置的方法,在日本京城设立类似于唐国子监的大学寮,在地方设立国学,学习和考试内容是“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伦语》,儒学成为贵族阶层广泛学习的学问之道,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如菅原清公、大江音人、营原道真、三善清行等教授儒学的教育家。
13世纪,中国程朱理学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这种被称之为朱子学的儒学精致理论很快在日本传播起来,对武家政权产生了极大影响,朱子学中强调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前提下通过“格物穷理”的方法加强个人修养的理论,成为日本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到了江户时代朱子学经江户幕府历代将军推崇,被列为在幕府直属学校中统一能够教授的学问,江户幕府还实行奖学政策,优待儒者,培养出了一批独立的儒学传授者,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教育最为兴盛的时期。
日本儒学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气息,从中国儒学传到日本起,日本人就在根据自己的需求不停地改造它,从中日两国古代教育中对儒学思想不同地阐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本古代社会是以身份制做为统治基础的。镰仓时代以前贵族把持政权,官吏世代相袭,镰仓时代以后虽然武士掌握政权,但武士阶层中依然是以身份来划定各自的权力范围乃至生活轨迹的,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人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身份管理制度达到了最严格时期,由此在传播和向学习者灌输儒学思想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特别强调“礼”以及从“礼”中衍生出的大义名分思想,为固化日本社会等级秩序辅垫理论依据,排斥以“有德者王”为核心内容的“仁”的思想,推崇“礼治”的孔子被神化,而宣称“汤武革命”的孟子被极力贬低,在教育体系中“尊孔贬盂”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一情况直到幕末才有所改变。其次,在“忠”、“孝”教育中与中国儒学相反,大力宣扬“忠”的思想,而将“孝”放在第二位,通过“忠”的教育使下级对上级、卑者对尊者单方面无条件忠诚,通过这种教育使日本人树立“孝”从属于“忠”的观念,在“忠”、“孝”的两难选择中必须义无反顾地选择“忠”。这些与中国儒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导致了日本民众的心理倾向于绝对服从,也使日本人在各自的阶级层次中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各司其职。
二、实用实利思想在日本古代教育中占有突出地位
《大宝律令》中“学令”所规定的各类学校与唐代学校一样把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但是由于日本自古以来的选官制度是以贵族体系的世袭制为主,虽也从中国引进了科举考试但由此选拔出来的官吏很少而且也只能担任最低级的技术型官吏,因此从日本设立正式学校开始,在教育中就很重视基层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实用实利的教育思想比较突出。
大化改新后除设立大学寮、国学外,还设立教授特殊技术的阴阳寮、典药寮、雅乐寮,专门培养天文、医学、音乐方面的人才,到了奈良时代,适合日本人现实生活需要的文章道、纪传道(历史学)兴起,为了能使日本人更好地学习这些学问,日本文字的基础平假名、片假名被创造出来,由此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和历史书籍,这对日本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创建独立民族文化开辟了道路。奈良时代时日本私学也迅速发展起来,私学除传授儒学和佛学外也将传授工艺美术、金工、木工、雕刻、绘画等各种技艺作为主要内容。平安时代时,日本国风文化兴起,这一时期日本文化产生了“体”、“用”分殊思想,即道德观念和实能生活中的技能可以遵循不同的规则,《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就提出了“和魂洋才”的理论(幕末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观与此有相同之处),“体”、“用”分殊从此在教育观念中也有了充分的体现。平安时代末期上层贵族和公卿纷纷在自家兴办学校,学习者除了学习儒学经典,以应付官吏录用考试外,掌管家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后,“资于用”的教育目的更为明确。镰仓和室町时代,武家特别重视“弓马之术”,但教授武士的实际技能也是教育的重要目的,室町时代上杉宪实整顿足利学校,使易学和兵学成为最重要的教学科目,为武家政权培养出了大量人才。
江户时代日本古代教育达到了鼎盛时期。德川家康对教育非常重视,在他主持制定的京都公卿贵族、各级武士和普通民众必须遵守的多项法令中,都有倡导教育学习的规定,以后江户幕府的历代将军都遵循这一原则,极力奖励学问。仔细剖析江户时代的教育,可以看到虽然武家政权推崇儒学。希望以封建伦理道德观使民“教化”,但是“体”“用”分殊的思想。使这一时期实用实利的教育观,以“有用”为目的教育宗旨。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朱子学是江户幕府的“第一学问”,但以复古为名希望从朱子学理论中摆脱出来的古学派,代表民间思想发纫于明代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与神道思想相联系的国学派涌现了一批如伊藤仁斋,获生徂徕、中江藤树、吉田松阳、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著名的学者,他们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说,加之在普遍民众的基础教育中以求实利为目的的功利性教育非常兴盛,使日本民族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了讲究实际、倡导实用的民族性和努力提倡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户幕府前期由于要禁绝天主教,从1633年起先后下达了5次“锁国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到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由于政局已经稳定,便于1720年颁布了“洋书解禁令”,下令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
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日本,允许荷兰人在长畸开设医院行医,允许日本人向荷兰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发了“兰学勃兴”的历史事件,造就了青木昆阳、杉田玄白等兰学家和新井白石、岛律重豪等倾慕西方科技的朝廷重臣、地方大名以及一批喜爱西方科学技术的普通文人。洋学从此成为日本人不可缺少的知识,为此后日本人接受近代西方科学奠定了基础。对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三、私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有举足轻重作用
大化改新后成立的大学寮和国学都有严格的入学要求,大学寮不接纳庶民入学,而国学只有定员不足时,才允许庶民子弟入学,到了奈良时代由于招生名额有限,学校数额不足,使庶民子弟根本不能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由此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日本古代教育中发挥了重要功效。
在大化改新前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南渊清安和僧曼在家中开私学向学生传授儒学,大化改新中的重要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曾就业于此。奈良时代政府支持私学,鼓励学者和有技艺的手工业者广招学生,传授各种技能。到平安时代官办的各类学校极度衰落,由此出现了众多影响很大的私学,如营原家族、大江家族创办的文章院、和气广世创办的弘文院、藤原冬嗣创办的劝学院,在原行为创办的奖学院,尤其是僧人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面向庶民子弟办学,招生对象不问贫富和贵贱,不论僧俗,提倡自由研究的学习之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界限,开辟了庶民教育的先河,在日本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镰仓、室町时代官办的学校消失,教育的任务完全由私学承担,学者们一般在家中开私塾,向求学者传授技能,如教授算学的三善、小槻两家,教授天文、历道的安倍、贺茂两家和教授医学的和气、丹波两家,寺院此时也招收各类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庶民子弟和武士子弟一齐在寺院中研习汉学、和歌和佛典。江户时代官办的幕府直辖学校、各藩的藩校、半官办的乡校相继成立并迅速发展,但由寺院教育转化为基础教育的寺子屋以及私塾等私学,依然在日本社会的教育体系占有重要地位,明治维新后的许多学校,都是在寺子屋和私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到现在日本无论在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私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国私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比日本私学历史漫长的多,日本私学的兴起也无疑得益于大化改新后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学习,但对比二者在各自教育史上的作用却有着较大的不同。首先是地位不同。日本私学自大化改新前后兴起,一直与官学处于平等的地位,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更取代官学成为日本人接受教育的最重要方式,江户时代的寺子屋尤其是私塾学习的门徒非常多,在普及文化和传授儒学以外的学问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反观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将教育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使中国私学始终从属于官学,即使在宋代书院广泛兴起的情况下,私学地位也赶不上官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精致化后,私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衰落。已于官学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同。日本官学以培养官吏和实务人才为目的,以儒学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而私学以普及文化和基本技能为目的。主要学习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读、写、算的各种知识,私学不但讲授儒学,而且传授国学、洋学、医学、军事学等多种学问。私学教育中注重实学精神,主张通过自由的学习气氛和学术竞争,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自唐以后的私学和官学的教育目的都是通过严格的正统儒学教育使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而走入仕途。在教育中都片面强调封建伦理道德,鄙视和摒弃实用技能教育,加之官学和私学的教材都是由国家编写并命令使用的,使官学、私学在教育理念、方法和学习内容上没有根本性区别,在中国古代教育上难以形成多种学术、多种流派、多种教育思想共存共荣的局面,这是使中国在清代以后的学术上难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三,造成的结果不同。日本私学是突破官学教育桎梏的最重要力量,也成为明治维新后建立新型学校的基础,其在日本民众中普及文化的教育目的使江户时代成为日本古代教育发展的顶峰,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这一比例在亚洲各国名列前茅,兰学也是由于私学得到了广泛传播,私学的兴盛广泛提高了日本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为明治维新做好了观念上的准备工作。中国的私学确实与之无法相比,中国私学做为官学的补充,基本上承担了中国古代人启蒙教育的任务,但中国私学并不以普及文化为目标,而是教育学生从小适应科举制的需要,与官学一样采用刻板、僵化、模式统一的教育方法,特别是明清后完全抛弃了孔子“应材施教”的教育方式,这同样是造成清代以后的中国人眼光狭小、崇尚空谈、缺乏应变能力重要原因。
四、僧侣阶层在日本古代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佛教经典繁多,思辩性强的特点,加之广泛传播的需要,使佛教僧侣在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是富有文化气息的阶层,这一点在日本古代僧侣们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就决定了日本僧侣们在教育上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时就有大量僧侣随同到中国去学习,归国后自然就承担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其中的著名人物僧曼不但担任了大化政府国博士的职务,更开办私塾传播儒学。空海创办综艺种智院为贫贱子弟提供学习机会,既传授佛学也传授儒学。镰仓、室町时代、寺院成为日本人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武家子弟和庶民子弟从六、七岁开始在寺院中学习《孝经》、《千字文》等儒家经典,研读佛典,僧侣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教师。在官学衰落后僧侣们维系了日本古代教育的命脉,使日本普通民众受教育的范围得到了扩大。镰仓时代日本佛教逐渐世俗化和本土化,出现了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禅宗等佛教新宗派,这些佛教新宗派与奈良、平安时代佛教宗派相比,其教义通俗易懂,修行方式简单朴素,与日本民众的心理特点和需求相契合,迅速在全日本传播开来,其中的杰出人物法然、亲鸾、日莲、荣西、道元等人及其一批深受教诲的僧侣们利用寺院教育和民间教育活动,把新宗派的思想和理论播撒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传播宗教时,自然普及了教育。
13世纪时朱子学传入日本,这种对以后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学问之道是由到中国求学的日本僧侣们带回日本并由他们传播给日本人,朱子学在最初是伴随佛学思想一齐在日本流布的,朱子学长期依附于佛学思想。这一状况直到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儒学家藤原惺窝批判佛教思想,鲜明阐发自己“离佛人儒”理论后,日本朱子学才真正走向独立并达到了全盛时期。在此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僧侣们在教育过程中所贯彻的“佛儒不二”的教育理念,对日本古代教育乃至民众思想有着深刻影响。江户时代后佛教逐渐势微,但由于武家政权“兴禅”的举措,使“参禅悟道”的热潮不但在武士中流行而且也被普遍民众所推崇。投身到寺院中接受佛教思想教育的人从上层贵族、武士到一般平民络绎不绝,僧人心越兴俦应德川光国之邀在祗園寺开堂讲法时,来自日本各地的民众有一万七千余人。僧侣们仍然在日本教育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在宋元交替时有大批入日僧人。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人,他们抵日后不但传授佛学而且在教育学生中着重阐发朱子学理论,他们也是使朱子学在日本迅速流布的重要人物。明末清初时也有大批入日僧人,如隐元隆琦、木庵性瑶等人在日本广授门徒,促进了日本书法、绘画、治印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这些中国僧侣们同样对日本古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札记‘学记》中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为俗,其必由学”,这种思想使中国古代统治者从春秋时期起就非常重视教育,此后的历代王朝都沿袭教育为先的治国理念而日本直到江户时代才确定了文教立国的政策,把对民众的教育放在治国的第一要务上,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虽然两国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同样推崇儒学,但在教育上却呈现了较大的差异,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笔者粗浅分析主要是由于无论是贵族体系社会还是武家政权,日本社会利用身份制进行管理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等级秩序森严,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身份和职能,基本上无法改变,通过学习考取功名进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办法很难奏效,加之日本虽然在大化改新后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但由于选官制度主要依靠世袭制,实际上通过科举考试的文人只能担任最低层次的官吏而且也很难得到升迁,因而日本古代教育并未把培养学生如何参予科举考试做为主要的教育目标,缺少了功名、仕禄思想的日本古代教育把着眼点放在了普及大众文化和钻研“有用”之学的理念上,从而也使教育方法和学习内容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中日两国古代教育理念的不同尤其是十七世纪以后教育理念的不同,使两国在通过教育以怎样的标准培养怎样的人才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是造成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