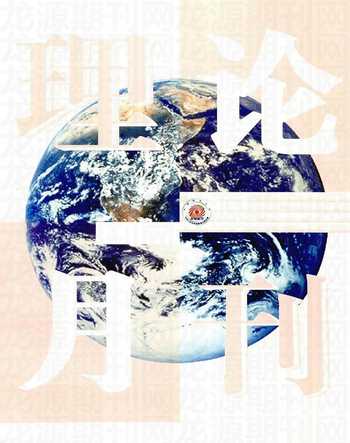证据法律模式论
2009-04-29秦绪才
秦绪才
摘要:对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的研究和论证,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几近空白。对这一新的证据理论的研究,既需要法哲学的指导与启迪,充分运用“法律模式论”的理论,又需要对诉讼模式和证据法律模式的关系的正确把握,同时,亦需要对各国证据法律模式进行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比较。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与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特点,以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的互动关系为基础,首次提出了证据法律模式的双重含义理论。即证据法律模式应包括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这两层含义。证据法律的宏观模式与其诉讼模式相一致;而证据法律的微观模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和证据法的各个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出发点,将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现代职权制模式和微观上的“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而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对抗制模式和微观上的“规则-概念”模式。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法律的分析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证据法的模式,从宏观上看,应属中国式的对抗制模式;而从微观上看,则属“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无疑,证据法律模式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理论,对我国统一证据法的制定和理解及适用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模式;诉讼模式;证据法律模式;宏观模式;微观模式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096-09
对于证据法律模式问题,国内目前尚无人探讨和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和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剖析我国现行证据法律模式,以探寻我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如同诉讼模式理论一样,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应是十分重要的。如此重大的证据理论问题,竟被我国学界长期忽略和漠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但仅凭笔者的一篇文章。显然是不够的。希望籍本文以抛砖引玉,引发并带动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研究的兴起和深入。
一、证据法律模式的法哲学基础
对于“模式”(pattern or model)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若仅从语义上理解,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标准样式或标准形状与结构。人们在许多学科领域和学术领域都在广泛地使用“模式”这一概念,如有“政治模式”、“法律模式”、“经济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管理模式”、“教育模式”、“诉讼模式”、“审判模式”等等。虽然“模式”的含义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意义,但其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明确的,即“模式”是指某一系统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亦是某项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即模式是通过揭示该事物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说明或表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差异。我国许多学者抓住模式概念具有揭示和说明事物本质属性并可以区别某事物与他事物不同的功能,以诉讼模式这一概念来研究和概括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并以两大法系诉讼模式的研究为基础,揭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民事诉讼模式——大陆型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而对证据法律模式,可以从多种视角来探讨,但笔者在此是从民事诉讼的视角来剖析和研究我国证据法律模式问题。而且,学者们对诉讼模式的探讨和研究,已经为我们研究证据法律模式提供了示范和引导。因而,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参照研究诉讼模式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证据法律模式问题。当然,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不言而喻,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要建立某种诉讼模式,需要对其诉讼结构或诉讼构造进行分析,而要分析某一诉讼模式的诉讼结构,就要弄清楚该诉讼结构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该诉讼结构由哪些要素组成?这些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诉讼结构是不是这些结构要素的简单相加?这里。黑格尔关于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与它的统一体的关系的论述正好给我们以启发和说明。黑格尔认为,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的统一体中方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经过解剖学家的手才能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此时所碰到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死尸。又如,收音机中每个器件均有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且不相同,但每个器件的作用都是整体作用的一部分,都受整体作用的制约。可见,我们既要弄清楚诉讼结构的结构要素是什么和有哪些,又要弄清楚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即彼此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应明白,某一诉讼结构并不是其全部结构要素的简单相加。某一诉讼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应是各个“结构要素”共同作用且整体一致的结果。而诉讼结构恰好揭示和说明了诉讼模式的基本特性。这就是笔者概括出的诉讼模式理论。而这一诉讼模式理论与法的模式理论又是一脉相承和相互协调的。
所谓法的模式论,就是指法的系统或整体与法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法的模式论需要借用系统论的理论及其相关范畴。在系统论中,系统是指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整体;要素则是指组成一个整体或系统而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可见,我们借用“系统”或“要素”等系统论的范畴来揭示和说明法律现象或法律事物时,就形成了法的模式论理论,即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法律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以这种法律模式论来分析和研究诉讼结构,就形成了诉讼模式理论,即诉讼模式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诉讼结构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而以法律模式论和诉讼模式论理论来分析和研究证据法律现象时,就形成了证据法律模式论,即证据法律模式亦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证据法律结构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通过对某一证据法律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就可以揭示和说明某一证据法律的基本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来解析证据法律,使我们对证据法律的认识更清晰、更具体、更丰富,而且对证据法律的制定和适用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概而言之,“模式论”是通过对某事物或行为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来揭示并说明该事物或行为的结构样式及其基本特征。运用“模式论”来研究法律和法律现象时,就形成了“法律模式论”。“法律模式论”在各个部门法学中甚至某个部门法学的各组成部分中的运用,就形成了诸如立法模式、诉讼模式以及证据法律模式、证人作证模式,等等。法律模式论通过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就可以揭示和说明法的本质和基本特性。对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研究,也应从其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人手,并通过比较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结合我国证据立法的实际情况,来探索我国证据法律的基本特征和运行发展的规律,进而构建我国的证据法律模式理
论,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制定我国的统一证据法。
可见,法的模式论是对证据法律模式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的理论基础。证据法律模式作为法的模式论的分支性模式,是法的模式论被运用到对证据法律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果。
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影响较大的法的模式论主要有三种,即庞德的模式论和哈特的模式论以及德沃金的模式论。无疑,这三种模式论对我们分析和研究我国证据法律模式具有重要的借用价值。
(一)庞德的模式论
庞德的模式论,作为法的典型模式,是由美国著名社会法学派人物庞德提出来的。庞德认为,任何一个法都应当由技术、理想和律令这三种成分构成。故庞德模式论又称为律令一技术一理想模式论。所谓律令成分,主要指规则,同时还包括原则、概念、标准及学说等因素。规则作为律令的主要形式,其功能是对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具体的后果;原则的功能在于作为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的出发点;概念则是一种可以包括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而标准的功能在于作为一种行为尺度来适用于各个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况。所谓技术成分,是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规定和概念的一系列的方法。包括为审理特殊案件而在权威性法律资料中寻找审理依据的方法。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技术成分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立法模式的主要差异。
所谓理想成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特定的社会秩序应当是什么以及通过法律对社会实行控制的目标又是什么等等。因而,这种理想成分可以解释为是指法律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成分往往用于指导某些新奇案件的解决。
概而言之,技术成分是一系列的方法,律令成分主要是规则,原则成分是权威性的出发点,概念成分是权威性的范畴,而理想成分则是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庞德认为,律令、技术和理想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技术从法律的理想中得到其精神和方向,律令从发展和适用它们的技术中获得实际意义和全部生命,并从理想中得到其形式和内容。
(二)哈特的规则模式论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在批评奥斯丁的法的命令模式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规则模式论”。哈特认为。法无疑是一个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其中,主要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而次要规则是关于“规则的规则”。人们依据次要规则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引入新的主要规则,取消或修改旧的规则,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决定这些规则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实施。由于次要规则主要是授予权利,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授予权利的规则”。
(三)德沃金的模式论
德沃金作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规则—政策一原则模式论”。德沃金认为,实证主义的法律模式理论并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实践的典型运行模式,由规则、原则和政策三因素而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才是其典型的法律运行模式。德沃金认为,原则和政策相对于规则而言处于同一个抽象的层次。但政策和原则又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政策是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特征的改善,以及某种集体目标的保护和实现;而原则则是关于个人的权利、正义或公平的要求或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显然,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区别。原则是抽象的,而规则是具体的;在适用时,规则是僵硬的,要么有效,要么无效,而原则具有灵活性;原则与原则发生冲突时,应比较各项原则的相对分量和重要性。而规则与规则之间并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的区别,对规则的比较,应在规则之外寻求相应的标准,规则本身并不包含可以评价它自身重要性程度的标准。
上述三种法的模式论分别阐述了各自关于法的本质的理解和观念。事实上,这三种法的模式论都各有自己的缺点。
庞德的模式论由于将理想视为法律的要素,因而,在此种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法与非法界限的混淆,使法失去应有的确定性,并为法官自由裁量的宽泛化甚至滥用留下隐患。尽管,将法律理想视为法律的要素,可以增加法的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克服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教条主义。
哈特的规则模式论虽强调了法的逻辑结构和确定性,但此种模式论将法律视作一个封闭式的僵硬的体系,则可能会导致法律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泛滥。
而德沃金的模式论,虽然亦具有灵活性的优点。如将原则视作法律的要素,但是,它又将政策作为法律模式的一个要素。则又可能会导致政策与法律之界限的混淆,似有不妥。
我国有学者在上述三种法的模式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模式论,即“规则-原则-概念模式”。这一法律模式论也是我们研究证据法律模式的理论基础。而证据法律模式,作为法的分支性模式,当然不能等同于法律模式,也不应是法律模式的细化和广义化,而应与相关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相联系。通过对相关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进行抽象和概括,则可以确定该证据法的结构要素,而将该证据法的结构要素依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即相互关系进行合理且科学地排列组合,则就形成了该证据法的模式,即证据法律模式。既然,证据法律模式是对证据法律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高度抽象与概括。那么,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应当有哪些?笔者认为,一般而言,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的范围与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的范围既是相联系的,又是有区别的。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包括了法律模式的一般结构要素如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原理、原则、概念、制度、规则和学说等,但并不限于法律模式的一般结构要素,还应有其特殊的结构要素,如程序、方式、科技、诉讼理念、诉讼文化,等等。但一国的证据法律模式到底有哪些结构要素,则取决于该国的证据立法。
可见,要搞清楚我国的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特点和类型,就必须要搞清楚我国证据法律模式已经包括了哪些结构要素,而这又只能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法律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得出。而对于我国证据法律模式应该包括哪些结构要素才是合理、科学和完备的问题,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对证据法律模式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应当说,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据法律模式的研究与论证还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几近空白。当然,这与一些人持淡化模式研究的观点有关,但原因不仅限于此。也与学界对模式理论的学术研究不够深入有关。人们不应当忘记,二十世纪末期,学者们以诉讼模式的研究为切入点所带来的我国诉讼模式和诉讼体制的变革和转换。因而,对模式理论的研究不应当淡化,而是应当进一步深入和加强。事实上,对于证据法律模式这一问题的研究,既需要法哲学理论的指导与启迪,又需要对证据法律模式与证据法及于诉讼模式的关系的正确把握,同时,亦需要对各国证据法律模式进行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比较。
二、证据法律模式与证据法及与诉讼模式的关系
(一)证据法律模式与证据法的关系
证据法的模式,不同于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
分,当然也就不同于证据法。正如同诉讼模式不同于诉讼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一样。证据法的模式与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尽管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范畴,证据法的模式属于证据理论的领域,而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则属于证据立法的范畴,但证据法律模式与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又是相互联系的。具体来讲,一国现有的证据法律决定了该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的范围,也体现出一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性特点。因而,分析和研究一国的证据法律模式,就应当着眼于一国现有的证据法律。通过对一国现有的证据立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揭示和说明一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特点和类型。而证据法律模式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即对证据法的制定具有指导性和预决性。有什么样的证据法律模式,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我们通过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分析和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相应的证据法律模式。总而言之,证据法律模式与证据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证据法律模式影响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证据法亦影响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样式和类型,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二)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的关系
证据法律模式必须与诉讼模式相协调,相一致和相呼应。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有什么样的诉讼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证据法的模式。也就是说,诉讼模式直接规划和制约着证据法的模式,诉讼模式是证据法律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证据法律模式并不是消极地适应和配合诉讼模式。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证据法律模式理解为诉讼模式在其运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证据法律模式作为诉讼模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性模式,体现着诉讼模式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且对诉讼模式的发展和变革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证据法律模式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诉讼模式区分的主要标识或说分水岭。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就是我们区分纠问式诉讼模式与现代职权式诉讼模式及对抗制诉讼模式的主要依据;同样,不同的证据规则,又是我们区分现代职权制诉讼模式与对抗制诉讼模式的主要依据。从我国目前审判方式改革的情况来看,证据法律模式对诉讼模式积极的推动作用,亦是十分明显。可以说,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对证据制度的改革上。也正是证据制度的改革推动了我国诉讼模式的变革。从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到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再到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都是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为核心,并将证据问题作为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瓶颈之一,以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推动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和诉讼模式的转换。但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理论作为指导,而证据法律模式论理论应当是指导我国证据制度改革与完善的证据理论之一。对诉讼模式理论的研究,带动了我国审判模式和诉讼模式乃至诉讼体制的革新与转换,因而,笔者预言,对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必将带动我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并最终进一步带动我国审判模式和诉讼模式及诉讼体制的继续革新和发展。
我国从全面落实和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人手,转移法院审判权的重心,强调当事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和法院当庭认证。显然,证据制度的这一变动,使得我国的审判方式和诉讼模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证据法的模式与诉讼模式的这一互动关系,既有形式上的,又有内容上的。形式上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证据立法体例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将证据法律制度置于民事诉讼法之中,亦可以进行单独立法。内容上的互动关系则主要表现在证据立法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影响诉讼模式和受诉讼模式的影响。而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重心正是证据法的模式与诉讼模式在内容上的互动关系。
为了最简明和最清晰地阐释诉讼模式、证据法律模式、证据法这三者的互动关系,笔者用图形表示如下。
三、两大法系证据法律模式类型
(一)两大法系诉讼模式对各自证据模式的影响众所周知,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模式或称对抗制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则为职权主义模式或称职权制模式。基于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从内容上谈谈两大诉讼模式对各自证据制度的主要影响。
1当事人主义模式对其证据制度的主要影响
当事人主义模式或日对抗制模式对其证据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事人对各自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事实负有主张责任。法院对当事人未主张的基础事实不得代为主张。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通过审前程序中的诉答程序来主张各自的基础事实。原告提出事实主张,被告则针对该事实主张进行答辩。被告的答辩既可以是消极的自认或否认,也可以是积极的抗辩。积极抗辩是被告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它是指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提出新的事实加以对抗。如果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还有新的事实主张,则仍可以再次答辩。双方当事人通过答辩和交替性的事实主张,达到形成争议焦点的目的。如果没有争议焦点,诉讼程序便不再继续进行。
(2)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主张和抗辩主张,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至表面可信的程度,从而形成各自的案情。即双方当事人有提供证据形成各自的案情以推进诉讼的责任。此种证据,英文表述为“Prima Facie Evidence”,可译之为“初步证据或表面证据”,其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基础事实的证明程度只要求达到20-30%即可。基于此种证据(Prima Faeie Evidence)而形成的案情,英文称之为“Prima Facie Case”。如果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形成自己案情的程度,则对方当事人无反驳的责任,而且,对方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法院基于诉答文书作出判决或作出简易判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此特援引美国一位学者的一段英文著述加以说明:“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or goingforward is satisfied by evidence which, viewed in the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
burdened party,
is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trier of fact reasonably to findthe issue for him,For example。when the burden of persuasion 0f more probablv true than not true is also placed upon the party,the burden of producingevidence is satisfied bv the introduction of evidence
which, viewed in the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burdened party,is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trier of factreasonably to find that element of the claim for reliefto be more probably true than not true When theparty thus burdened introduces such evidence as toeach element of the claim for relic£he is said to havepresented a prima faeie case,Failure to satisfy the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requires a decision bythe court as a matter of law on the particular issueadverse to the burdened party,”
英美法系中举证责任或说证明责任的这种独特含义,即当事人提供证据形成各自的案情以推进诉讼的责任,无疑是与其对抗制的诉讼模式相呼应的。这也表明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其证据法律模式对当事人主导诉讼的特定要求。法官因无举证责任而几乎完全是消极被动的。
(3)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由当事人提供而不是由法院代为提供。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要求当事人收集证据。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发现程序就是为当事人收集证据而设置的。当事人依靠发现程序,可以直接向占有证据或了解案情的任何人或单位收集证据,且不必取得法院的首先同意或批准。
(4)当事人在法庭审理程序中,负有调查证据的责任。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中应当庭提供证据,并引导出证据的具体内容。对证人的询问,不论是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还是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都是由当事人进行的,法院一般不询问证人。显然,这也是对抗制诉讼模式对证据制度的必然要求。
(5)对证据规则的影响。对抗制诉讼模式不仅影响和规定着证据制度的性质和原则,而且对某些证据规则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律规范中非常重要的且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证据规则之一。它的产生,就与对抗制的诉讼模式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运行。就不会有对传闻证据规则的需求。所谓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一般理解为即排除传闻证据,而传闻是指在诉讼中作证的人以外的人所作的陈述。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3.1条第a项将传闻界定为指在诉讼程序中以言词方式作证的证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的以证明有关事项所作之陈述。确定一项证据是否为传闻证据,步骤有二:一是看是否包括他人先前之陈述。这种重复他人先前所说的话的方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二是分析有关证据提出的法律目的,既是否用作证据以证明法院裁判所依赖的案件事实。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1(c)的规定,所谓传闻是指不是由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中作证时作出的陈述。且在目的上用它来证明主张事实的真相。
显然,传闻证据规则体现了当事人主导诉讼和控制诉讼的对抗制原则。通过实行传闻证据规则,使双方当事人能够实际地进行交叉询问,以发现案件真实,同时,也可以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当事人行使交叉询问权的前提就是证人必须亲自到庭,而且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应是证人本人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也就是说,传闻证据规则是当事人行使交叉询问权和对证人证词进行质证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对抗或攻防的证据规则基础。
2职权主义模式对其证据制度的影响
大陆法系国家所实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所实行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各自的操作方式不同而已。我们说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为职权制或非对抗制,实际上仅仅是指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上的职权行为和诉讼进行上的职权行为这两个方面。而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式辩论原则仍然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也是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共同特征。
一方面,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在收集证据的问题上,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态度有所不同,除强调以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基础外,还辅之以法院的协助查证职责。因而使其民事诉讼显现出职权的色彩。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55条规定:“调查证据,由受诉法院为之”。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62条亦有类似的规定:“法院可以委托官厅或公署、外国的官厅或公署以及学校、商会、交易所或其他团体,进行必要的调查”。
另一方面,在诉讼的推进问题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实行与英美法系国家完全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进行主义,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奉行职权进行主义。也就是说,英美法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有主动权和控制权。其法官几乎完全消极被动:而大陆法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程序启动和继续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由法官依职权行使。这也使得大陆法民事诉讼的职权色彩较为明显。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主要差异,即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彻底的辩论主义原则,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则实行的是不彻底的相对辩论主义原则。正是基于此,学者们将英美法民事诉讼称之为当事人主义模式或对抗制,而把大陆法民事诉讼称之为职权主义模式或职权制。
正是因为大陆法民事诉讼实行不彻底的相对辩论主义原则,因而,使得其证据制度亦有别于英美法国家的证据制度,呈现出职权主义的色彩。鉴于辩论主义的诉讼原理对证据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笔者在此仅从辩论主义的诉讼原理出发,来阐述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对其证据制度的主要影响。
彻底的辩论主义有三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有主张责任,即事实主张责任,这种主张责任不同于举证责任且先于举证责任而产生。也就是说,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只能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没有主张的事实,法官无权调查,即使通过职权调查得到证实,也不能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应作为法官裁判的事实依据。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自认,无论是明示的自认,还是默示的自认,都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具有拘束力。三是当事人对各自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不允许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
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由于奉行不彻底的相对辩论主义原则,所以,其证据制度亦归属职权主义类型。主要表现如下。
(1)法官在当事人举证的基础上负有一定的调查取证的职责。(2)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责任,这
一责任不同于举证责任且是举证责任的基础。当事人有责任提出事实主张,以形成各自的案情,即“Prima FaeieCase”。否则,法官可基于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利于对方的裁判而结束诉讼。(3)在某些证据形式的形成中,法官的职权作用明显。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72条规定:“受诉法院可以命令鉴定人一人或数人参与勘验”。(4)法官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主动地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核判断,而不以当事人是否提出异议或申请为前提。在英美法国家,法官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若要进行审核判断,需要有当事人的申请或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若既不申请审核,又不提出异议,则适用自认规则。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模式正出现一种相互融合、不断接近的趋势。受此影响,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模式亦呈现出一种混同和融合的趋势。实行对抗制的英国和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由于陪审团作用的变化,正处于改革之中,其目的在于赋予民事诉讼一定的法官职权色彩。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程序则发生着相反的变化。如德国于1977年7月实行了《简易程序修正法》,对其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使德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分为准备程序和主辩论程序两个阶段,改变其一直采用连续审理主义和没有严格审前程序的做法。而采用集中审理主义原则,严格区分审前程序。实行举证时限制度,等等。这些都使德国的民事诉讼程序透入了许多对抗制的空气。
(二)两大法系证据法律模式类型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诉讼模式,会产生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证据制度和证据法律模式。而证据制度和证据法律模式的不同又非常强有力地佐证了诉讼模式的不同。对抗制下的许多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在职权制诉讼模式中就没有。反之,亦然。
正是基于诉讼模式和证据法律模式的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证据法律模式首先应与其实际运行的诉讼模式背景相一致。换言之,证据法律模式首先应归属其相应的诉讼模式类型。举例说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首先应归类为当事人主义模式或对抗制模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亦首先应归类为职权主义模式或职权制模式。这是我们从宏观上理解证据模式,此其一。其二,如果我们从微观上来理解证据法律模式。就会发现,将证据法律模式解释为证据法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仅是从微观的层面上来理解证据法律模式,而这种对证据法律模式的理解,因缺乏宏观的高度,又忽略了诉讼模式对证据法律模式的既定作用,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我们对证据法律模式含义的理解,既应从宏观上理解,又应从微观上来理解,才是全面的和正确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所谓证据法律模式,应包括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这两层含义。证据法的宏观模式与其诉讼模式相一致:而证据法的微观模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和证据法的各个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搞清楚这一点,是我们研究证据法律模式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点。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说,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从宏观上讲,属对抗制模式;而从微观上讲,属“规则-概念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从宏观上讲,属职权制模式;而从微观上看,属“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
为什么说从微观上讲。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属“规则-概念模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则属“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其理由概述如下。
1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属“规则-概念模式”
这里,笔者主要以美国的证据法为例来加以说明。美国证据法在继承了英国普通法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经过许多新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普通法与成文法并存的局面。20世纪中后期,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成文证据法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国会通过的《联邦证据规则》(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目前已有38个州以《联邦证据规则》为蓝本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美国在证据方面的立法采取民事和刑事统一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有众多的成文证据法规,但浩如烟海的判例仍然是美国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联邦证据规则》对美国证据法的巨大影响,因而笔者在此仅以该成文证据法为例来分析研究美国的证据法律模式。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共11章,62条,内容包括:总则(规则101-106),司法认知(规则201),推定(规则301-302),相关性及其限制(规则405-415),特殊(规则501),证人(规则601-615),意见和专家证言(规则701--706),传闻(规则801--806),认证与辨认(规则901---903),文书、录音和照片的内容(规则1001--1008)以及附则(规则1101--1103)。
从上述《联邦证据规则》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其实只涉及法庭处理证据的各项规则。而我们所熟悉的调查证据和证据交换规则因属于诉讼程序的范畴,故由美国诉讼程序中的发现程序加以规定。这也说明美国证据法与其诉讼程序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发现程序中所规定的调查证据和证据交换规则应属广义上的证据法的内容。若以《联邦证据规则》为主干,再结合联邦诉讼法典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美国证据法的内容极其丰富,但其主要内容则不外乎下述10个方面:(1)证据的相关性与可采性规则。(2)证人规则。(3)特权规则。(4)意见证据规则。(5)司法认知。(6)传闻证据排除规则。(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8)证据交换规则。(9)证明责任。(10)证明标准,等等。
可见,美国立法者们在构建美国证据法的结构和内容时,是以“规则”模式为主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证据概念,联邦证据法典又以“定义”的方式加以明确,如《联邦证据规则》801(a)、(b)、(c)、(d)对“传闻”(hearsay)和“陈述”(statements)的所作的定义和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美国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和结构样式,即对美国证据法的微观模式,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化为“规则一概念模式”。
2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属“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业法官裁判制度,基于职权主义原则,法官对证据的调查起主导作用,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的大小由法官依其人格、能力、知识和经验作出评价。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查明案件事实,法律对证据能力基本上不予限制,但对审查判断证据的程序规定较为严格,建立了许多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如直接审查原则,言词审查原则,等等。就证据规则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复杂且严格,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却简略且灵活,这些简略且灵活的证据规则为其抽象而概括性的证据原则留下了宽广的适用空间,凸显出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模式的“原则化”
色彩。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主要强调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问题,对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范围予以严格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却主要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程序。其原因是: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着重于调整和规范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是围绕法官的主观思维活动(审查判断证据)而展开,并不是以证据能力为中心而设置。其证据法的内容着重于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活动和法官的认证活动与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活动而非当事人的举证活动。我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9年12月17日最后一次修改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五节有关调查证据的一般规定和第十二节有关独立的证据程序的规定中,可以发现和找到上述特征。这也表明了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的职权色彩。即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的证据法律模式。
可见,相比之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笔者用“原则一制度一程序一规则一概念”模式来描述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应是恰当的。
四、我国现行证据法律模式类型
对于我国现行证据法的模式的探讨,笔者将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主要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和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法律依据,来分析、阐释我国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和结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概括和抽象出我国现行证据法的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只有12个条文。这些条文基本上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问题。同时,由于没有可供遵循的具体的证据规则,经验甚至直觉往往成为审判人员分配举证责任和判断证据的依据,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权因只有概括性和灵活性的证据原则而实际上很难有效控制,也因此而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有证据原则而缺乏具体的证据制度和众多的证据规则以及对一些重要的证据概念缺乏明确的立法定义,这样的立法状况使得我国证据法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这也表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法的结构类型应为“原则”模式。《这种证据法律模式的严重结构性缺陷已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重要因素,换言之,证据法律模式问题,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实现与达到。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这一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无疑对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构建,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证据法律模式的理论视角来透析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笔者发现,《证据规定》所确立的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应属“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我国证据法的模式从最初的“原则模式”到目前的“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无疑,这表明了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也表明了我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审判方式及诉讼体制改革的深化。以下是笔者的分析和论证:
1从举证责任含义的界定和分配规则的确立来看,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概念和规则已成为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重要结构要素。尤其是规则要素,就其作用而言,已成为我国证据法律模式中最重要的结构要素,且其与大陆法系证据法律模式的规则要素在内容和作用上已大不相同,而更接近于英美法系证据法律模式的规则要素。即我国的证据规则主要是围绕当事人举证和质证以及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来设置。这一点与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相近而与大陆法系的证据规则不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对举证责任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分配规则及其他情形没有规定。而《证据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基础之上,在第2条中对举证责任的含义作了规定,同时,《证据规定》在第2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中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倒置规则和特别规则。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我国理论界深受大陆法国家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影响,而以此说为通说,《证据规定》对此亦予以确认。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倒置规则,《证据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相应的倒置规定。对于举证责任的特别规则,确立了实质分配标准,即允许审判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即不属于形式分配标准的情形),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综合具体案件的情况,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
2从对自认规则的空白到原则规定再到自认规则的进一步具体化来看,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规则构成要素。其内容正日益丰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自认规则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对自认作了原则规定,即规定了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对于自认的条件、范围和法律效果及有关拟制自认(推定自认)、代理人的自认与自认的撤回等问题,没有规定。而《证据规定》就上述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3从《证据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证据交换制度和证人作证制度及鉴定制度等来看,制度因素是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又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限,但《证据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证据规定》除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外,还对证据交换制度及新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特别规定。证据交换是举证时限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对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案件适用举证时限制度的特殊要求。证人作证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证据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民事诉讼法》只对证人作证作了原则规定,而《证据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之上,使证人作证问题真正制度化,对证人资格、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及询问证人等问题作了规定。关于鉴定问题,《证据规定》亦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之上,确定了具体可行的鉴定制度,对鉴定程序的启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确定,重新鉴定,鉴定书的形式要求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4从《证据规定》确立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以及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来看,原则要素仍然是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性要素,但其数量和其重要性已让位于规则要素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证据规定》第73条根据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在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第63条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依据什么来判断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和大小,这一问题则属证据规则的范畴。如相关性规则。传闻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意见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及书证优先规则,等等。而“高度盖然性”和“法律真实”这样的规定,因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应归属于原则结构要素。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原则”,即是指“原则要素”,是从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的角度来理解,而不仅仅限于我们通常所讲的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法律模式的原则要素与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两者之间有区别,亦有联系。一般而言,证据法的基本原则都属证据法律模式的原则要素,但“原则要素”并不仅仅限于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还包括其他一些具有原则性的证据规定。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的学术观点。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原则。《证据规定》第64条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这一原则既强调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依据法律的规定,也强调法官应依据法官的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地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显然,这一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符合审查判断证据的一般规律。同样。这一规定亦属于原则要素的范围。
5从《证据规定》有关视听资料的规定来看。科技亦是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之一
当今世界各国都倾向于将视听资料划归书证或物证的范畴,而我国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视听资料的科技性。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是视听资料的主要特点,而我国在证据法中将其规定为独立的证据形式,这就表明了科技亦是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之一。其实,我国现有的证据法律在很多地方都涉及关于科技手段的问题,如,在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诉讼案件中,在环境污染诉讼案件中,在缺陷产品诉讼案件中,在医疗事故诉讼案件中,在鉴定结论的产生过程中,以及在证人作证的方式上(证人可依法通过双向传输技术手段作证),等等,对当事人的举证问题都可能涉及有关科技手段的运用。所以说。科技也是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之一。
另外,我国证据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已包含在或体现于证据法的各项原则、各种制度及各个证据规则之中,因而不宜将其单独作为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成分。且指导思想类似于德沃金模式论中的政策要素,将其作为法律模式的一个独立要素,则不仅可能混淆政策与法律之界限,而且亦可能导致法律要素与非法律要素之界限的混淆,其错误应是显而易见的。而价值目标亦类似于庞德模式论中的理想要素,显然,将其作为法律模式的独立结构要素也是不妥当的。至于证据程序,笔者认为亦不宜单独作为我国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要素,因为我国各项具体的证据制度实际上已包含了各自的证据程序,可见,程序已属于我国各项具体的证据制度的一个部分。例如,我国的证人制度就包含了相关的程序,如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又如,我国的鉴定制度,也包含了相应的鉴定程序,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用“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来描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证据法律的结构类型,亦应是恰当的。由此,笔者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证据法律模式,从宏观上看,应属中国式对抗制模式;而从微观上看,则应属“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
无疑,这种证据法律模式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证据理论,对我国统一证据法的制定和运行,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