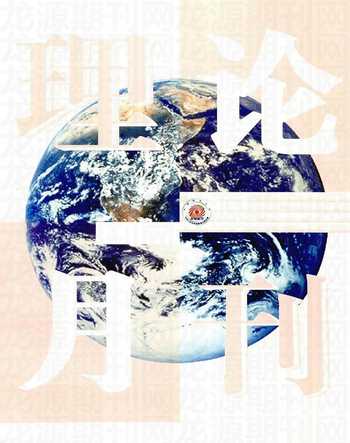英汉名+名结构互译中体现的认知属性
2009-04-29刘鹏李光群
刘 鹏 李光群
摘要:英汉名+名结构在语言运用中相当普遍。由于其结构精炼,语义凝练,因而给人们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一定困难。通过对这种结构的英汉互译,明确了困难产生的原因,即人们一般根据其语言线性排列进行理解和运用。针对这一弊端,本文从英汉语对这种结构的互译过程中在各自的目的语中形成的各种语言形式。并结合认知规律,探索了这种结构形式下潜藏的认知规律,即范畴层次性、认知隐喻性、背景目标认知序列性、路径图式的意象性。通过英汉跨文化互译对这种结构进行了非穷尽性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其形式的束缚。捕捉其语义的脉搏,因而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种语言组合形式。
关键词:英汉;名+名结构;认知属性;图式;互译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093-03
英汉名+名结构的句法属性主要有主谓关系、偏正关系、联合关系、同位关系、动宾关系、补充关系等关系类短语,通过这些句法关系能清楚地认清英语和汉语在各自语法规则和语用规则的制约下,在整个句子框架结构中是如何进行线性搭配的。任何一个语言形式。懂得了其句法特征,只能说明掌握了语言线性组合结构。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就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个语言形式,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会经常出现语用失误或表意不当。要想深入地理解和运用名+名这个结构简练的语言形式,还必须深入到其深层的认知语义层面,弄清两个名词间的语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英汉名+名结构。因此,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两个名词语义间的认知属性。
一、范畴层次性
不同范畴的两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并置在一起,虽然比单个名词或短语的范畴有所缩小,但是可以辨认其它范畴,同时合成后的“语义合成的内涵比输入的语义结构更为丰富”,正如熊学亮教授举的例子:如“电脑”和“病毒”两个原属不同领域的范畴合成为“电脑病毒”这一新范畴,可以用来辨认“杀毒软件”等其它范畴。因此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中许多不同范畴的名词并置在一起,一方面丰富了语义内涵,另一方面有助于辨认其它范畴。具有原型性的基本范畴正是人们对世界事物进行范畴化的有力工具。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都是寄生于基本范畴之上的,因为他们依赖基本范畴获得完型和大部分属性。上位范畴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突出所属成员明显的共有属性;二是聚合功能,即集合低级的范畴构成上位范畴等级。为了满足认知需求,我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范畴层面的词汇上,因为“在基本层面上,可以用最小量的努力获得最大量的信息;基本范畴词汇还具有共同的完形,有助于完形认知,即格式塔感知。”由于基本范畴和原型是人类认知纵向和横向上的最佳点。而且“基本等级范畴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区分最基本的心理等级,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所以在名+名结构上就体现了以基本范畴词汇为中心向上和向下构成不同类型,具体表现为:(1)N基+N基指两个表示基本范畴的名词并置在一起,如apple juice,raincoat,wheelchair,羊羔,马驹,嘴唇等;(2)N基+N上,指基本范畴名词+上位范畴名词,如杏树,桃树,梨树,经书,男人,女人。蚊虫,韭菜,虬龙,羔羊,鲍鱼等;(3)N上+N基指上位范畴名词与基本范畴名词,如心房,心扉,心坎,心田,心弦,电棒,电笔,电场,电车,电工等。
汉语往往在概括词前加上能够区别特征的词来构成新词。而英语采用综合法往往要单独用一个词来表示。如,图书馆library,博物馆museum,饭馆restaurant,体育馆gymnasium,葡萄酒wine,水族管aquarium,红葡萄酒Chianti火车头locomotive,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倾向于用基本范畴层面的名词构成下属层面的复合名词,而英语倾向于用单个名词或符合名词来表达相应的概念。每表达一种事物,就要有新的搭配。如概括词“汤”,有“番茄汤”、“牛肉汤”、“人参汤”,英语相应的译文是“tomato soup”,“beef broth”,“ginseng decoction”,英语根据性质不同,可以有:government revenue,customsduties,income tax,tariff rates而汉语词义表达的笼统性、模糊性为词语搭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国税,关税,所得税,税率。汉语的球迷、影迷、计算机迷、棋迷,但是英语要根据亲身参加与否,而翻译成:football fan,movie fan,computer addict,chess addict。由此可见,英语和汉语在名+名组合的关系上表现出了认知范畴层次的相通性和差异性。
二、认知隐喻性
隐喻一般被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即对语言进行修饰和美化,但是认知语言学却把隐喻看作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它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并且两种概念之间相互关联。名+名结构直接将本体和喻体并置在一起形成简洁凝练的语言结构,体现了隐喻认知模式的有效认知效果。其语言表达模式主要有:(1)N本体+N喻体。即这种模式中喻体对本体进行形态说明表现为语义中心在前的名名结构,如胞衣、碑林、岛弧、矿柱、月球、月牙。这种组合在语义关系上则是后一个名词性语素修饰、限定或说明前一个名词性语素。(2)N喻体+N本体。即这种模式的语义中心一般在后,因为前一个名词修饰、限定或说明后一个名词,如瓜子脸,鹰钩鼻子,月牙湖,ponyengine(小火车头),potbelly,羊肠小道frogman(蛙人;潜水员)等。(3)N整体+N喻体。即前一个名词一般是表示物体的整体,而后一个名词则是以隐喻的方法表示前一个名词的组成部分,如山头、山腰、山脚、山顶、河口,山口等。人体范畴属基本等级范畴,人体词属基本等级范畴词。因此“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之后人们又把对人体的认知结果投射到对其他物体、事物等概念的认知与理解之上。在名+名结构中,两名词表现的隐喻认知模式,英汉语言有着共同的认知序列,即一般是先言本体的整体范畴词语,再言人体名词的喻体词语,如瓶颈、山头、山脚、洞口、火舌、床脚、箭头、火柴头,bottleneck,table leg,arrow head等。但是英语由于介词系统比较发达,在语言序列上还可以出现由人体名词的喻体词到本体的整体范畴词的序列,如headof an arrow,head 0f a match, eye of a needle,arm ofa chair,foot of a mountain,heart of a cabbage,flesh offruit,tongues of flames,etc,(4)NI+N2=N喻体。两个名
词并置在一起,任何一个名词并不具有隐喻的认知功能,而是两个名词构成的语义整体具有这样的认知功能,如“鹅雁”一起指呼喊之声纷乱糟杂,“燕雀”一起指品质卑劣的人,地位卑微的人。而在英语中也有这样的名名结构,正如“外向型复合名词不是就构成形式而言的,而是从两个名词客观所指的具体对象间的关系而言的。这些复合词一般具有贬义色彩,具有非正式文体风格,一般指人,有时也指物”,如butterfingers中butter和finger结合在一起指“笨手笨脚的人”,再如egghead(知识分子),featherbrain(轻浮的人,健忘的人)等。在此两个名词间的语义关系可能很复杂,但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这些名+名结构之间的句法属性似乎都消失了,而且成为一个语义整体产生新的比喻意义,如冰镜喻指月亮,rabbit ears喻指V型电视天线,clover leaf喻指立体公路的交叉点,rainbow指彩虹。
三、背景目标认知序列性
当人们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总是把一个物体当作“目的物”,即我们所要感知的直接对象。而把另一个相关的物体当作“参照物”,借以确定“目的物”的位置和方向。人们感知一幅图景总是以两种方式来感知参照物和目的物,即(1)由目的物到参照物,(2)由参照物到目的物。参照物和目的物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导致了语言表达中中心词和修饰语的语序排列。但是在名+名结构中根据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原则,倾向于“修饰语到中心语”的词序,即当一个结构涉及目的物和参照物时,参照物倾向于出现在目的物之前。如五角大楼、中国客人、中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Department head(系主任)、housewife(家庭主妇)。感知“目标”和“背景”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固定的物体为“背景”,不固定的为“目标”;较大的物体为“背景”,较小的为“目标”;整体为“背景”,部分为“目标”,相当于认知语言学的“射体”和“陆标”的关系,即如果有个客体处在相对于另一个客体的位置,或者向后者移动。那么前者叫“动体”(trajeetor),后者叫“陆标”(landmark)。如,街心公园、湖心亭、bartender酒吧侍者),station master(站长)等。汉语中存在“参照物”在语序上先于“目的物”的原则。当一个结构涉及“目的物”和“参照物”时,“参照物”倾向于出现在“目的物”之前。这种倾向性决定了偏正性名词短语中“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词序。“参照物”到“目的物”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汉语中地名和时间都是遵循由大到小的原则,而英语遵循由小到大的原则,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政务专题小组第二次会议”。再如“曹家后院那种花好看极了。”句中,三个不同层次上的主语由大到小,也是由“参照物”到“目的物”的过程。“曹家”是“后院”的“参照物”,“后院”是“那种花”的“参照物”,从而体现了名名结构在此表现出的递归性原则。
同一种东西,英汉语言具有相同的认知序列,但是在认知参照物的视点选择上却存在着差异。“耳机”与head phone(字面意思为“头机)两个词语,前者着眼于“耳朵”,侧重于耳机具体的佩戴位置;而后者则着眼于“头”,侧重于模糊的佩戴位置。英语laptop(字面意思为“膝上型电脑”)的命名参照点是其使用时摆放的位置,而汉语则依据此种机器的携带特点称之为“手提电脑”,或依据其外观形状称之为“笔记本电脑”。
四、路径图式的意象性
路径图式可以很好地说明意象图式的基本特质,清楚地体现了典型意象图式具有的内部结构。它由三个成分组成,即源点A、终点B、和其间代表路径的一条线,其中的关系是从A点移动到B点的动力向量关系。由此可以看到典型的路径图式是:起点一路径一终点的线形序列,即“起点一路径一目标”图式(The Source-path-goalSchema)。路径图式有其生理基础,构成要素和达到的目标。根据典型路径图式的基本构成,在名+名结构中似乎不存在这种认知图式。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在此结构中存在着路径图式,也就是说两个名词或两个名词短语可以构成路径图式。图式一般具有抽象性,而“抽象性,使艺术作品的读者借助想象填补那些与读者个性、知识域和个人兴趣相对应的具体性细节的空白。”通过两个名词构筑的结构形式和语义空间,读者能够通过两个词语意象来唤起路径图式的完整意象结构,而且还会通过想象去填补空白处空间的细节。“现实世界中两种相异的成分被揉成一个合乎字面说法的整体时,就会造成结构上的一种冲突”,读者遇到文字上的这种冲突时,往往“在各个成分所共有的某种外观特征抑或内在特性的某些方面取得结构的统一性。”从艺术空白和读者想象空间可以明确名+名结构中存在着路径图式的认知方式,表现的模式有:(1)N起点+N终点。即在这种路径图示中省略的是路径而只出现两个具有意象性的名词,如茶壶、饭碗、图书室、书店、车库,windmilL air-rifle,steamengine,oi1 welL power plant,tearoom,textile mill,teapot,sand dune,birdcage,C01"destination,busstation等。(2)N起点+N路径。即在此只出现了起点名词和路径动作性名词,省却了终点名词,如政治影响、思想准备、电影工作、政治影响、president arrivaL pohceinvestigation等短语在句法结构上称作主谓结构。(3)N终点+N路径。即这里省却的是起点名词,而将终点名词提到路径性动词的前面,从而形成了“终点名词+路径名词”的非典型性路径意象图式”,如经济剥削、工业计划、历史研究、文艺演出、case investigation,news probe等,这种路径图示在句法上称作宾语前置的动宾结构。
五、部分一整体图式性
世界上任何物体都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根据人们的认知习惯,一般是先完形后部分的先后顺序。赵艳芳在其《认知语言学概论》中从生理基础和构成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部分一整体图式的意象图式。而张敏在其《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从身体经验、构成成分和基本逻辑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个认知图式。这些分析表明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使整体存在,那么所有部分必然存在,但是所有部分存在,不一定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物体被分成若干部分,可以用整体来表示部分,也可以用部分来表示整体,这就是英语中所说的“提喻(synecdoche)”修辞手段。但是现实世界中实体的整体和部分投射在名+名结构中,也基本上遵循了整体到部分的“格式塔”认知规律,即一般是由整体名词到部分名词的先后顺序,可以略作:N整体+N部分如,人手、手心、手背、山尖、山峰、树干、树叶、树枝、社会家庭、社会机构、家庭成员、身体内部、口舌、桌面、桌腿。raindrop,bread crumb,chocolate bar,snow flake,tortoise--shellwhalebone,arrowhead等。戴浩一把物主一领有物的关系叫做整体一部分关系,因为物主常为整体而领有物常为它的一部分。他发现,如果两个名词性成分处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中,那么在语法顺序上,指整体的名词性成分就先于指部分的名词性成分。英语在N1和N2的序列安排上有两种选择:N1s N2或N2 of N1,而汉语中N1是整体、N2是部分这一事实决定N1和N2词序。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的固定词序是临摹的,英语是让抽象的形态或句法成分标出两种选择的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