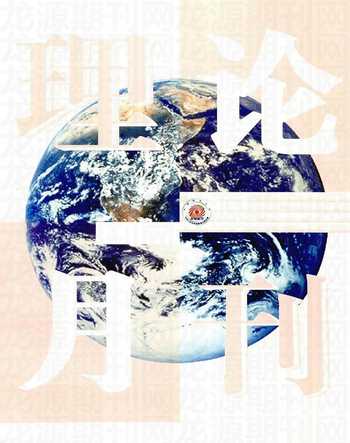双语活动中的认知心理转换机制
2009-04-29丰国欣
丰国欣
摘要:本文从讨论双语的定义入手,以语言知觉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利用心理模块理论和一些心理实验结论。论述了双语活动中的认知心理转换机制,认为人脑通过语言知觉而获得的概念在一定的外界刺激作用下,可以根据它所涉及的事物的时空接近性而联想到一起,从而连接了心理事件和环境事件,达到双语的表述目的;具体表现为,双语活动(如翻译)首先是通过认知心理转换机制来实现两种语言概念系统的转换,然后在概念系统转换的基础上达到两种语码系统转换的目的。
关键词:双语活动;语言知觉;心理模块;心理转换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087-06
人们常常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双语者在交流时,很自然地、无意识地交替使用两种语言。针对这样的双语现象。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值得思考的问题:交流双方为什么要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双语交替使用本质上交替了什么?双语交替使用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立足广义的“认知”定义,即“包括对五官感知的加工、记忆、注意、情感、思维、推理、语言等等”和“认知的无意识性”来分析和论述双语活动中的认知心理转换机制。
一、双语活动中的认知取向
什么是“双语(Bilingualism)”?比较简单的认识就是能够同时说两种语言。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双语现象,特别是如果考察双语的认知心理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双语的情况十分复杂。Bloomfield(1935:55-56)指出:“如果一个人外语学习得很完美,同时没有对第一语言带来妨碍。就会导致双语现象,即母语般地掌握两种语言。”可见,Bloomfield所强调的是,两种语言之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互不影响,互补使用。
不仅Bloomfield持这种观点,很多其他的学者也怀有同样的看法。Maekey认为,“显然,如果我们要研究双语现象,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某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同时,它不仅必须包括使用两种语言,还必须包括使用多种语言。所以我们认为,双语现象就是同一个体交替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转引自余强,2002:2)
另一位学者(Weinreich)认为,“我们把那种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实践叫做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把从事这种实践的人叫做双语人(Bilingualist)。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所有关于双语现象的论述都适用于多语现象,即交替使用三种或者更多的语言。”显然。这两位学者把双语现象的含义扩大了,不仅包含两种语言。而且包含三种或更多的语言。但其基本内涵和Bloomfield一样,也是强调几种语言之间的独立性。
然而,熟练掌握和交替使用两种或更多语言存在着不同的熟练程度,即一种语言使用起来更加熟练一些。而另一种语言使用起来则不如前一种语言那么熟练。换一句话讲,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独立性”存在着较大的相对意义。所以上述定义对双语现象的描述在Bloomfield看来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很难做到这样。Bloomfield认为其原因是“在儿童早期以后,由于人的肌肉和神经系统的灵活性下降或是由于闲暇时间和机会不足,很少有人能够完美地掌握一门外语。……当然,讲外语的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熟练程度才算双语人呢?要明确界定这个标准是不可能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Weinreich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关系角度,论述了双语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并且还论述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如何依托人的大脑产生相互联系的。对此,Weinreich提出了三种假设性的关系:“双语共存”(coordinative bilingualism)、“双语复合”(compoundbilingualism)和“双语依存”(subordinativebilingualism)。我们知道,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信息)以概念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又以语言的表征形式提起。我们以英语的“pen”和汉语的“钢笔”为例加以说明。其英汉两种语言的表征形式可能这样相互联系:双语者大脑中存在着两个概念,分别对应于“pen”和“钢笔”,即英语的“pen”和汉语的“钢笔”不直接产生联系,而是并存于大脑,这种关系就是“双语共存”;或者双语者大脑中只存在一种概念(“一种书写工具”),表现为两种语言表征,即英语的“pen”和汉语的“钢笔”相互联系,这种关系叫做“双语复合”;还有可能是把母语作为中介,第二语言表征才能同概念联系在一起。假设英语是第二语言,汉语是母语,那么英语的“pen”是通过汉语的“钢笔”才和“一种书写工具”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叫做“双语依存”。
应该说,Weinreich的论述明显渗透着语言认识论思想,对双语现象的认识十分精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双语共存”是最理想、程度最高的双语现象。“双语复合”是最普遍的双语现象,而“双语依存”是程度最低的双语现象。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双语之间存在着相对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有关双语的定义,无论是强调双语之间的绝对独立,还是强调双语之间相对独立,还是对双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分,都没有脱离双语的认知取向这一根本的属性。这是因为“人类通过对现实的体验和认知,形成了自己的范畴、概念、推理、语义,进而形成了语言”;而“现实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现实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形成语言的”,简而言之,人们通过认知心理来体验现实世界。从而形成语言,反过来,人们的认知心理又利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世界。双语环境里的人们对现实的体验,逐步形成了两套“范畴、概念、推理、语义”系统,表现为双语交替使用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交流中的双语现象。双语现象进一步说明了,“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所以双语现象也就是人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两种或更多语言来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运用也是人的认知心理外化形式之一。双语并行使用,实际上就是两种认知编码和两种认知解码相互交替使用的形式。因此,要进一步了解双语的本质,我们还应该了解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
二、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
双语转换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呢?双语转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它总是受到心理表征的制约,也就是说,常常受到认知的制约。笔者将结合一定的理论和已有的实验来描述双语活动的心理转换机制。
1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具有认知心理的一般性特征。它以语言知觉为基础。在人的心智本能作用下,瞬间完成表象、注意、记忆、概念、推理、问题解决、言语表述等这一全部认知心理过程。
(1)语言知觉就是大脑对语言的辨识、理解的过程。语言知觉曾经有过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知觉如同我们
辨别物品一样,一件一件地识别或者如同知觉书面文字一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词一个词(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识别。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
Miller利用相关仪器测量被试讲话时的声音频率变化,制作出了语图,其结论是:第一,言语是连续的。各个声音之间很少有停顿,同一个词的不同声音会相互参杂,甚至同一概念不同语言的语音也是相互参杂的。图1就是一个被试在说This is a pen.这个句子时的言语图解表征,其中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声音的频率,单位是赫兹。图中较暗的区域所表示的是每个频率上各个音的强度,而空白边缘是不同单词或者不同音节的边界相吻合。这说明,当你在听一个人讲话时,音节和单词之间听起来好像有停顿,其实这当中很多是错觉。第二,单个的音节会因为上下文而听起来有所不同。图2显示,虽然baby,boondoggle和bunny是同一个音素开始,但是仔细检查,会发现这三个词根本没什么共同特征。另外,同一个音素男女发出来,其频率也不同;同一个因素由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时间不同,或是在叫喊、诱哄、低语、演讲等等)发出,频率都是不同的。
正因为不是一个一个音素地听辨,所以知觉语言才如此轻松,双语者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轻松的,否则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就不会连贯。大脑在听辨语音时具有类别性,即在毫无觉察时(不经意间)自动将声音归到不同的类型中,同时保留产生意义的语音组合,过滤非意义的声音组合。
对于大脑的这种声音归类机制,心理学家都作了一些实验,来描述这种大脑机制。Lisker和Abramson(1970:563-567)的实验证实了大脑相关神经能够自动对声音进行分类。这两位学者运用计算机产生由一个双唇闭塞辅音(这个音听起来既像[b]又像[p])紧接着一个“ah”音组成的人工言语声音。我们知道,[b]和[p]这两个辅音具有很多的相同属性,只是在嗓音启动的时候时间上有所不同。嗓音启动时间(Volce Onset Time,简称VOT)指的是在辅音发出后多久声襞(vocal fold)开始震动。VOT的负值说明声带震动是在声音释放之前。Lisker和Abramson利用计算机把VOT值控制在-0.15秒到+0.15秒之间,结果产生了31个音节。当他们把这些音节呈现给被试时,被试只听出了两个音,即“ba”和“pa”。被试的分类是,VOT值小于或者等于+0.03秒的音被试都听成了“ba”,而其它VOT值大于+0.03秒的音节被试则听成了“pa”,对于分界线两边的音节被试说不出区别。在被试的听辨中,VOT值分别是-0.10和-0.05的音节没有什么两样,而两个在VOT上相似却分布在分界线两边的音节(如VOT值是0.00和0.05的音节),所有被试都认作是不同的音节:“ba”和“pa”。
这个实验说明了大脑在进行语言知觉时。只是自动注意了有意义的声音而忽视了其它无意义的声音。这个结论描述了语音知觉的神经机制,所谓“自动注意有意义的声音”和自动“忽视无意义的声音”其实就是“神经认知协同机制,而上文Miller的实验所证明的‘言语是连续的说明了语言是可以通过知觉进行协同的,Miller所证明的另一个结论‘单个的音节会因为上下文而听起来有所不同则说明了语言知觉协同功能的多样性”。大脑神经的这种语言知觉协同功能既是一种语言本能,也是一种智力本能。
(2)语言知觉不仅仅依赖于语音,而且还依赖于视觉。Massaro和Cohen所做的实验就证实了这一点。两位研究者研究了[b]和[p]这两个只是在清晰度上有区别的闭塞辅音的类别性知觉。研究者让被试听到9个计算机合成的音节,根据声音合成属性从清晰的“ba”到清晰的“da”排列。在“中性”条件下,被试只能听到声音,没有视觉信息,而在其它两个条件下,被试既能听到声音又能获得视觉信息的帮助:被试会看到一个没有出声音但与磁带声音同步作出“ba”或者“da”发音模样的人。当磁带发出“da”这个声音而发音模样的人发出“ha”时,被试却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差别。但是,讲话人看上去在讲什么确实影响了被试所听到的内容,在相对“中性”条件下,在知觉“ba”到“da”系列中间的音节时,录影带中发音模样的人的口型会使知觉产生细微差异。这显然说明了视觉线索影响了声音的知觉。
视觉影响语言知觉进而可以描绘成一种情景效应。我们在这里提及几个实验,可以证明语言知觉的情景效应。
首先,Warren(1970:392-393)和Warren&Obusek给被试听一个句子的录音,这个句子是:
The state governors met with their respective legilatures convening in the capital city,
句中☆处被咳嗽声音掩盖,所占时间为120毫秒。在20个被试中只有一个报告了所缺少的声音被咳嗽声音所掩盖,但是并不能确定咳嗽声音的位置,其余19位被试证实了音素复位效应(phoneme restoration effect)的存在。这说明了在一定的情景效应条件下人们能够“听见”根本不存在的音素,这意味着在语言知觉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其它的语言信息的预测来回复缺省的音素。而所谓“其它语言信息”就是指情景效应。
其次,Marslen-Wilson和Welsh作了一个“跟踪”言语的实验。这个实验要求被试大声重复听过的内容,研究者呈现给被试的言语有所变化,比如使用cigaresh这个假想词,研究者发现被试在大声重复时,往往会把所改变的形式恢复过来,例如把cigaresh这个假想词恢复为cigarette,这是因为这个词前面存在一个高度相关的上下文语境:Still, he wanted to smoke a——。这说明听者或者读者会根据上下文语境来预测后面的词语。
(3)上述几个实验证明,人脑中存在着一种自动协调神经,能够通过语音和视觉进行语言知觉,以概念(意义)为表征形式,形成单一语言之内和双种(甚至多种)语言之间的表述转换机制,从而实现概念(意义)和语言表征之间互译。概念和单语之间的转换机制同概念和双语之间的转换,其原理是一样的。在道理上,前者要比后者容易,不过对于大脑双语神经很早被激活的双语者来说,这个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这几个实验同时也印证了Weinreich对双语的区分,“双语共存”、“双语复合”和“双语依存”都是心理表征和语言表征之间相互转换的形式,所不同的是,转换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双语共存”是两套平行的转换机制;“双语复合”是一套心理表征对应两套语言表征;“双语依存”是一套心理表征通过第一语言表征过渡到第二语言表征。但它们都是以语言知觉为前提,以认知心理的一般性特征为基础。这三种双语情况反映了不同的双
语思维水平:“双语共存”者的思维水平最高,因为他(她)有两套概念体系和两套语言表述系统;“双语复合”者次之,因为他(她)只有一套概念体系,但有两套表述这个概念体系的语言系统;相比之下,“双语依存”者的思维水平最低,因为他(她)的第二语言表述系统必须通过其第一语言系统作为中介才能进行表述。
2上述实验固然证明了人脑中的确存在一种自动调节包括双语活动在内的一切言语活动的神经机制,但并没有具体描述这种神经机制具体工作的情形,因为大脑就是一个“黑箱”,其机构十分复杂,现有的科学水平和科学手段尚不能精确地描述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在一定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一些解释这种神经机制工作原理的理论。心理模块理论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机制。
(1)模块理论是基于认知系统功能作用差异提出来的,强调不同心理区间的不同功能。所谓“模块”指的是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它具有推理机制,并且所接触的背景知识受到认知结构一般特点的制约。模块理论自提出以来不断有人发展它,也不断有人批评它,但是至今影响最大的还是Fodor的模块理论。
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上,Fodor的心理模块理论在其《心理模块性》(一书中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来了。心理模块理论遵循的是这样逻辑:“行为是有组织的,但行为组织仅仅是派生出来的;行为的结构依赖心理的结构就如同结果依赖原因一样。……采用那些提出并说明心理结构的学说来对行为组织标准进行心理学解释。”各种心理模块相互作用,保持协调,取得一致,最终完成整个认知过程。那么,双语活动中的心理模块又是如何转换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从心理哲学的层面对心理结构的描述。第一,新笛卡儿主义把心理结构看成知识结构,其核心思想是“本能的(心理)结构是丰富的……并且是各种各样的……各种(认知)范围的发展是一致的,而(心理的)先天状态的本能特性是相似的、无差别的——这种假设可以从Skinner到Piaget的研究中找到依据(尽管他们在其它很多方面观点不同)”。第二,官能心理学中的“水平”观把心理结构看作水平官能意义的功能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认知加工体现了记忆、想象、注意、感觉、知觉等这类官能的相互作用;而每个这类加工的特点取决于参与该加工的官能特定组合。但是,心理状态的特点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主观对象:而官能则被认为从一个思维主题到另一个主题不发生变化。”第三,官能心理学中“垂直”观把心理结构看成是垂直官能意义的功能结构。“垂直官能是范围特异性的、由遗传决定的、与不同神经结构相联系的、而且在计算上是自主的。”第四,联想主义的心理结构。双语活动中的心理模块应该属于这一种分类,所以另作一自然段讨论。
(2)我们探讨心理结构就是为了弄清楚认知能力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联想主义认为,官能的存在就像现象论认为桌椅板凳的存在那样。也就是说,官能这个十分心智的现象是由某些更基本的实体组成,实体之间相互连接形成内在的心理机制,然后这种心理机制又同外界对象产生连接,从而构成一个活动的整体。Fodor把以下内容归纳为认知理论中参与联想的要素:“第一,心理结构赖以建立的一系列元素。如反射是那些认为心理结构就是行为结构的联想主义者所喜欢的元素,而观念则是那些认为心理结构就是心理结构上的联想主义者所喜欢的元素。第二,元素之间初步的联想关系(仅仅是‘初步的,因为可联想的特性就保存在联想之中;联想规律可以应用于那些本身就是联想产物的观念,反射,于是产生出基本心理结构与复杂心理结构之间的区分)。第三,联想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机体经验特性决定了哪些观念可以联想在一起或者(类似地)哪些条件反射可以形成。第四,心理结构即它们之间的联想关系的理论关联参数。例如联想关系可以具有不同的力度,反射具有不同的操作水平。”Fodor谈到的这四点可以说描绘了联想的心理内部机制——把心理事件之间的同时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机制,而这种同时性关系反映了环境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么,心理事件之间的同时性是如何同环境事件之间产生联系的呢?Fodor认为“形成联想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经验特征就是刺激之间的时空接近性的相对频率。例如,观念可以根据它所涉及的事物的时空接近性而联想到一起,反映可以根据辨别刺激与强化刺激之间的时空接近性而形成条件反映等等。”这样,刺激、观念、接近性交织在一起,连接了心理事件和环境事件,其中观念起着指向性的作用。可见,联想主义的本质通过一连串观念的作用,环境事件成为心理中的副本,这样联想主义就成为一种在心理和行为中产生一系列冗余度的机制,这些冗余度反映了环境中的一系列冗余度。
以上的分析旨在说明,心理结构具有区域性和模块性,它们各司其职,并且同环境事件保持密切联系。双语转换的心理机制就是基于心理结构的区域性和模块性的,而心理结构的区域性和模块性一方面使双语有可能存在于人的大脑,另一方面,心理结构中区域性和模块性的不同功能又同语言交际功能连接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双语转换发生的心理条件。
(3)再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认知机制进行功能性分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也就知道了双语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双语者的思维优于单语者的心理学依据。我们知道,认知心理的一切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操纵装置(symbol-manipulating devices),这里的“操纵”暗含着心理功能,而“装置”则暗含着心理模块。这样,Fodor(1983:39)建议用三分法对心理功能进行分类,区分出传感器、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同时,Fodor也承认。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区分,因为现有的认知理论无法穷尽全部心理机制及其功能。Fodor指出。“输入系统的功能是让信息进入到中枢加工器;输入系统通过对心理表征的编码来为中枢机制提供操作范围,它们是传感器的输出与中枢认知机制的中介。然而,这并不是说输入系统将传感器提供的表征翻译成中枢编码下的表征。恰恰相反,翻译保留了信息的内容。而输入系统进行的计算却不具有那样的特点。传感器的输入通常可以解释为描述了机体‘体表上刺激的分布情况。而输入系统所传输的表征通常可以解释为归纳了世界上的物体的排列特性。”Fodor在这里简要地描述了三个相对独立心理功能在进行认知处理时相互协调的作用原理。可以看出它们明确显示出了心理结构的模块性,所以接下来,Fodor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心理结构的模块性(modularity)。我们把Fodor的论述高度概括如下。
首先,Fodor首先强调心理结构具有模块性,而不同的模块又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由不同的系统组成。不同的系统就是不同的模块(module),不同的模块具有不同的区分性特征,例如,有的是语言系统,有的是听觉系统,还有的是视觉系统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Fodor
的心理结构的模块性与生成语法中的模块性是不同的。后者指的是语言本身的系统,而不是心理结构,强调的是语言结构中的管辖与约束关系,称为管辖与约束理论。
其次,Fodor描述了心理模块的工作原理。Fodor认为,外界的信息首先经过传感器,把信息转变成不同功能的模块能够处理的形式,几乎在这同一个时间每个模块又以中枢系统适应的形式输出信息。注意,这里所说的“以中枢系统适应的形式输出信息”表示,不同的模块在输出信息时所采用的形式是相同的,以便同中枢系统的工作环境保持协同状态。
再次,Fodor继续描述了心理模块的工作特征:第一,各个心理模块具有固定的神经结构;第二,每个心理模块都具有区分性的特征,即具有区别于其它模块的特征;第三,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速度是瞬间的,其计算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第四,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强制的,并不是可要可不要的环节;第五,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自动的;第六,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自主的,也就是说,心理模块自身就可以完成信息运演的过程,所谓传感器和中枢系统是信息的通道,它们并不承担信息运演本身;第七,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受刺激驱动的,外界的刺激相当于给心理模块“提出问题”,然后心理模块再去“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第八,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按照自下而上的处理程序进行的;第九,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时对中央认知目标不敏感;第十,心理模块对信息的处理是封闭式的。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只有上述10个特征同时具备,心理的结构的模块性才能形成,心理模块才能实施各自的功能:另一方面,每一个心理模块只能实施它自己独特的功能,对于和它的功能无关的信息则“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即对无关信息非常不敏感。这个现象就解释了为什么心理模块运演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为什么心理模块运演的自动化程度是如此之高。于是,Fodor干脆把心理结构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天赋模块,一个是实施演绎等心理过程的非模块性中央处理层次。这个简单的分类似乎同Frankish把人的心智分成两个层面的结构是一样的:基本心智(basie mind)和超心智(supermind)。
总之,无论怎么确定心理结构的模块性。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应该看到母语和第二语言的获得也是心智活动的一种结果,是具有心智机制的,这种机制就是各司其职的心智模块相互协调、共同参与复杂的思维活动。
(4)我们之所以把心理模块之间的协同看成是双语活动的心理转换机制,是因为心理模块在第二语言(包括母语)的获得、两种语言的脑分布以及基于这种分布所形成的语言认知等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语言的产生到语言的各种活动也都能在心智中找到相应的模块,处理语言模块的独特性表现在它的处理形式的表征,而语言输入和输出以及中枢处理等的表征都是有模块性,所以心智不仅要确定这些模块本身,还要运用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确定模块之间连通的途径,这说明不同的模块在结构上是并列的。发现了这些规律有助于探索和了解语言心智进化过程,从而达到解释双语活动的心理转换机制的目的。
关于心理模块性,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它的定性问题。Fodor认为语言感知就是理解言语或者文字意思的过程,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活动,因此心理模块是一个信息封闭的认知机制,具有天赋性;但Jaekendoff并不同意Fodor的看法,甚至认为Fodor是错误的。Jackendoff(2002:164-170)指出,语言感知模块并不具有天赋性,语言感知之所以能够快速、自动进行,是因为一个人对所习得的语言规则十分熟悉,所以语言感知模块性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属于天赋的应该是普遍语法中的“Chomskian”模块,这个模块通过语法规则激活语言处理器(language processor)中的天赋因素。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不然,他们只是说话的角度不一样。如果强调语言的神经机制,那么两者就一致了,因为即便是Jackendoff所说的语言问题也是需要神经依托的,否则语言的表述机制就成了“空中楼阁”。既然承认了语言问题的神经依托,那么就意味着承认了语言问题的天赋性。所以,笔者在此拿出看似与Fodor“相反”的观点,其实是为了反正Fodor心理模块的天赋性,从而说明双语活动中心理转换机制的科学性:双语者能够运用自如地进行两种语言的转换,这正是心理模块天赋性的表现。
三、讨论与结论
1本文从讨论双语的定义入手,以语言知觉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利用心理模块理论和一些心理实验结论,论述了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概括起来就是:(1)双语现象在本质上同单语现象相同,也具有语言知觉的一般特征,只是心理转换机制较单语复杂得多;(2)人脑各个语言神经之间具有自动协调的功能,能够协调人的语音和视觉进行语言知觉,实现概念(意义)和语言(单语和双语)之间的转换。因此,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主要指的是双语(语言表征)及其概念(心理表征)体系之间的互译,有时也涉及到两种语言表征之间的互译,分别表现为“双语共存”、“双语复合”和“双语依存”三种形式:(3)人脑通过语言知觉而获得的概念在一定的外界刺激作用下,可以根据它所涉及的事物的时空接近性而联想到一起,从而连接了心理事件和环境事件,达到双语(或单语)的表述目的;(4)心理模块作为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是一个信息封闭的认知机制,具有天赋性。
2以上四点对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的描述,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它并不是抽象得不可捉摸。我们通过对一些双语活动的分析,就可以感知到这种机制的存在。我们知道,翻译是典型的双语认知活动。对此,Bell(1991)对翻译的认知心理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认为翻译:(1)是人类信息处理这个普遍现象中的特殊案例;(2)应该在信息处理的心理学范畴内将其模式化;(3)既发生在短期记忆又发生在长期记忆里,并需要通过源语里的篇章解码装置和目的语里的篇章编码装置相互作用,又需要经过与语言无关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阶段;(4)不管是在对进来信号的分析过程中,还是在对离去信号的合成过程中,翻译过程都在小句的语言层次上运行;(5)在处理语篇时按照自下而上(bottom-up)与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进行,并通过串联(cascaded)和相互作用(interaetive)的操作方式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一个阶段里的分析与合成要在下一个阶段被激活和可能修正后才能完成。
Bell虽然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谈翻译的认知过程。但是其认知这一属性与笔者所论述的双语活动中的心理转换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Bell的翻译“模式化”就包含了笔者所说的心理模块及其功能;Bell认为翻译“既发生在短期记忆又发生在长期记忆里”则强调了翻译的认知心理过程;Bell谈到翻译涉及“篇章解码装置和目的语里的篇章编码装置”、“小句的语言层次上运行”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语篇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双语活动心理转换机制的具体内容;最后,Bell说到的“串联和相互作用的操作方式”则突出了心理模块之间协同工作的基本原理。
总之,双语活动(如翻译)首先是通过心理转换机制来实现两种语言概念系统的转换,然后在概念系统转换的基础上达到两种语码系统转换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前一个阶段称为内在转换,它是转换的过程;把后一个阶段称为外在转换,它是转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