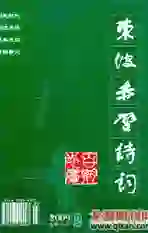用形象和画面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2009-04-27吴闻章
吴闻章
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描述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通过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来表达、寄托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艺术形象越典型,生活画面越丰富,则感染力越强,作者寄托的情感和思想就越能影响读者,从而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本身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致敏·考茨基》)。其意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来实现的。
作为传统诗词的创作,也应该这样要求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传统诗词的创作既然属于文艺创作,那自然应遵循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即毫无疑问地把塑造艺术形象和描述生活画面、场景作为根本任务来追求和完成。当然,短短的几句诗词不可能塑造出完整丰满的文学形象和描绘出绚丽多彩的生活场景,但写人物外形或性格的一个侧面,描绘生活中的一个角落和一朵浪花,同样算是按这一艺术规律来创作的。所以,古今中外,关于诗歌创作的任务和手法就有许多表述各异而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论述。如中国古代的诗论家,主张写诗要用“赋、比、兴”;宋代苏轼称赞唐代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欧洲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出,“诗歌就像图画”;毛泽东主张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而近人钱锺书则批评“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诗词创作必须遵循艺术规律,用形象和画面来表达思想和感情,而不能用“讲道理,发议论”来进行艺术创作。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一看老诗人王英写的一组称赞我国改革开放的七言绝句,则可以看出,王英在创作中就遵循了“用形象和画面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正确路子,从而获得了比较好的艺术效果。在《李家渡》这首诗中,他抓住了两个艺术要素:艄公和摆渡的船。“艄公”,“昔日瘦根雕”,言其贫困和可怜,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下代”艄公却今非昔比——“革履西装”了,生活自然也富裕了起来。这是写人,写形象。“驾起风帆风送渡”,旅客“南来北往”,这又是今非昔比,一派欢快繁荣的画面。这样,作者想要歌颂的改革开放,不是用“讲道理,发议论”的“道学”口吻去写,而是通过“李家渡”今昔艄公的形象对比、渡口欢快热闹的场面描述这两大因素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作者的“倾向”是通过艄公形象和渡口场景“流露”出来的。试想,如果作者不借助形象和场景,而是用几句概念化的语言去称赞改革开放,能达到这种令人愉悦的艺术效果吗?显然不能。
同理,《栗树垸变迁》一首,作者也是着意用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来写改革开放后科技给农村带来的实惠和变化。“栗树婆姨无育能,徒生大叶盖穷村”,这里,作者把不结果只会长叶的栗树比喻成“无育能”的“栗树婆姨”,然后笔势一转,因为“科研嫁接施新技”,“栗树婆姨”终于有“育能”了:“金果累累挂满林”。在这样一幅丰收的画面中,寄托了诗人的喜悦之情,进而使人联想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论断。四句诗,有形象,有画面,情在诗中,意在诗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英不是自发而是自觉地运用艺术规律进行创作。除上述的用具体的人的形象、生活画面,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来写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外,作者还有意识地把一些抽象的、固态的内容拟人化、形象化。如将“栗树”比拟成“栗树婆姨”,把“树”变成“人”(《栗树垸变迁》);说艄公贫困羸弱,不直说贫弱,而用“瘦根雕”喻之(《李家渡》),则把“人”变成了“树”。在《村长夜读》中,作者甚至把非常抽象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比喻成“科鸟”,变抽象为具体化、形象化。尽管作者的这种努力并非完美(如把“科学发展观”喻为“科鸟”有嫌牵强),但这种自觉用形象化、场景化的努力却是对头的,值得提倡。
最后要说及一点的是,现在有些作者写诗填词,喜欢通篇采用抽象的、议论的、说理的语言。这是诗词创作中的大忌;用这种语言写出来的诗词,很难成为好作品。笔者之所以评介王英的这一组诗,就在于说明,我们在用诗词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观点、倾向时,要尽量避免“以议论入诗”、“以说理入诗”,而要转一个弯,借助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来完成一我们要的是“本身流露”,而不要“特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