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诗神在黑铁上发烫”
2009-04-26北塔
北 塔
在21世纪初重读骆一禾的诗,我更加强烈而明确地认识到了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精神和艺术,是的,骆一禾是太“80年代”了。他的生命终止于那个年代的最后一年,他没有来得及在时代的分界岭上转身,没有沾染90年代的气息。假如他的生命跨越了1989年,他是否会像有些青年诗人一样迅速转变?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不太可能,至少会延宕个三五年。因为80年代的诗歌,无论其价值标准还是表现方式,都让过来人无比留恋,也确实有值得留恋之处。我们现在连90年代都过完了,可以从时代差异的角度来谈论骆一禾的向度了。
骆一禾的思与诗具有非常明显的神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神话写作。他认为,诗人写作相当于上帝创世,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创造另一个世界,当然,这两个世界是相互叠加并渗透的。他时不时会把自己神化——化身为神说话。他在诗论《火光》一文中阐释道:“《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里,有一些段落带有‘神说的记号,创世行为以‘神说来给标志揭示,万物万灵不仅长在天空、大地、海洋,也是长在‘神说里的,诗歌作为‘是的性质在此可以见出。”神不仅用手创造世界万物,还用嘴说出自己的创造,包括创造的过程(说与做同步进行)和结果(给万物命名)。骆一禾认为,“说”就是神的诗歌行为。存在主义哲学之所以把诗歌定义为人类精神栖息的家园,就是因为诗与世的这种共生关系。他们把“泰初有道”的“道”解释为“言”。诗人写作等同或者说近似于神明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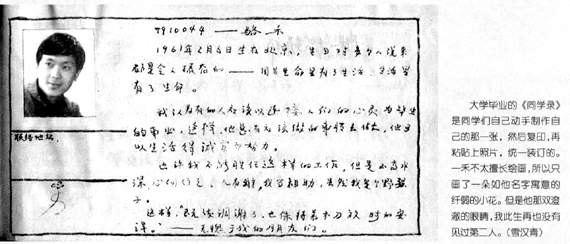
骆一禾向往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那里,神界与人间并不老死不相往来,神固然高高在上,但也时不时化身为人,前来人间活动甚至鬼混。到了现代,神依然没有消失,尤其存在于诗歌和诗人,只不过可能更加隐性了,有了更多的变形。诗人的任务是充分利用自身与神相通的优势,发现、挖掘并弘扬自身的神性,替神说话;当然,更加本质的是,那是神让你替他说话,主动权不在你,而在神。诗人所能做的,是等待,等待神来附体;跟语言一起等待,因为语言是诗的母体。在日常生活中,诗人与诗可能处于分离状态,但一旦神到来,两者就会合二为一,犹如卵子和精子相遇而共造生命的胚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骆一禾一再强调,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消极行为(这种说法来自济慈的“客观消极”说)。如果说诗人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话,那也就是迎候,在迎候时人扮神装,放弃自己作为人的一切,学着神的步态和语态,像原始宗教里跳大神的巫师巫婆一样,祈祷着吁请神早早进入自己,激发自己的灵感、记忆和舌头,从而进入诗歌创作的忘我状态:
我如巨人
有神明那样的饥渴
却又浑身滋生陶土 隐藏着你
铸造着飞行的胎体 那美和泥炭的胚子
那呼之欲出的 那旋流的时光 性灵与胸怀
你祝福于我 降生于我
——《曙光三女神》
骆一禾犹如通灵者,他的写作是与神对话,或者潜对话。如《和平神祇》和《曙光三女神》(颂歌)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只能与人对话,神是缺席的。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对话只能是痛苦的倾诉和吁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人们/都曾经衷心地感觉到这样的痛苦/”(《对话》)。没有神的生活不可能快乐和幸福,哪怕是圣人,也必然是可怜的苦难的。为了安慰自己、麻醉自己,人们学会了自我蒙骗,假装说自己看见了上帝(犹如皇帝的新装),或看见了真理(仿佛有了真理我们就可以不要上帝,仿佛真理可以在没有上帝——信仰的情况下获取)。圣人与凡人都没看见神,所不同的只是:圣人不原意自欺欺人,说出了自己的痛苦。
在近代世界,神之所以很少光临人间,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忘恩和狂妄。这世界的主人本来是神,是神借给人类使用的——“世界,你这借自神明的台阶”(《月亮》)。人类对自身赖于生存的这个世界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随着自身能力和信心的加强,人类渐渐地自我膨胀起来,以为自己可以与神明分庭抗礼,以为自己从房客升格成了房东,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骆一禾认为,人性得到过度的开发,必然导致神性的削弱乃至丧失,这样的文明之路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下行着多少大国/和它们开发过度的人性与地方”(《月亮》)。这一观念来自尼采,他反对人性对神性的戕害,认为基督教文明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骆一禾希望诗人能保持甚至加强自己与神明的关系,从而阻止文明之路向下的趋势。和海子、王家新等人一样,他更青睐的精神方向是“北方”,“因为就精神坐标而言,北就是向上。”(陈超《骆一禾:敲响的火在倒下来……》)。但是,环顾周遭,人性的加与神性的减这种趋势并没有因为诗人堂吉诃德似的逆向努力而停止,于是,诗人只有给自己设置一片精神自留地,那就是海子和骆一禾以及其他大量诗人诗中曾经爆发的“麦地”,毫无疑问,“麦地有神,麦地有神/就像我们盛开花朵”。(《麦地-致乡土中国》)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叙,还不如说是对乌托邦的呼吁。骆一禾的乌托邦想像始终具有回到过去的冲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人类因为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而痛苦时,就会“眼望着家乡”。正因此,程光炜说他的“诗歌主题具有某种怀旧性”(《中国当代诗歌史》),而陈超说,他的诗歌具有“缅怀的力量”。(《骆一禾:敲响的火在倒下来……》)
我们盼望中的家乡显然不在这里,而在“在那里,在远方,在彼岸,在过去。它的质地是黄金,起码是白银。而我们身处的是黑铁时代,诗歌和神灵被放逐了,如果她们不识时务,非得要留下来,就逃避不了被迫害的命运,领受炮烙之酷刑——硬邦邦的黑铁烧得通红,诗神被剥光了,她那柔软而娇嫩的肌肤……”
具有神性思维的诗人往往是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作为坚定得有点狂热甚至顽固的理想主义者,骆一禾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向上、向外,一直没有低下头来,对周围日常生活的兴趣也始终提不起来。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描写他缺乏耐心,却乐于放纵他的想像,越是放纵,他的想像力就越强、越野,神的视角和速度使他的想象更加超凡,他思维的走动简直是漫无涯际,古今中外,随时往还。这与90年代许多诗人的看法和写法迥然不同,他所不屑的被后者奉若法宝,后者注重个人日常经验的捕捉,尤其是生活细节的处理、小情小调的再现,与时代的纽带加强了,现实氛围浓烈了。但在骆一禾看来,这些可能都属于鸡毛蒜皮的范畴。他的高明和缺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而,骆一禾的诗歌并没有因为远离世态而让我们感到隔膜、冷漠或枯燥、空洞,他拉近读者的方法不是共同经验的还原,而是在字里行间投射了强烈的情感和痛苦的思索,回荡着熊熊的生命的烈火,读者的回应不是通过起用现实生活的联想,而是通过动用超现实的幻想,读者的心灵很容易被他的诗歌燃烧,从而产生共鸣,从而觉得他那些来自遥不可及的地方的意象也是亲切的、温暖的,这就是情感的力量、移情的作用,也是人情优于世态的证据。
骆一禾最热衷于“火”及其相关的意象,这是他的激情的图腾,也是他的旺盛生命力的表征。有人为了强调他跟海子的区别,牵强地说“海子的诗可用灼热一词来形容其风格,而骆一禾的诗始终是沉静的智慧的”。(王干《诗的生命》)他的作品中固然加入了智慧的因素,但并没有达到沉静的程度,并没有减弱激情。海子的写作资源主要是青春激情、单纯信仰和诗歌情结,确实是激情大于理性;但骆一禾并不是理性大于激情。跟闻一多一样,他的理性和激情都是高涨的,而且相互激荡得更加如火如荼。骆一禾的风格同样是灼热的,他的很多诗跟郭沫若的一样,不是写出来,而是“泄”出来的,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所不同的是,他的语言姿势更加内倾,他的能量释放法不是裂变,而是聚变。其实,在相当多的时候,骆一禾是任凭自己的激情自然流露,并没有考虑用什么瓶子去赋予形式。程光炜说他和海子、西川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作品结构和语言比较地对称和匀整。”(《中国当代诗歌史》)这是源于“理智说”的对他诗歌的进一步误读。在厚达近900页的《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版)中,除了个别早期练笔作品,有几首是对称和匀整的呢?
其实,骆一禾最崇尚的是生命诗学,确切地说,是“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美神》)。这种哲学因其以情感为本体,所以生命的特征大于哲学的特征,他反对“使诗成为哲学的象征而非生命的象征”(《春天》)。生命,跳荡的、深沉的、本能的,神在此,诗也在此,是自足的,同时也是施与的。但是,这种自足状态并不局限于或依附于人类或生物类,而是与整个宇宙尤其是精神宇宙(黑格尔意义上的)血肉相连的一种状态。唯其如此,它也是开放的,神人合一的。这生命是一团火,神火,也是鬼火,既能催生,也能毁灭;这是一团加速燃烧的火,海子和骆一禾的天才就被这团火烧成了诗歌,在过程中,他们始终抱着缪斯女神,一同领受火刑。他们苦于斯,也乐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