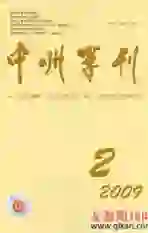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
2009-04-14胡全章
胡全章
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新小说创作如火山喷发,高潮迭起,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文坛与诗坛热闹非凡,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新派与旧派营垒分明。1903年的文学界,呈现出新小说创作一枝独秀,而报界、文坛和诗坛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关键词:1903;新小说;文学转型;年份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10-05
在中国近代史上,1903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是年,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的展开,《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的风行,章太炎著名的革命文章的发表和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的发生,使得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更加迅猛,影响乃至决定了此后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走向,使这一年“成为革命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同样是关键性的年份。是年,章太炎、刘师培、邹容、陈天华等革命派作家的重要著述的问世,不仅是政治思想界的大事,亦是文学界的大事,对中国近代文学的主题导向和发展趋势影响甚巨。是年,梁启超于1902年冬日点燃的“小说界革命”火炬迅速形成燎原之势。1903年,晚清小说界如火山进发,高潮迭起;新小说创作如雨后春笋,盛况空前。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新小说中成就最高的社会谴责小说,诸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金松岑《孽海花》等,均在这一年问世。小说界的热闹与繁华,亦伴随着报界、语言文字学界、诗坛和文坛的喧哗与躁动。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梁启超于1902年冬揭橥的“小说界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禁锢的小说观念,唤起了晚清一代新小说家的创作激情,成为新小说蓬勃发展的催化剂。时人对应运而生的“新小说”有着形象的描绘:“二十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扣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砣石乞;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1903年,新小说一纸风行,风光无限;一飞冲天,傲视文坛。
1903年的小说界可以开列出一长串耳熟能详的作品:5月,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文明小史》和《活地狱》在《绣像小说》连载;《胡雪岩外传》出版。6月,忧患余生《邻女语》在《绣像小说》连载。7月,陈天华《猛回头》刊于《湖南俗话报》;张肇桐《自有结婚》初编十回发行。8月,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等在《新小说》连载;刘鹗《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连载;苏曼殊译《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连载。9月,鲁迅译《月界旅行》出版;《空中飞艇》出版。10月,金松岑撰《孽海花》(前五回)在《江苏》刊载;鲁迅译《地底旅行》在《浙江潮》刊载。12月,林獬《玫瑰花》在《中国白话报》连载……新小说创作掀起了高潮。
李伯元的写作生涯并不始于1903年,此前已发表了《庚子国变弹词》这部“中国民众的受难史”和“中国反帝文学在弹词方面的最初一部书”。然而,真正使他“骤享大名”的则是那部引领了晚清社会谴责小说创作潮流的《官场现形记》。这部在新小说创作潮流中涌现的潮头性作品,不仅使李伯元坐上了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头把交椅,而且以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显示了“小说界革命”的实绩。其所开启的“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纠弹”的取材倾向和主题意向,“笔无藏锋”的讽刺艺术和“谴责”的基调,对晚清新小说创作有着覆盖性的影响。1903年,《绣像小说》创刊是小说界的一件大事。主编《绣像小说》是李伯元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作为继《新小说》之后创办的晚清最为重要的小说杂志之一,《绣像小说》从第一期起就表现出对“小说界革命”的主动回应。李伯元在主办《游戏报》时,曾公开声称“觉世之一道”是“游戏”,倡导的是游戏人生的态度。然而,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李伯元则声称“欧洲化民,多由小说,樽桑崛起,推波助澜”,强调自己编发小说的目标是“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这些话语几乎是梁启超新小说理论的一种翻版。是年,李氏重要代表作《文明小史》与《活地狱》自《绣像小说》第一期开始连载。“夙报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的李伯元,在“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的时代背景下,立下“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的写作誓言,试图在政治道路之外寻找一条以拯救“世道人心”而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
刘鹗《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连载,是1903年小说界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创获。这部被夏志清定位为中国的第一本游记体“抒情小说”和“政治小说”的旷世杰作,以丰富的思想意蕴、哭泣与醒世的创作意向和独特的文类价值。赋予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其富有深度的心理刻画、娴熟的限制叙事技巧和高超的结构艺术,均显示出作者艺术思维的超前性和戛戛独造的创新性。叙述人脱掉了传统小说家那件说故事的外衣,具备了现代抒情小说的质素,取得了近乎革命式的成就。相比之下,胡适誉之为“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的“前无古人”的“描写的技术”。尚属细枝末节问题。
1903年秋,吴趼人在《新小说》因缺乏高质量稿源而陷入困境之时援之以手,将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写情小说、笑话小说齐头并进,在《新小说》第八号推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新笑史》四种小说,成为《新小说》第一创作主力。吴趼人凭借《新小说》这一得天独厚的平台(“小说界革命”之旗帜),成就了其“小说界一时无两之巨子”的声誉。《痛史》是晚清历史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写的是宋元鼎革之际的历史故事,针对的却是晚清政治腐败、列强侵凌、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以“警世之文”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继《官场现形记》之后影响最大的社会谴责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谴责小说从揭露官场迅速扩大至批判整个社会黑暗现状。出于对处身其中的那个无法修补的现实世界的极度失望乃至绝望,晚清小说家努力表现出对这个丑恶世界的谴责与批判,而其秉持的价值标尺则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以拯救道德而达于救世救国,是中国传统文人奇特的政治假想,生活在20世纪初年的晚清新小说家依然没能摆脱传统文人的
道德救世情结。
1903年10月,金松岑所撰《孽海花》(六回)在《江苏》刊载,是为曾朴《孽海花》之前身。金松岑不仅为该著奠定了“以赛(金花)为骨,而作五十年来之政治小说”的创作题旨,而且与曾朴共同酌定了“其预定之六十回目”。金松岑所撰广告词称:“此书叙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党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至,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逸闻。”可见曾朴《孽海花》之内容纲要,已在“爱自由者”擘划之中。
同月,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的《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中译本《惨社会》刊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译著者将其打造成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革命小说,说明这种为我所用、著译参半的“豪杰译”依然盛行于晚清文学翻译界,20世纪初年的中国仍处在“循华文而失西义”的翻译时代。同月,周桂笙所译侦探小说《毒蛇圈》在《新小说》连载,吴趼人作评。周桂笙是晚清最早运用白话来翻译西洋文学的先驱者。是年,他被《新小说》社聘为“总译述”,与“总撰述”吴趼人一起成为《新小说》的台柱子和“当时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毒蛇圈》全用通俗晓畅的白话译成,且是我国最早的直译小说,这在“豪杰译”盛行的晚清文学翻译界显得尤为可贵。
是年,鲁迅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行世,虽然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社会影响,却是鲁迅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标志性作品。这两部科学小说的译介,既是鲁迅科学救国思想的体现,又是其正在形成的“文学救国”思想的具体实践。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对“科学小说”作了堪称经典的界定:“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间。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短短三十几个字,却从取材倾向、主题模式、结构特征和文体风格等四个基本侧面粗略地勾勒出了“科学小说”的类型特征。初出茅庐的周树人对“科学小说”类型特征的把握,远比同时代新小说批评家精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清小说的骤然繁荣是以政治为催化剂、以市场为扬声器。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宣传家创作小说是为了“觉世”而不大考虑“传世”,报人和职业小说家追求的是风行一时而不是流芳千古。政治和市场为“新小说”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却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其创作面貌。20世纪中国小说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困扰,幸与不幸都在历史的必然之中。
1903年,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是年,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用白话对国民进行政治思想启蒙和素质教育蔚然成风,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大量行世,蔚为大观;“言文合一”的时代呼声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统一语言”则成为时代赋予国语运动的一项新使命;“俗语之文学”不仅获得了与文言作品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目为文学进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晚清白话文运动以白话报刊为主阵地(载体),以白话文写作为主要手段(工具),迅速蔓延到白话教科书、白话告示、白话宣传品等,自然也包括白话小说、戏曲、通俗歌诗等文学体裁。而其宗旨和目标,则在开启民智乃至宣传民族民主革命。1903年创办的白话报刊有十多家:《中国白话报》(上海)、《宁波白话报》(上海)、《智群白话报》(上海)、《童子世界》(上海)、《绍兴白话报》(绍兴)、《湖南俗话报》(长沙)、《湖南时务白话报》(长沙)、《湖南演说通俗报》(长沙)、《俚语日报》(长沙)、《潮州白话报》(潮州)、《启蒙格致报》(北京)、《山西白话报》(太原)、《江西白话报》(日本)、《新白话报》(东京)等。此外,出版更早且坚持到本年的白话报尚有《白话报》(浙江)、《苏州白话报》(上海)、《杭州白话报》(上海)、《改良启蒙通俗报》(成都)、《启蒙画报》(北京)等。1903年的上海、江浙、湖南等地,白话报刊的创办已蔚然成风。
在众多的白话报刊中,林獬主持的《中国白话报》成就最著,影响最大,历时最久,且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最为进步,因而最具代表性。本年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一期,设有论说、历史、传记、新闻、时事问答、科学、实业、小说、戏曲、谈苑、选录等栏,几乎全是“白话道人”(林獬)所撰。这位用白话报来作革命宣传的第一人,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辞》中宣称“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将启蒙的眼光转向“干的各种实实在在、正正当当的事业”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不遗余力地鼓吹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林獬的白话文明白晓畅、浅显易懂、情感浓烈、大胆奔放、冷峭凌厉。作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林獬以白话为载体,以民族意识、民权意识、科学意识为主要内容对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效果明显,成绩卓著,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作了先导。
1903年,与白话文运动互为孪生兄弟的国语运动,已由“切音运动时期”进入“简字运动时期”,且在本年度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年,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伦从日本考察学制归来,正打算说服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行王照创制的《官话合声字母》和中国的“普通语”,不料尚未赴京就职就病死故里。国语运动的先驱者王照撰《挽吴汝伦》,痛悼这位支持国语运动的古文大师,是为公开发表的最早提出“国语”概念的文章。是年,张百熙、荣广、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把“官话”列入师范及高等小学课程,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音”。自此,国语运动的目标在原来的“普及教育”和“言文合一”基础上,又增加了“统一语言”的新使命。1903年,何风华等上书袁世凯,要求奏明公布官话字母,推广“国语”教育,提出设师范学院、立演说会、用官话字母出白话报和编白话书、劝民就学等具体措施,得到了袁氏的赞成和支持。此后,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相辅相成,各自独立行进了一段艰难的行程之后,最终在五四时期汇流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之下,形成了双潮合一之观,其轰腾澎湃之势已难以遏阻。
1903年,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撰写了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以饱蘸爱国热情之笔,一字一泪,一语一血,痛陈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亡国亡种就在眼前”的危急形势,指斥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以革命手段起而拯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产生强烈反响。激烈的思想配以通俗畅达的文字,使其成为革命派阵营的锐利武器,读来惊心动魄,怒发冲冠,极富鼓动性与感染力,其影响力“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
以《新小说》、《绣像小说》为代表的一批主要刊载白话小说的文艺期刊的出现,亦可视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年,致力于“小说界革命”事业和“新小说”创作实践的梁启超,开始用进化的观念审视各国文学史,对中国语言文学发展进化之大势作出了大胆断言: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日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
梁启超所持的文学进化史观和“俗语之文学”必将取代“古语之文学”、“俗语文体”必将被“凡百文章”普遍采用的语言文学发展观,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论,走在了时代前列。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和“白话文学正宗观”,在梁氏上述文字中已经呼之欲出。
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国语运动的蓬勃发展。白话与白话文学在清末民初的广泛运用与试验,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是时,白话文与“新文体”相辅而行,相互促进,极大地推动了文体改革。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因其对白话文合法性的大力肯定,在观念上开了风气;而大量的白话文创作实践,为语体文和现代汉语文学的形成试探了道路,积累了写作经验。不仅如此,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陶铸锻炼了领袖人才,培育了作家队伍,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一切,都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造成一种蓄势和铺垫。
1903年,文坛与诗坛亦不甘寂寞,政治思想倾向上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激战,语言、体式与风格上则有革新派与守旧派之纷争,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在这个群雄并起、山头众多、旗帜纷繁的末世与乱世,文坛与诗坛可谓众声喧哗。热闹非凡。乍看新旧营垒分明,难分轩轾,前路不明,实则新派旧派都有求新的倾向。新的文学因素在加速萌育、成长和组合,沿袭古范的文学亦悄然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自我调整以求延存,却终因恪守古范而走向式微。求新求变是这一社会文化剧变期文学界变迁之大势,不惟新派如此,旧派亦然;不独诗界、文界如是,小说界、词曲界、文论界乃至学术界亦然。
1903年,后期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伦在桐城老家溘然长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具有开放视野和实践精神的旧文坛领袖,置身西潮强势东渐的变革时代,抱定教育救国之宗旨,为了保存中学而力倡古文之学。由于他和一批笃旧的教育主管官员的努力,古文教育的传统和地位在日渐成为风气的新式学堂中得以维持,给古文留下一席生存之地。是年,这位执清末文坛之牛耳的古文大师的去世,预示着一线孤悬的古文事业前途难卜,其无可奈何走向式微的时代命运已经注定。
1903年,严复译《群学肄言》、《群几权界论》出版。作为颇受吴汝伦赏识的“译界泰斗”,严复“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而吴氏亦先后慨然为《天演论》和《原富》作序,对这位“雄于文”、“其书乃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后进奖掖有加。而今,桐城吴先生已归道山,严复只能喟然长叹:“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然而,这位“我国现世惟一之大著作家”本年行世的两大译著,已经走过了“一言而为天下法则”的时代,尽管其书稿因知名度高而稿酬特丰,销路亦很不错。梁启超先前指出的“文笔太务渊雅”、“一翻殆难索解”的弊病,限制了严译名著的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力。这一点严复自己心里也清楚:“购者未必能读其书,然必置案头,聊以立懂而已”。这位当年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如今已颇受落伍之讥。
1903年,梁启超继续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大量发表负载着新民救国使命的新体散文。然而,由于是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复由激进转向保守,尤其是游历美洲之后完全放弃了先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加之革命阵营中的大文豪章太炎、章士钊、刘师培等辈的崛起,这一切都使得其在本年度的“新文体”创作不似此前那么风靡。由于其在政治思想上未能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其文章感人之力亦随之大打折扣。尽管梁任公笔端依然具有绝大的魔力,黄遵宪所谓的“唯我独尊之概”犹存,却难再获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巨大威力。此后几年里,这位重又服膺保皇立宪事业的“天纵之文豪”,在与革命派诸文豪的对阵中已不占上风。
1903年,弱冠之年的刘师培在开封会试中落第,自此绝意科场,开始了革命宣传活动。是年,刘师培撰成《中国民族志》和《攘书》两著,署名“光汉”,标志着这匹黑马已搭乘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列车,在晚清文坛和学术界初露峥嵘。其政论文和述学之文,思想新颖,感情充沛,学贯古今,理融中外,言简意赅,精辟透彻,影响甚巨。刘师培的出现对于晚清文坛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倒不在于其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激烈派第一人”的激进姿态,甚至也不在于其寓政治批判于文化批判之中的深邃眼光和深远意绪,而是供其驱遣自如的骈文文体。刘师培的成名和对六朝文的大力弘扬,见证了这一古旧文体在近代中国仍能焕发出巨大活力。而骈文文体在此后不久的民初政坛、文坛和小说界蔚然成风,大放异彩,乃至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学景观,则是这一古老的文学体式幕落花凋之际一次哀感顽艳的回光返照。
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发表《序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而声名大震,而此后《苏报》案的发生,则使这位革命大文豪的盛名达到了巅峰。章氏《自定年谱》中对这段令人神旺的经历亦颇为自豪:“余驳康有为虽无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辈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的章太炎,1902年以后“文章渐变”。虽然其言论常常站在文体和文风革新者的对立面,对突破传统形式的作家严加痛斥,对梁启超的“报章体”和严复的译著文章均不吝讥刺,然而,章氏此期的文风确有明显变化。他在1903年那段峥嵘岁月里所写下的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代表的战斗的文章,凸显出以内容为重而不再刻意模仿的行文祈向,文风和文辞方面亦表现出锐利畅达和渐趋通俗的特征。这是章太炎顺应时势之需而对古奥晦涩文风作出的调整。尽管章氏后来对此类文章表示不满,认为它们“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然而在当时却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影响甚巨。
1903年5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撰《革命军》一书由柳亚子等革命党人集资交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立即轰动全国,风行海内外。它以火一样的热情,痛快犀利的笔调,浅近通俗的文字,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政府的暴虐和媚外,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排满,以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惊醒了沉睡的国人。《革命军》的问世,不仅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特出的意义——“它实现了宣传性与文学性的融合,建立起了新的宣传性散文的典范”。
1903年的诗坛,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辟的“饮冰室诗话”栏目里继续弹奏着“诗界革命”的主旋律,“诗界潮音集”
园地的新体诗试验尚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宗唐、宗宋、宗汉魏六朝等等,一面面复古的旗帜依然在诗坛高高飘扬,而且占据当时诗坛的主要位置。在旧派诗人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不墨守盛唐”相标榜,以宋诗为主要学古方向的“同光体”诗人。其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其中,陈三立不仅是该诗派甚或是整个旧诗坛的领军人物,陈衍则是“同光体”诗派的鼓吹者、总结者和诗论家。“诗界革命”的提出和兴起,虽然将“同光体”诗人推到了“旧派”的位置上,却未能动摇其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他们在“不墨守盛唐”的诗学旗帜下,继承宋诗派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传统,力图在大厦将倾、变风变雅的时代,循着宋诗人开创的“点化陈腐”、“以故为新”的变通之路,为旧体诗歌的生存与发展开疆辟域。
1903年,新小说在文学界一枝独秀,独领风骚。而透过繁荣热闹的文坛表象,深入新小说阵营内部,则可发现其所呈现出的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驳杂局面与多元发展态势。且不说晚清小说家在政治思想倾向的保守、改良与革命之分,其小说类型分划、艺术旨趣与创作风格亦异彩纷呈,实非一个“谴责小说”所能囊括。1903年的报界亦热闹非凡,《苏报》、《新民丛报》等文言大报不仅充当着革命党和维新派的舆论喉舌,而且成为孕育新文学的温床。白话报刊和白话文著述及白话文学作品的大量行世,使得晚清白话文运动在本年度蓬勃发展。“统一语言”目标的提出,则是国语运动取得新进展的标志。是年,桐城派古文宗师吴汝伦的谢世,古文翻译大师严复《群学肄言》、《群几权界论》的问世,新民师梁启超“新文体”的继续行世,骈文大家刘师培以鼓吹革命而名世,革命大文豪章太炎著名的革命文章的骇世,邹容《革命军》和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的惊世,都使得本年度的文坛沸沸扬扬,颇不寂寞。1903年的诗坛,同样显示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态势。“同光体”的诗坛霸主地位虽未被撼动,但“诗界革命”的开展将其推到了“旧派”的位置,相对于借助现代报刊而热热闹闹开展的新体诗试验,传媒视野中的旧诗坛反而显得相对冷落。1903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的文学因素在加速萌育、成长和重新组合,求新求变成为文学界变迁之大势。
责任编辑: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