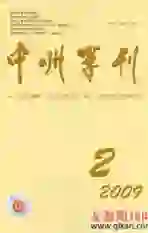上博楚简道家文献《恒先》篇通解及章节拟构
2009-04-14顺真
顺 真
摘要:《恒先》篇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中的一篇,属道家文献。许多学者深研此文,会通大义,并深入阐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之重要地位。但其文本之解读,成果并不完整。《恒先》共一十三简,原文并未分章,然其结构井然有序,今通解其意,分出章节,以便学界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恒先;或;道;名
中图分类号:B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51-07
上博楚简道家文献《恒先》篇一经公布,就引起学界更为广泛的注意,许多学者深研此文,会通大义,并深入阐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之重要地位。但对文本之解读,必是一项艰巨之工作,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由于文字古奥,说理又相当玄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基本的认识。”今不揣冒昧,略述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简文通解
1、第一部分通解
1.1恒先无有朴、静、虚——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马王堆帛书《道原》曰:“恒先之初,迥(洞)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混混)梦梦,未有明晦。”多解恒先为道之别名,甚确。然恒先构词之法、恒先用词之意为何?《老子》四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恒先者,恒之先也,亦如帝之先。帝谓上帝,然老子曰帝先;恒为恒常,此篇曰恒先,皆为哲学构词中否定之法。帝先超越于帝,恒先超越于恒。《老子》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道乃体验境界,浑然直观,当体冥会,故本无名。出离此境,宣告他人,故可命名。然名是假名,境乃真境,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即无名。孔子《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知不止则不能得定,欲得知之止,必以明“无名”之理为其先导。《庄子‘齐物论》曰:“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老子》帝先之语,本篇恒先之名,皆本无语,皆本无名。
恒先以下断句,多以“恒先无有”为一句,且以为“恒先无有”即庄子《天下》所言之“常无有”。愚意当以“恒先无有朴、静、虚”为一句。朴、静、虚,皆为老子之用语。《老子》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老子》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朴、静、虚,既为道体之本然,亦为体道者体验之境界。然一为文字,久必成病,闻之者或空谈朴朴朴,或乱解静静静,或妄论虚虚虚,故使道真之本、复命之境,全成非真之糟粕、戏论之臆语,故曰“恒先无有朴、静、虚”,意为恒先并无(空言所说)朴、静、虚三者,朴、静、虚乃超越语言之存在,唯体验而能知;故无可奈何,接下而言“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即有朴亦是太朴,有静亦是太静,有虚亦是太虚。亦如若空言帝帝帝,老子乃曰“帝先”;若空言恒恒恒,本篇乃曰“恒先”。故为去空言朴静虚之病,亦唯“强为之名曰”——“太朴”、“太静”、“太虚”。如是断句,则前后意贯,颇显本篇著者之苦心,旨在复返《老子》“行不言之教”之真意而诠显体验入门之正途。
1.2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
“厌”,多训为满足,如是“则与‘不自忍之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丁四新先生之批驳甚为有力,然训为嫌厌、厌弃,亦有商榷之处。许慎《说文·厂部》曰:“厌,笮也。”《竹部》曰:“笮,迫也。在瓦之下芬之上。”《段注》曰:“笮在上椽之下、下椽之上,迫居其间故曰笮。《释名》曰:‘笮,迮也。编竹相连迫笮也。以竹为之故从竹。”可知厌者有因绵绵内充而自我笮迫之意。忍,孔子《论语·卫灵公》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自厌不自忍,或作”一句呈上句而来,其意为:恒先本然无名,超越常言所谓朴、静、虚,然恒先亦非断灭之无,恒先者乃不可言说之太朴、太静、太虚。太朴、太静、太虚则自我迫笮。因恒先自身内充自迫至于极而恒先自身又不能自忍,故有“或”之生起。《说文·人部》曰:“作,起也。”可知恒先既为动之源亦为动本身。孔子《易传·系辞》曰:“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恒先”“自厌”之情状。
或,乃《恒先》至要用语,主要有两种阐释。李零先生以为:“‘或,在竹简中是重要术语。它是从‘无派生,先于‘气、‘有的概念,从文义看,似是一种介于纯无(道)和实有(气、有)的‘有,或潜在的分化趋势。(‘或有或然之义。)”颇为透彻,引人深思。又李学勤解为域,转读为宇,意为空间;或解为宇宙,似皆可商榷,已有研究者详论之。陈静先生虽从李先生之说,然亦不无疑虑,曰:“这里真正难解的是连读‘或作。‘作单独解释也容易,就是‘动了。可是连读‘或作而把空间与动联系起来,在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困难。”然“或”之诠释,或可另辟蹊径。
文王《易经·乾卦·九四》曰:“或跃在渊。”孔子《象》曰:“或之者,疑之也。”意为君子修行至九四爻位,已有小成,如龙可在渊水之中自由腾跃,然非大成如《用九》爻位“见群龙无首,吉”之境界,故对“跃在渊”之境颇有疑窦。故或字在人即是自我疑问、自我怀疑之意。在本篇“或作”即疑起。此乃《恒先》作者以拟人之修辞法而描摹由宇宙本体刹那生起宇宙精神之情状。意为恒先于浑然太朴、太静、太虚之氤氲鼓荡中,生起一念自我怀疑,自我内冲、迫笮至极而不能自忍,不能自忍故一念疑动,一念疑动即“或作”。故知“或作”,乃“恒先”朴极、静极、虚极内充之刹那所生之自然情状。“或”即由无至有、由道至器、由形上至形下一念之转内在之玄机。孔子《易传·系辞》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深”即“恒先”,“几”即“或”也。王弼《注》曰:“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逋动微之会则曰几。”“恒先”即“未形之理”,“或”即“动微之会”。《易传·系辞》又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王弼《注》曰:“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鉴于未形也。”《庄子外篇。至乐》曰“万物皆出于几”,成玄英《疏》曰:“几者,发动,所谓造化也。”则知“或”即造化,其在西洋哲学,即宇宙精神之谓也。故知《恒先》之篇,旨在诠显老子“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理。《恒先》作者以为,无一有一物,由前至后,于“无有之间”,有一“或”为之中介,无、有二者皆无名之世界,然由无之有必有一念之生机、刹那之蕴育,此即“恒先”之无,因“自厌不自忍”所生起“几微”之“造化”。恒先之无为道体之体,造化之“或”为道体之能,以此能而为中介,故有道体潜藏之物之所由生。故《恒先》之序为:恒先→恒→或→气。
而“气”之后又有“有”、“始”、“往”三重朴散。于“往”之后,方有万物之“天地”。则恒先“无名”之境为:恒先→恒→或→气→有→始→往。
此七者即《老子》所言“无”之扩充。故《恒先》文末曰:“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疑,荒言之;后者校比焉。”道本无名,无名亦在,不明无名之在者,必于无名之道大为怀疑,然此怀疑又非名言逻辑所能确析,以其本然无名故。故《恒先》作者,以“荒言”这一言说方法而言说之。《老子》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即于“先者有疑”者。而于上士,则知道(恒先)非言说之境乃无名之境,欲达无名之境,则必以离言绝待之体验法“勤而行之”。而若迷于“校比”之存在,则离恒先之道愈为下矣。故《恒先》之篇,判然剖别“无名”与“有名”乃至“多名”,欲以明晰之理而使人返回大道真体、无言之境,故全篇结尾曰:“举天下之名无、有法者,与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意为凡天下之名,其为无法者即无名者或其为有法者即有名者,即凡无名之道,有名之器,若予天下王中之明王、君中之明君、士中之明士,则明王、明君、明士,皆恒常以“上士”之根性“勤而行之”,于大道真体,不虑不疑,而非“中士”之根性“若存若亡”而“有疑”不已也。则《恒先》之序乃由智慧理性而达于实践理性,终极者乃在于践履道体而人无名之境也。
焉,乃也。意为恒先有一念“或”——“几”、“动微之会”之动,同一刹那即有气之生起;有气之生起,同一刹那即有“有”之生起;有“有”之生起,同一刹那即有“始”之生起;有“始”之生起,同一刹那即有“往”之生起。故曰:“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意为绝言离待之宇宙本体因宇宙精神——“或”刹那之动,故有“气”、“有”、“始”、“往”之生起。“或”为因,“气”、“有”、“始”、“往”四者为果。宇宙本体因宇宙精神一念之动而生起宇宙显形最初之情状,即“气”、“有”、“始”、“往”四者。《恒先》之生起次第为:道(恒先)→或→气→有→始→往。而《老子》二十一章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状,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其迦道次第为:状→象→物→精→真→信。信即道体。若逆转此序而为道之生起次第,则可明《恒先》之所指:
《老子》:信→真→精→物→象→状
《恒先》:道→或→气→有→始→往
道即信、或即真、气即精、有即物、始即象、往即状。再参以下文,其意更明。
1.3往者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往字,依李学勤所补。上文已言,《恒先》之生起次第为:道→或→气→有→始→往。此段以“往”为例而明道、或、气、有、始、往六者同体而异质、异质而同体之性状。
宇宙道体(恒先)虽因宇宙精神之一念(或)而有气、有、始、往四者之生起,然往之境,亦是“未有天地”之境;其性自然,故“未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未有实体性天地之生起,故曰:“而未或明,未或滋生。”简文之“往”,即《老子》之“状”,参以屈子《天问》,即是“上下未形、冥昭瞢暗、冯翼惟像”之境。往者如此,而往由始生、始由有生、有由气生、气由或生、或由道作,故道、或、气、有、始、往六者,六位而一体、一体而六位,浑然而为一。
2、第二部分通解
2.1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然有无之间,其状何如?此段即为老子有无之间之诠释。依上文可知,《恒先》生起次第有六位之别,即:道一或一气一有一始一往。而气之生,全由“或作”,故此曰“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意为气乃是自因而生、白因而作,非道体恒先之所生,以“道”、“气”之间有“或”故。李零解“恒莫生气”曰“是说道并不直接产生气”,甚确。有或,即宇宙精神一念之起,宇宙元气即刻而生。故下文曰:“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意为气者虽是自生自作,然其生作必以“或”为中介,故曰“不独”;其“有与”者,即其中介者为“或”。而或又为“恒先”“自厌不自忍”之所生起,故气虽自生自作,此气非恒先外之存在,故曰“恒气”,即“恒先之气”之意。“或恒焉生”之主语,仍为“恒气之生”。“或恒”,为“或于恒”之省文。“或于恒”即“于恒有或”之意。联上而言,意为恒先之气之生起,非是无因独然而生,其生起有中介之与者即“或”,在恒先之中必有“或”之生起,于是恒先之气乃能生起。《说文》:“同,合会也。”焉,于之。于之之“之”,指代恒先与气二者。“或者同焉”,即“或者同于之”,正言之即“或者于之同”,意为宇宙精神之“或”在恒先与气二者之间合会也。则知“或”,上达于恒下通于气,故曰“或者同焉”。或之几既发于恒又显于气,“或者同焉”即总结简文恒→或→气三位一体之境。
2.2昏昏不宁,求其所生:异生异,畏生畏。韦生韦,悲生悲,哀生哀;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
此承上而来,则知“昏昏不宁”者,乃谓气也。《说文》曰:“昏,曰冥也。”《段注》曰:“冥者,窈也。窈者,深远也。”气昏昏然,即气窈冥深远之貌,亦即老子所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之境。宁,安也。气本昏昏、窈冥深远,因得“或”一念动之性,故亦不宁不安,由是故于运化之中,必“求其所生”也。其所生者,曰异、畏、韦、悲、哀。异为所生之总纲,《说文》曰:“异,分也。”《段注》曰:“分之则有彼此之异。”所生之始,异分为先。然异分之中,亦有类对焉,如畏与韦对,悲与哀对。因此类对,故有下文浊与清对,乃至地与天对。故《恒先》之意,气精之中,寓有情性,情性类分,然后清浊有体、地天剖分。道体寓藏精神,宇宙精神化为宇宙情性,终了由宇宙情性生出有形之宇宙即天地万物。
然“昏昏不宁”之气,于“求其所生”而向下化生之同时,亦必向上“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复者,即回复于生之所为生那一运行之中,此行即“或”。“或”为中介,生生不息,故上应恒而泯于道,下启气而化于物。故生谓二生,向下者所生,向上者复生,且向上向下,同时而生。若不如此,则所生之物,终有尽时,而“恒先”之能亦可断矣,生生之息亦可灭矣。故此段之要,在窈冥深远之一气,开出同显之二门:所生者“流转门”也,复生者“还灭门”也。
2.3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察察天地。纷纷而复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复以不废。
信,《老子》曰:“其中有信。”信为道之显现,且为道显现之终极。“气信”,为气中所含之信,此信为道之极,故曰神哉。依此气之信,故芸芸之物相因而生。上节已言“异生”、“类生”,依彼“类生”,乃有此“相生”。“类生”之中有“复生”,“相生”之中
岂无“复生”?故曰“纷纷而复其所欲”。纷纷即芸芸,即天地万物于彼此相生之当下,亦各复归其所欲,所欲即前文所言“求欲自复”之“求欲”。若天地万物于相生之时,不同时复返于恒先,则下泻无穷,上补无助,唯下生而无上源,则察察天地枯,芸芸万物死矣。故曰:“明明天行,唯复以不废。”孔子《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即“恒先”之道。《剥·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乾息则盈,坤消则虚,同时而运。”坤消即相生,乾息即复生。
2.4智既而荒思不殄。有出于或,生出于有。意出于生。言出于意,名出于言。事出于名。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意非意,无谓意;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
以上所言皆是宇宙之事,自天地出现后,方有人类,而人类之尊贵,在人类有智思,故此章详叙人类智思之要。智,智慧。既,《段注》曰:“既,已也、尽也、终也。”智既,谓智之已然、全体、终极。“智既而荒思不殄”,承上启下之句。陈静以为:“这句话当属下读,因为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话题,从宇宙的自然生成,进入到人的名言世界。因此在我们的分章结构中,此句是这一章的首句,而不是上一章的末句。”甚确,今从其说。上言“明明天行”,人智若不明,何可明“天行”之明明。能明天行之明则人智必既,若人智既,则人道亦必明矣。人道之要,在于智思,智思之用,首先要明“或→有→生→意→言→名→事”七位前后衍生之次第;其次要明或、有、生、意、言、明、事七者之真实。“或非或,无谓或”——意为宇宙精神“或”若非宇宙精神“或”本身,则于人之智思必不能确立“或”之判断。有、生、意、言、明、事六者,亦复如是。可知《恒先》之智思原则,是逻辑判断中之存在命题。依此原则,即知识之前提在于A=A,故能运“荒思”而“不殄”。荒,原字为巟,李零曰:“是广大之义。”殄,原字从一从天,李零读为殄,《说文》曰:“尽也。”不殄,即不尽而无穷之意。《庄子·齐物论》曰:“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文所言“智既”即“得其环中”,所言“荒思不殄”即“以应无穷”。
2.5恙宜利主。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天之事,自作为事。庸以不可更也。凡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
恙宜利主者,谓恙于宜者乃利之主也。《说文》曰:“恙,忧也。”孔子《易传·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恙宜,谓忧患于宜。宜者,义也。利,《说文》曰:“铦也。刀和然后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有和意。主,《说文辨字》曰:“主本火主字,借为主宰之主。”又《左传》曰:“民者,神之主也。”
综上所引,“恙宜利主”者即“恙义利主”,谓忧患于对立面之存在乃和谐境界之主宰也。此乃终上开下之句。恒先之道,本然为一,因“或作”而生“气”,由“气”而生“有”、“始”、“往”。则“或”与“恒”有别,“恒”与“气”有别,此对立面存在之一也;“气”自生自作,然其运化有“流转门”、“还灭门”之不同,此对立面存在之二也;“气”衍生之“往”,乃从无形之宇宙生出有形之宇宙,“浊气生地,清气生天”,地浊天清,此对立面存在之三也;天地产生,人类化生,“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然贵在何处?《恒先》以为,人性最贵者在人之“智思”,然人运智思,又有“是”“非”二边之别,如“或非或,无谓或”(中含“或是或,谓或”之意)之类,是与非,此对立面存在之四也;本章有“有事”与“元事”、“乱”与“不乱”、“善”与“不善”等不同,此对立面存在之五也;后文又有中外、小大等,此对立面存在之六也;又有“荒言”与“校比”、“天下之名”与“天下之作”之不同,此对立面存在之七也。则道、气、天地、人、智思、物,无不在二边之中。然《恒先》之境,皆为就二边而诠一理,以明天道“唯一犹一”之恒常。故此“恙宜利主”,实为全篇之警策,亦显“智既而荒思不殄”之妙用。
“采物”,董珊先生以为“采物”即是万物,可从,今扩充之。《诗经·曹凤》“采采衣服”,《传曰》“采采,众多也”,可知采物即众多之物,亦即万物。“采物出于作”,意为若无宇宙精神“或”之生起,则存在就不能成其为存在。“举天之事,自作为事”者,举者凡也,意为凡天地间之存在,皆为自作自生之存在。何以故?天地源于气,而前文曰“气是自生自作”,故由气所运化“浊气生地,清气生天”之天地,亦为自作自为之存在。更深之缘由,为恒先之道,遍在天地故。故曰:“庸以不可更也。”《九家易》曰:“庸,常也。”意为凡天地间之存在皆为自作自生之存在,此一事实为永恒之真理而非可改易者也。
“凡多采物”之“多”,意为重叠增益。《说文》曰:“多,重也。”可知“多采物”,为增益之采物。前言“采物”谓天地之物,天地之物即自然之物。增益于天地自然之物之上者,必为人文之物。“凡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乃对人文之物历史性之评价。《恒先》以为,凡增益之物即一切人文之物,其出现产生有先者、后者之分;若对其作一价值判断,则《恒先》以为,凡早出之人文之物为善,而后出之人文之物为不善。《恒先》作者从老子之指归,以为穴居之于宫室、衣薪之于棺椁、结绳之于书契,前者为善而后者为不善,前者为有治无乱而后者为无治有乱。何以故?“有人”故,人者圣人也。而圣人所作刻意性之人文多非自然之人文。至《庄子·马蹄》以为:“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蹄歧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正是此意。
2.6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天道既载: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
焉者,乃也。中外、小大、柔刚、圆方、晦明、短长,两两相对之中,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前者为源后者为流。既者,已然。载,《毛传》曰:“事也。”“天道既载”,谓恒先之气所化之天地,其内中之道体已然成事,即天道不虚,已然显形,成为存在。所谓存在,即天地之“采物”与人文之“多采物”,然恒先以为,采物、多采物,皆生而有序、序中含理,其性以一显一,其德以复显复。“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即“唯以一犹一,唯以复犹复”。犹,图画其貌而显其形也。《周礼》曰:“以犹鬼神示之居。”《段注》曰:“犹者,图画也。”前文言“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谓凡物皆得气之信,即采物、多采物皆得气中所含道体恒先之信,故采物、多采物虽物有分别,然皆以其一性而显现其存在之一性;且自然之物、人文之物,皆于生生之当下,同时复反于恒先道体之本身,即皆以复反之德而显现其存在之德。道、
气、物,三位一体,向下流转之当下亦向上还灭于同时,然流转、还灭皆是直观显形之境而非概念推演之说。
3、第三部分通解
3.1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疑,荒言之;后者校比焉。
“先”字下,原有墨钉,李零以为应是表示专有名词的符号,可从。余反复玩味,因先与后为对文,故断句如是。先者,既为无名之存在即道,又为《恒先》开篇描摹无名之道之部分,即《荒言章》(详见下);后者,既为有名之存在即器,又为《恒先》逻辑化分析有名之器之部分,即《校比章》(详见下)。如是理解,则此句文意及全篇结构,思过半矣!“荒言”与前文“荒思”相类,且与“校比”相对。荒思者,无名之思也,超越之思也,自然之思也,一无人为之搅扰,故近于道。荒言者,描摹道体“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之言也。所言“恒先无有朴、静、虚”:“为一若寂,梦梦静同”云云,皆此类也。
3.2以下六段,乃第二部分相应之总结阐释。
3.2.1举天下之名,虚树,习以不可改也:
此一段乃是对2.1-2.6全部之说明。举者,凡也。树,原字从言从豆,李零读为“树”,树者,作也。屈子《九章·抽思》曰:“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习者,李零解为“袭”,可从。谓凡天下一切之名言,即人类之语言系统,无非是约定俗成、假名虚设而已;又因其代代相袭而不可改易也。谓人类语言系统一经产生,即自有因果相续之延转,成为人文之载体,文明之工具。然《恒先》依从老子之说,以为道体道用,本皆自然,皆为体验境界,本与语言毫无瓜葛。故无形之道,“强为之名”而已;有形之器,“虚树,习以不可改”而已。故作者本无言可言,为使人能明道体之真,勉强依“不可改”“习”之“虚树”而言说之。故《校比》一章六段,皆“勉强为之言”而已。
3.2.2举天下之作,强者果;[举]天下之大作,其冥龙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
此一段乃是对2.2之阐释。“作”与“大作”相对。作谓“异生异,畏生畏,韦生韦,悲生悲,哀生哀”,而“大作”谓“昏昏不宁,求其所生”。此第一重“作”与“大作”之别;二者,“作”谓“生”而“大作”谓“复”。两重作与大作,皆具“强者果”与“其冥龙不自若”性质之别。凡“作”者,皆非自然之事,乃勉强之事,非自然勉强之事,易为人觉,故有“果”即现实性之显现。而“大作”者,皆“道法自然”之事,道法自然之事,不知其然而然,故“冥龙不自若”。冥,原字从一、炅、支、糸,廖名春以为乃“冥”之异文。冥龙者,惚恍也,混沌也。谓“大作”之事,恒然惚恍,常为混沌,恍若他物而非自体。然“作”之事,常果而似真;“大作”之存,必“不自若”而真真。似真、真真,唯在眼界。真人以真真为真,而众人以似真为真。“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意为天下勉强而作之事,常有果与不果二种结果即常有能实现与不能实现二种结果,然此二者皆为存在,并行不废。
3.2.3举天下之为也。无夜(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
此一段,乃对2.3之阐释。意为天地之生,万物之复,皆是无为而无不为之事也。舍,原作夜,李零读为舍,可从。“舍”“与”相对,陷在二边之分别,非惚恍大道之本然,故《恒先》以为,凡天下所为之事,本自然也,若无刻意之舍弃亦无刻意之介入,则皆自为而成也。有舍、有与皆有为也,若反于是,则为无为,无为即《恒先》之自为。
3.2.4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天下之作也,无迕极。无非其所;
此乃对2.4一段之阐释。生即存在即万物,同即万物为万物之本身,其在判断即A=A也。然其同之因在“其事无不复”,复于何?复于道也。然“道可道非常道”,即道不是什么,道只是道,亦即“道是”(Dao ist),即A=A也。是故,即在“天下之作”,若乃“无为而不为”者,亦为“无非其所”,即无不是其所是、无不在其所在,即存在之“此在”(海德格尔之Da-sein),何以故?以“天下之作”皆法于自然而无有迕逆其存在之极即与道相和而无分别也。迕,原字作许,廖名春读为迕,可从。
3.2.5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极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
此乃对2.5一段之阐释。依前释文可知,《恒先》以为,自然之物即“采物”,而人文创造之物为“多采物”。“多采物”又有先后之别,先者为善后者为不善。“天下之作”之“作”既指“采物”亦指“多采物”,二者皆因“得其极”即上段“无迕极”方能成就其存在即“果遂”。极,道之极也。若反于是,即“不得其极”而“迕极”则必不能“果遂”,故曰“庸或得之,庸或失之”。庸者常也。得之即“果遂”,“失之”即“果不遂”。
3.2.6举天下之名无、有法者与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
此乃对2.6一段之阐释。“无、有法者”,谓“无法”与“有法”二者,《老子》一章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即“无法”,“常有”即“有法”,然此二法,亦是假名而已,故曰“名无、有法者”,意为一切存在本不可言,勉强言之无非“有”与“无”而已,达于道之法亦无非“无法”、“有法”而已,故为道而授法于天下者,其法非实有之法,乃假名之法。言者无心,听者自悟;言者无意,听者自履而已!《庄子·外物》:“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正显此境。
太史公《老子韩非列传》以为,春秋之时,在周则有老子,在楚则有老莱子,“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则知老子、老莱子两位圣者,其学说有“意”与“用”之不同,《恒先》之篇,详阐“道德之意”,归结为“道家之用”,然终不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旨趣。其后《庄子·寓言》曰:“言无言:终始言,未尝言;终始不言,未尝不言。”唯如是,乃显道家“意用之间”之妙处。
《庄子·应帝王》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由是可确会《恒先》之意。即《恒先》以为,“道德之意”、“道家之用”,非授予王、君、士,亦非授予名王、名君、名士,必授予明王、明君、明士。何谓明?《老子》十六章曰:“复命日常,知常曰明。”即明了“归根复命”之理亦即透悟坚信大道之理者,方可曰明。得明之王、君、士,已入“自知者明”之境,深通大道,得意忘言,故能“庸有求而不虑”,庸者常也。谓将观无、观有“意用”之法授予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则明王、明君、明士常能“求而不虑”,即恒常求于无名之道而弃去“昭昭”“察察”之虑,此既为道家之良愿,亦为道学之门规也。
二、章节拟构
《恒先》共一十三简,原文并未分章,然其结构井然有序,且篇中自有说明。第八简末至第九简初
曰:“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疑,荒言之;后者校比焉。”由此句至文尾,乃一篇之总括,而前于此有“荒言”部分与“校比”部分之不同。故《恒先》一篇,其结构乃三段式,唯为研读方便,可拟加名曰《荒言章》、《校比章》、《乱曰章》。前两章采篇中之名,末一章用屈原楚辞“乱目”之义。则其章节如下:
恒先
《荒言章》
1.1恒先无有朴、静、虚——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1.2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又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
1.3往者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校比章》
2.1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
2.2昏昏不宁,求其所生:异生异,畏生畏,韦生韦,悲生悲,哀生哀;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
2.3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察察天地,纷纷而复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复以不废。
2.4智既而荒思不殄。有出于或,生出于有,意出于生,言出于意,名出于言,事出于名。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意非意,无谓意;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
2.5恙宜利主。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天之事,自作为事,庸以不可更也。凡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
2.6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天道既载: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
《乱曰章》
3.1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疑,荒言之;后者校比焉。
3.2.1举天下之名,虚树,习以不可改也;
3.2.2举天下之作,强者果;[举]天下之大作,其冥龙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
3.2.3举天下之为也,无夜(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
3.2.4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天下之作也,无迕极,无非其所;
3.2.5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极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
3.2.6举天下之名无、有法者与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
责任编辑:涵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