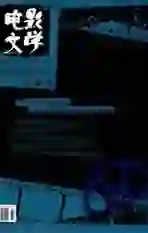老舍在西方传媒夹缝中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
2009-04-14李丹
李 丹
[摘要]研究老舍至今已走过了80年,这期间在作品研究、思想性格研究、文化视角和比较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老舍国外工作的近10年,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的贡献却研究不足,这不能不说是老舍研究的一个缺憾。本文意以老舍英伦受聘和美国讲学两个时期,从汉语教学、中国古典名著翻译、小说创作和电影改编等方面对老舍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关键词]老舍;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贡献
2003年11月老舍上个世纪20年代在伦敦的住所被镶上“名人故居”蓝牌,这是英国首次将“文化遗产”授予中国人名下,这样的蓝牌在英国只授给为人类福祉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是英国人对老舍在人类文化方面卓越贡献的肯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虽然我们对老舍作品的文化蕴涵做过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老舍对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贡献却鲜有人去探寻,即使有人提到老舍的欧美经历,也是为了补充“老舍生平传记中的一大段空白”,虽然偶见《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珍贵遗产——试论老舍在伦敦期间的对外汉语教学》这样的文章,试图“对老舍在伦敦的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一番考察”,遗憾的是作者本人仅是探讨了老舍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贡献,并未对老舍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方面做更多的阐述。老舍一生之中在国外工作近十年,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不能不说是老舍研究的一个缺憾。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试图从英伦和美国两个时期对老舍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一、英伦时期:通过教学、广播讲座和翻译等进行汉语及中国文化传播
第一,汉语教学、广播讲座和教材编撰。1924年老舍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汉语教学生涯。老舍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名著”“翻译”和“历史”等;五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人学习官话,这仅是课堂上对于汉语的传播,更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受邀到英国广播电台(即BCC)作汉语知识广播讲座;同时受“灵格风语言中心”之约,与英国同事一起编撰了一套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并由他本人朗诵灌制了15盘留声机片称为《言语声片》。这套教材流行了近30年,影响大传播广,因署名“c.c.Shu”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终被证实为老舍编著和录制,此事曾经轰动一时,老舍遂被尊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鼻祖。这一时期老舍对汉语在海外传播的贡献是无法用数字计量的。
老舍在英伦时期,英国学风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重实用而轻理论,重功利而轻玄思。这也反应在英国的汉学研究上,老舍在其著述中提到过“远东语文与学术的研究,英国显然的追不上德国或法国”,就当时的东方学院而言,“重要的语言都成为独立的学系”“所谓的重要与不重要,是多少与英国的政治、军事、商业等相关联的。”因此,校方派给老舍更多的是汉语教学任务,以便于对中国的殖民输出,但这并未影响到老舍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例如在《言语声片》中,老舍有意把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日常交际用语,如“过奖”“贵姓”“贵国”“贱姓”“敝国”等编写在句子中。
第二,公共讲座。尤其令我们注意的是老舍题为《唐代爱情小说》的公共讲座,老舍不仅对唐代爱情小说的类型、语言、发展脉络以及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作了鞭辟入里的阐释,同时推荐了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参考书籍。这就为海外的汉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同时,老舍通过比较的方式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由此而影响的中国人独特的性格、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具体而言,老舍在解读唐代爱情小说中展示的中国包办婚姻制度时,他通过中西方宗教信仰的对比得出:“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那里,宗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但在中国人心中则不然,对没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宗教只是一种迷信,全然不考虑教义的出处,而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宗教则是哲学和公共准则。不过,对这两个阶层的人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对命运的信念是相同的。他们坚信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老舍以为中国婚姻的精锐就在于此,一切都被月下老人安排好了,剩下的便是顺从和接受,而且能在屈从中得到满足。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这将导致缺乏积极性和勇气;可是在中国人这里,屈从命运却是安定的基本因素。当一个中国男人发现他的婚姻是不美满的时候,他决不会向命运挑战,他以为,生命之水都必须归顺主宰生命的大河,享乐的最高形式便是简单地将他自己交付给这条大河。因此,他便忘掉了自己的痛苦。”这对西方听众提出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宗法制度而代之以婚姻自由?”给予了符合中国国情又是独辟蹊径的回答。
进而老舍又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的情人们不像欧洲小说或者美国电影描绘的那样,在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而是总等着别人来救他们?”疑问:“这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他们受的教育不同。中国的教育是将青年训练成上等人,拥有高雅的态度和崇高的心,他们是哲学家,是绅士,优雅而亲切,决不能去打架!打架是勇敢的将军们的事,而将军们只不过是幽雅亲切的绅士们豢养的狗。所以,当中国情人们处于困境时,他们并不为自己而战斗,总是旁的人把他们解救出来,有时甚至是靠想像出来的英雄。”
众所周知“在19世纪,汉学家与殖民者合谋,精心虚构了中国的形象:专制、落后、愚昧、肮脏,与西方的开明、进步、理性、高贵、完美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为西方对中国进行殖民寻找合法性和正当理由。”因此西方民众无从得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老舍站在比较文学、文化学、宗教学的角度,为西方听众不仅提供了了解唐代爱情小说,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一个客观视角,也是对于西方19世纪普遍出现的对中国形象误读的一种正名。
第一,古典文学翻译。1925年初老舍结识了汉学家埃杰顿,并协助埃杰顿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译本,成为《金瓶梅》在英国惟一的权威译本。出版时,译者特意在扉页上题词:“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在“译者说明”中,第一句话就是:“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由于老舍的帮助埃杰顿的英译本相当成功,曾一版再版,很受西方读者欢迎。
二、赴美讲学时期:通过讲学、创作、翻译及作品
电影改编进行现代中国介绍及中国文化传播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当时的美国人“包括高等学府中的教授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知甚少,不论讲什么,他们都摇头,脸上一片茫然,完全没有反响。”不仅如此,来美之前老舍的《骆驼祥子》已被译成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且博得好评畅销一时。然而当老舍来到美国看到此书时却发现书的封面上所画中国人居然还拖着长辫子,而且书的内容也按照美国公众对于中国认知的习惯心理进行了篡改以迎和美国人的口味,这种习惯心理将中国篡改成美国人想象中的
愚昧落后的中国。同时老舍亲眼看见一位研究中国古画的美国人,在作品中竟把中国长城画到黄河以南去了,老舍确信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千百年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这使老舍在文章中反思到“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认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应该延伸到文化领域,“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
本着向美国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初衷,老舍在美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著名高等院校和艺术中心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讲。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老舍勾画了现代中国小说在吸收民间营养、摆脱传统束缚、接受外来影响中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发展轮廓,弥补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现代小说认识和注意的不足。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独到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现代中国小说,是指用白话(即普遍人的语言)写成的小说。”“早在唐、宋之时,甚至可能更早,已经有白话小说出现。”这样,老舍就打破了按年代划分文学史的传统做法,而是以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在特征为尺度,将“现代”的时间上限推到唐宋。这一观点不但为现代小说追根溯源,同时也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以崭新的形式介绍给了西方。
第二,在美国期间老舍还通过创作践行着传播中国文化还原真实中国的愿望,完成了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在《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里,老舍一改在《赵子日》《老张的哲学》时期的“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的创作态度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骆驼祥子》《月牙儿》等篇中的血泪控诉和不可遏止的义愤,我们不但看到了对苦难和屈辱的描写,而且看到了对革命力量的颂扬,对反抗和新生的讴歌,这当然是国内的抗战真相使然,也是老舍在美时期意图通过创作“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的意愿使然。“《四世同堂》被评选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菲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传统。”
第三,在创作的同时老舍将自己的四部长篇小说《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和《牛天赐传》翻译成英文,对小说也进行了电影改编,还将《断魂枪》改编成了英文话剧,《断魂枪》是老舍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力作,这部作品的改编亦可以看出老舍深刻的意图。“他回国后,这些译本还在陆续出版,并被转译成欧洲的许多文种,形成一次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较为集中地被介绍到欧美去的小高潮。”老舍通过文学作品让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愿望达成了,这些作品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
近年来我们用文化视角研究老舍本人和老舍作品的文化品格、文化蕴涵:为生平专辑的补充而搜集老舍在英美的点点滴滴,却不经意间遗漏了这二者的结合,即老舍在欧美时期在西方传媒夹缝中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最显性贡献,他在汉语及汉文化传播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是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