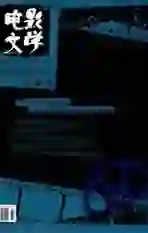《卧虎藏龙》的视觉文化解读
2009-04-14朱薛超
朱薛超
[摘要]自《卧虎藏龙》以来,中国的武侠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声誉,许多西方商业电影也开始热衷于借鉴和使用武侠的元素。但是武侠片的艺术表现形式负载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必然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这种不同的解读一方面与文化多样性有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一方面与权力有关,可生产更多意识上的分歧和不平等。
[关键词]视觉文化;武侠片;《卧虎藏龙》
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与最佳摄影奖的电影《卧虎藏龙》,其画面之精美,视觉呈现之独特备受称道。除却影片中颇具复古色彩的场景、人物造型,其浪漫化的、诗意舒缓的武打动作也帮助影片创造出更吸引人的视觉效果,几乎获得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比如《国际电影报》就称其为“一次美妙的令人兴奋的幻觉的飞行”。《卧虎藏龙》中的功夫元素是非常风格化的,每一个人物的动作都符合人物本身的人格特点。在这场“视听的盛宴”中,极其富有东方神秘韵味的,中国独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频频呈现的武侠功夫,无疑给观众(尤其是西方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部电影的奥斯卡光环似乎也激发了中国功夫的国际潮流,自《卧虎藏龙》之后,中国内地剑指奥斯卡的各大导演开始了对武侠/功夫的发掘、演绎、复制且乐此不疲,并一度制造出中国式大片唯“武”独尊的现象。好莱坞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商业电影也开始吸收和借鉴“功夫”元素,直至后来生产出直接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好莱坞主流影片《功夫之王》。在当代电影由叙事电影到景观电影的转变过程中,在功夫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同时,国内的功夫/武侠影片却多被诟病为奢华瑰丽的外表包裹下的意义的真空。比如《英雄》被评价为打造抽空了内涵,与主题完全割裂的唯美空间,而《十面埋伏》则体现出对视觉欲望的极度迎合和满足。
于是诸如功夫如何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武侠片如何摆脱空洞麻木的视觉盛宴的宿命,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很值得关注的。然而就武侠功夫本身而言,虽然其电影表现技术已日臻成熟,在银幕上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其形象特征尚有待细致地分析和解读。呈现于银幕之上的,作为观影者逃避现实和寻求心理满足的奇幻景象的武侠功夫是否仅仅提供愉悦视听的功能?它的背后,或者就是它的形式本身是否存在某种象征,某种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隐喻”,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它和观众之间能够产生怎样的心理互动?本文将选取《卧虎藏龙》中的一组镜头进行文本分析,以期解答这些问题。选择这样一部影片作为文本,固然是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本文的重点不是分析李安导演如何在武侠电影中注入艺术性,而是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电影文本进行解读,以期解构/重建文本的真正意义,从而阐释武侠功夫的视觉特性及其所面临的困惑。视觉文化研究旨在解析视觉文本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探索意义在视觉世界里是如何产生并传递的,并融合图像学、艺术史、意识形态、符号学、解释学等知识体系和分析策略来发现视觉文本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视觉文化希望向我们展示独立审视视觉图像的方式,领会那些图像的意义是如何被传达的,甚至探索视觉图像的意义是如何在读者解读的过程中被耗散的。
武侠功夫不是影视媒体的独创,但却是通过影视媒介将其“具像”呈现出来。文学作品中早有大量详尽的对功夫的浪漫主义风格的描述,如金庸的小说对一招一式都精描细绘,形象宛如跃然纸上。其中最奇特的是轻功。这一最不符合人的生物学常识,同时也是现实中最难实现的武功,于读者的想象中却是轻而易举,全然不费解。作为竞技的手段(攻击和逃避)和肢体的无限制延伸(空间转移),它提供了一种成年人童话式的对现实的逃避和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更重要的是,“轻功”还具有丰富人物内涵的美学意义。比如一个轻功卓绝的美貌女子,于凌空腾跃之间常常给人以仙女的幻觉,引起众多青年俊杰的倾慕。轻功也可以表现张扬、洒脱、浪漫的性格。但是文学作品的描写毕竟是抽象的,读者的想象可能各不相同。当这些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这些“武功”被诉诸图像来呈现时。影像技术把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表达得极具观赏性,为观众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和兴奋。现代的新技术和特效手段在电影中把武功,尤其是轻功,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源于香港的此类电影衍生出写实与写意两种打斗风格,并发展成功夫片和武侠片两种类型。但是两个片种并没有明晰的区分,交融的地方很多,一般说来古装的、刀剑的、侠义的影片称之为武侠片,其中武打更像是舞蹈。武侠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如20世纪40年代的张彻开创以“阳刚”为主题的中国男性电影,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徐克是把武侠电影带人“一个影响奇幻、意蕴驳杂的新阶段”,他以特技和剪辑制造出幻化的高难度动作,观赏性极高,具有显著的个人风格。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内地一向不善于制作运用大量特技的奇幻型武侠片,然而近几年来,国内的大片却以武侠片为主,在视觉奇观中反复地以各种风格复制和再现武侠神话。这一方面是受到好莱坞大片制作模式以及好莱坞技术的影响,国内导演开始热衷以巨资来打造巨制;另一方面得益于内地和香港电影届更紧密的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合作。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触发性”的因素,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似乎表明承载着关于古老东方想象的功夫片/武侠片似乎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通道。
《卧虎藏龙》的主要场景设在被誉为“中国画里的水乡”的宏村。而影片里的“功夫”也如同片中风景一样让人惊艳。有网友戏称这部影片在房檐上玩杂耍,在竹枝上跳芭蕾。电影里几个极具观赏性的段落是俞秀莲和玉娇龙深夜在房顶上的追逐,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里的对峙,以及片尾玉娇龙起身飞向万丈深壑(背景是武当山)。本文将细读其中的一个段落,即竹林中的一场戏,来探寻“功夫”背后的深层含义。故事情节是李慕白要求玉娇龙交出青冥剑,玉娇龙转身轻灵地飞起,一直飞到村外的竹林中,李慕白也同样飞起追逐,二人遂在竹林中进行打斗,最后玉娇龙败落下风,逃出竹林。其画面的视觉表现即是人像烟雾一样轻轻飘起,像鸟一样翩翩飞舞,甚至立于枝头。竹林是武侠片偏爱的场景。竹枝的轻灵摇曳。竹叶的婆娑舞动无不契合飞翔的意境。在1993年的影片《新流星蝴蝶剑》中,杨紫琼在竹林中施展轻功的一场戏就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这显然不是真功夫,只是对功夫的夸张和想象,但对于观众来讲并非不可接受。很多武侠影视剧中都出现过类似的飞翔的画面,而《卧虎藏龙》的想象力似乎要更高一筹。影片中一组最“不可能实现”的镜头就是白、龙二人立于竹梢之上,持剑对峙。画面已经不言自明地展示出两人轻功之高下:玉娇龙摇摇欲坠,面露怯色;李慕白则稳稳地站在随风摇摆的竹子上,气定神闲。一种刻意强调的男性的持重、自信、冷静、掌控自如的形象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而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白将龙踢下竹梢,龙仰面下坠,白则持剑紧逼,最终两人的力量对比和权力
关系通过这一串镜头展现得一览无余。
当然这是电影语言的表达,或者说是电影符号的表意。但是诚如罗兰巴特所言,神话即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它将特殊的言说成普遍的,将历史的言说成永恒的,而其根由正是这一特殊的和历史的建构所代表的特殊群体或阶级的权力。巴特关于“不言而喻”的论述,是神话学对视觉文化分析的最有用的贡献,它让我们透过表象来重新质疑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在影片中,玉娇龙的轻功已经被渲染得出神入化:在她盗取青冥剑时和俞秀莲的脚力较量中即频频占据上风;在她独闯江湖大闹酒楼时,众武林豪杰败得一塌糊涂,她的轻功自然是制胜秘诀。轻功就其视觉形象的表达方面而言显然是更适合女性的功夫,在武侠小说的描写中轻功最卓绝者往往是一些女性,轻功似乎是在所有武功中女性可以胜过男性的最显而易见的一种,因为它最能体现女性的气质:柔美、灵活、感性。但事实上,如果一个女性想在功夫上胜过男性,必须具有非比寻常的力气。比如在1994年的电影《咏春》中杨紫琼饰演的咏春的形象。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红粉金刚”——金刚两个字正说明影片的价值判断,男性是强大的和有力量的,女性战胜男性是因为她具备男性气质。对这种关于力量和柔韧的性别特点的关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最典型的是在体育竞技中男性通过吊环展示其力量,而女性通过平衡木展示其柔韧。在电影《卧虎藏龙》竹林的一场戏中,尽管还不能说李慕白以更具女性气质的轻功彻底挫败了玉娇龙,但至少有一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当玉娇龙施展白鸣得意的轻功以示挑战时,李慕白则用更完美的轻功战胜了她。在两人飞入竹林尚未停下来时,两人的身形如同穿梭于林中的两只白鹭,没有区别,飘动的白衣呈现同样的视觉效果(当然是非常的优美)。而站在竹枝上对峙时,两人已显现出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解释只能是中国功夫概念里的意念,或日“气”。而这种意念又是被相当随意地,想当然地,但是在绝对的支配中建构而成。
发展到今天的武侠电影中,轻功在电影画面中的表现多数和飞翔相联系,即人可以飞翔或者滑翔,不受地球引力的束缚。而追溯关于飞翔的艺术想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龙的形象。中国龙没有翅膀却能飞翔。因为没有翅膀,对飞翔的表现全凭各种意象,以一种含蓄和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它翘首、展尾、屈身、舞爪,时常出现于大海之上、深涧之中,伴着彩云万朵,霞光万道。它形体灵巧,变换多端,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飞翔不是通过飞翔本身表现出来的信息(比如西方的龙的形象即是振翅而飞),而是通过一系列紧密相连的元素传达出来的意义。正如敦煌佛教绘画艺术中的飞天形象,不用翅膀,不用羽毛,一条彩带婉转飘扬,便使得这些天神凌空翱翔,飞得轻盈巧妙、潇洒自如,传达出无尽的飘逸意境。尽管飞天的性别是男女不分的,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她通常是女性的意象,此外我国古典艺术作品中嫦娥奔月和天女散花的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在电影的视觉呈现中,为了表现飞翔这一意境,常常要制造飘动和“风”的意象。比方说摇动的树枝,飘舞的布幔(香港武侠片常常搭建染坊、布店或者挂满帷幔的场景来制造飘逸的氛围),即便是简单到随风飘舞的衣带或长发。飞翔的视觉语境所强调的重点是轻盈飘逸的诗意和想象,但是它同时带来的是一种关于非理性的、神秘化的、不可靠的事物的联想。而女性在文艺的建构中常常正是具有这种特质的——非理性,神秘化。同时按照萨义德东方学的说法,这种特质也正是西方对于“东方”的描述、判断、评价和想象。在西方殖民话语中,“东方”基本上是奇怪的、陌生的、神秘的、不理智的、危险的,愉悦感官的和女性化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影片,《卧虎藏龙》是很容易契合西方人的审美标准的,影片里的视觉元素构成了若干个层次的对立面。影片的视觉叙述首先构建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李慕白飞翔的镜头是很少的,而影片中另一个主要男性角色罗小虎则根本没有展示(或者不会)轻功。与细腻婉约的飞翔风格不同,罗小虎的形象是一种豪放的、在马背上驰骋的速度加激情的形象。李慕白显露功夫的次数不多(相对于俞秀莲和玉娇龙),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并非影片最核心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他稳重的、权威的男性形象。比如李慕白往往一出手就能达到一招制胜的效果;大多数时间他的身体是保持正直的,即使是在击剑时;即使站在风中摇曳的竹梢上也稳如泰山:他可以出其不意地一招夺取玉娇龙手中之剑。在那个镜头中琐碎的动作全被剔除,呈现出惊人的自信、速度和效率。相反电影充分地展示玉娇龙的肢体动作,可以呈现她的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飞翔姿态,当然也不忘记刻画她的面部表情(比如玉娇龙从竹枝上落下时的面部的特写),凡此种种,都是易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所理解和接受的。对于观看影片的西方人来讲,影片的意象不仅构造出了性别的二元对立,也呈现出了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虽然其中的一方在影片内部元素中看似是缺席的。然而当电影观众不是中国观众,而是西方观众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语境下的观看者与观看对象之间的互动。《卧虎藏龙》首先带给观众的是“可观看性”。正如影片的背景宏村,其所展示的古老东方的神秘意蕴不要说对西方观众,即使对国内观众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说历史人文景观在现实中具有可参观性(visitability),那么它在电影里就首先具有迎合男性观众欲望的可观看性(to-he-looked-al-ness)。于是对于女性的观看,对于东方的观看,都被置于同一个想象的空间。这部电影很容易被西方观众欣赏,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撇除了语言,纯粹由影像所构建的叙事策略。虽然作为一部纯粹的武侠电影,影片中没有任何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由图像构建的话语,无时无刻不暗示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观众中的在场。好莱坞评价李安是一个善于抓住边缘人的主体的导演,而《卧虎藏龙》的成功似乎正是由于影片所构造的这种不同的处于对立状态的中心和边缘的重合:男性和女性,理性和非理性,权威和叛逆者,西方和东方……影片以其性别的二元对立重合了关于东方的想象。意义的产生在于文本与不同的期待视阈的融合,对于一些符号只有作为恰当的文化的一员才能识别它们和阐释它们。因此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解读,中国的观众也许会把它看做一个充满张力、直指人心的关于东方哲学的读本;而西方的观众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关于欲望的游戏,只是这个游戏发生在遥远神秘的地方,看似不可能,却也合情合理。
在中国功夫作为影视视觉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大量输出到西方社会的时代,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功夫”?“功夫”是否能够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受《卧虎藏龙》推动而大行其道的国内武侠大片(有不少似乎也是为冲击奥斯卡奖而量身定做的),无不是以追求视觉效果,营造视觉奇观为首要的艺术理念,于是秀美的山川纷纷入画,奢华的服饰道具竞相登场,武侠角色的动作设计越发呈现奇幻不可思议的效果,在影像中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此类影片除了成功复制好莱坞电影生产的商业模式以外,在电影艺术层面却难有大的突破,甚至落入窠臼,或成为技术的滥觞。“飞翔”这一本来极具中国传统诗意的意象沦落为一场技术的游戏和娱乐的对象。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语境中,中国功夫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渠道,最近的几部美国电影如《功夫之王》《功夫熊猫》等都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功夫的书写。好莱坞式对中同文化的再现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国内大量观众的不满:无论是对角色的分配,对功夫内涵的诠释和对功夫形象的再现都带有明显的霸权痕迹。中国功夫似乎还不曾跳出被描绘、被审视的东方学知识体系。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国内电影界难道不应该反思怎样来寻找和重建“功夫”的真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