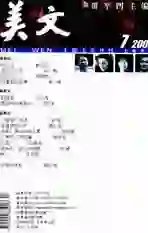我的“留学”生涯
2009-03-29张峻
张 峻
扔下猪,读私塾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从本村小学毕业一年多了。那是日伪政权办的“国民初级小学”,只能念到四年级;再念,需去县城,读“国民优级学校”(相当于高小)。县城离家40华里,爹不让去,说家里没钱,住不起校;爹还说,教书的多是日本人,打学生贼狠!姐说,城里孩子都坏,专欺侮乡下学生。书念不成,就放猪吧。一只老母猪,十多个小猪崽,撒在河旁草坡上,啃那青青的草。我在河边翻石头,捉泥鳅,挺美的。
可叹美景不长。放猪没一个月,我就觉得右大腿根隐隐疼痛,很快,由不敢跑动到疼得不敢迈步。伸手一摸,腿腋处肿起个鸡蛋大的硬包,爹不看一眼就说:长脓疖了,不碍的,挺几天,等它长熟了,爹给你放脓。他轻声一笑:别怕,脓一放,比不长还舒坦哩!我听信爹的,就咬着牙硬挺,没两天,随着疖子的肿大,里面像刀剜一般的剧痛。爹用手一摁,说快熟透了,再挺一天。第三天清早,爹趁我没起炕,找来一把剃头刀,揭开我的被子,上炕就抬屁股死死压住我的两条小腿,猛一刀,就将脓疖削破。我尖叫,立马觉得热乎乎的脓血顺腿腋流淌。爹不顾我的疼痛、哭喊,还用力将疖包挤了挤,又抹了下,说声完了,才松开我的腿。疖子被放了脓,我并不觉得怎样舒坦,反而觉得更加疼痛。爹并不懂得刀具消毒,疮口很快被感染,发炎、流黄水,疖包红肿得像发面馒头,一连好些天下不得炕。爹就在我身边砸酸枣仁,用勺焙熟,让我吃,吃得我昏沉大睡,爹就乐。
就在我昏睡那几天,村里发生了亘古没有的事——鬼子兵在戏楼下放一回电影!我疮痛卧床,没能去看;哥哥姐姐们看罢回来,眉飞色舞地说:神啦!电影里割草的人,活鲜鲜的,像个真人;柳树也跟真的一样,随风摇动;鸭子就在池塘里凫水……现在我想,许是风光片或记录片;可那会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戏楼前咋会有柳树和池塘?哪有什么会动的人和鸭子?半个月过去,当我的疖疮癔合后,能走路了,赶忙到戏楼下放过电影的地处去看,那儿依然是干硬的场地,火烤似的阳光,根本没有什么人和柳树、水池、鸭子凫水?电影的神奇,憋闷了我许多年,也抱憾了许多年,直至解放后在承德第一次看电影……
疖疮痊愈,爹不知为什么,不让我放猪了。姥姥家来人说,他们背着日本人,偷偷办起私塾,专教孩子四书五经,全是念中国书,学中国字;念那点洋文没用,鬼子占不长。妈就劝爹:让二子去念私塾吧,下地干活他还小,多识几个中国字,能记个账、看个信啥的,比啥都强。爹深知不识字的苦,也真想让我多识点字儿;可他搓着额头说:那得驮去七八斗小米呀!妈惊讶:咋会那多?爹掰着手指说:听说束修钱一季一斗,孩子的吃喝每月至少一斗(每斗约36市斤),半年哩?你算哪!妈撇他一嘴:净算瞎账!孩子在家就扎脖颈,不吃饭啦?爹有点儿不情愿地:那你就给二子收拾一下。收拾,即做准备。除我已有的启蒙小书,又托人从县城买回《论语》、《孟子》等书;在衣着上,妈用尽家里所有的“配给”布,给我做了一身带双兜的黑布裤褂,还有新鞋白袜。用妈的话说:出外不比在家,咋也得有个新样儿。
三道沟深不可测
姥姥家离我们镇子说是十五华里,其实过大河钻沟翻梁要走小半天。那天,黑毛驴驮着五斗米,爹还扛着二斗——他怕驴累着。黑驴吭吭哧哧地沿山道爬行;爹满脸淌汗又气喘吁吁。正是酷热仲夏,道旁山坡花草盛长,虫鸟欢鸣。我小心地夹着书包,什么也不敢看,也不想听,只是低头盯着爹的脚后跟,小心走路,生怕跌下沟坎;心里一直犯嘀咕:啥叫私塾?跟镇子里念日语的洋学堂有啥不一样?教书先生是怎样的人?打不打学生?我暗自想象着,憧憬着,忧心着……
姥姥家的小地名叫三道沟,是真正的深山老峪,和我们的村镇大不一样。虽说同属山区,但我们镇子河川很宽,西边有条大河,东山与西山相距二三华里,河两岸是大片平整的农田。河东岸沿河湾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当算小镇子。姥姥家山高沟深,蓝天很窄,人走在沟底就像掉进坛子里。贴北山根聚集四十多户人家,还用高墙圈着——那是日本人强迫百姓修的“部落”,人们叫它“入圈”。原先这儿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其余的二十来户全是从周围小山沟搬迁来的。这叫“集家并村”,说是“防共”;我们在伪满初小,也搞过什么“灭共日”,教员们教唱什么“防共歌”,其时共产党就在父老兄弟中,防不胜防。三道沟的南北两山相距特近,人们坐在炕上,能瞧清楚南山上的风摇橡丛,以及枝梢上起起落落的山雀。农田就像一块块布帘,挂在岭坡上。这儿当算真正的大山沟。更让我纳闷的是,说去姥姥家,爹却领我去了一位远房的大舅家。大舅叫宋勋,高石阶上破旧院子,还算是宽绰的三间北房,房台下的两边是粮仓屋和农具房。后来得知,大舅的父辈较富有,自打日本人强迫村民种大烟,大舅便吸大烟成瘾,可又因自家种大烟,大舅每年都设法少交烟干,勉强留够自己吸的;加之我的大表哥很能干,种着四十多亩山地,一家人吃穿自足,爹才将七斗米放到大舅家,并要我在他家吃住——此举竟惹起我亲姥爷的极大愤怒,这是后话。
那天在大舅家吃过午饭,已是后半晌,由大舅引领,我们爷俩走进庄后紧贴北山根僻静的三间草屋。一间是先生和家人居住,另两间被打通,摆放着形状不一的民间桌凳,分桌坐着二十几个学生。先生清瘦的长脸庞,两只带双眼皮的大眼睛,一副偏厚的嘴唇,约四十岁左右,身着长袖灰布衫,说话慢声细语,很像城里的买卖人。后来我知道,先生果然在城里西街开过店铺,他姓冯,名宝璋,自幼熟读私塾,因生意败落,才由亲戚引荐,冒险来山沟教私书。先生微笑着和父亲说了些什么,我没注意听。大舅和父亲一走,先生就让我站到教桌前,介绍给众同学。
听说我是从大镇子来的,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中有些人期盼着进洋学堂,因为想谋个伪差,必先读几年洋书;他们想不到念过洋书的学生倒来这儿读私塾。面对一双双异样的目光,我聆听着先生有关“学规”的训示。在先生的教桌后面,依墙供奉的是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牌,先生告诉我,众弟子每早要对先师牌位鞠躬敬拜;学生每天要规规矩矩在自己的坐位念书,不得说笑、串位、打闹,如若违规,戒尺(一条打手掌的硬木板子)严惩。让我至今不忘的是放在圣龛前的那个写着“出恭”二字的小木牌,谁若外出如厕,必须拿上这个牌牌;假若“出恭”牌被别人拿走,你再内急,也不许出走学房,哪怕屙尿在裤裆里……很久我才明白,先生所以这么规定,是防止两个以上学生同时出去就会玩耍或打架,因为茅房就在屋后,转过茅房钻过部落围墙的防水孔,可以径直登上北山,捉蝈蝈、逮蚂蚱、拾雀蛋等戏耍极容易。
念私塾十分呆板、困顿。开蒙学生都须从《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名贤集》依次读起,而后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每天由先生“号书”,即:指定读书段落,然后自己去读,不会或忘了可以问先生或身旁同学,临放学
前要到圣桌前背书,即将书本交给先生,随即转身背书,背不过就挨手板或用教棍敲头;不用心读书而又违纪打架者,常被罚站或不准回家吃午饭。谁有死记硬背的过硬的本领,谁就是“好学生”。通常,先生也坐在圣桌前陪读,边读边监督学生。先生在场,大家都摇身晃脑地高声朗读自己的书,学房内一片嗡嗡声;先生一旦离座出屋,读书声就乱了调,甚而互相打闹,小动作百出。为杜绝混乱局面,先生便指定一学生为“大学长”,如先生不在时由大学长全权代管。一般是读书最多、学习好的学生为大学长。
大约一个月后,我便被先生指定为大学长。尽管我是晚入学两个多月的插班生,但我读书最快,没一个月,便成为读书最多者。因为《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以及《大学》、《中庸》等,我在念日伪初小的寒暑假期间,都偷着学过,是校长徐化民背着日本人教的;有的还给讲解,如《三字经》中讲历史的一大段,徐校长明确指出:这就是我中华民族历史的“小纲鉴”,记住这些,就大体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名贤集》里为人做事的一些语句,在徐校长启发下,我也能懂其中的意思。一般说,弄懂的东西最容易记牢。因此,在读私塾的近一个月中,我等于把上述书籍重温一遍,再一次逐段、逐篇地背记。我学习之快,令冯先生惊叹。也就在这时,我爹来私塾看我,先生喜盈盈地一再夸我聪明,还说了“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赞语,意在讨取父亲欢心,要他下决心继续供我读私塾。
当大学长和读《论语》(上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记住“子日,学而时习之”于我并不难,难的是大学长怎么当?在二十几位同学中,我是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矬者之一;可那几位学习差又爱打闹的同学,都长得身高马大,还横不讲理。我对付他们的办法,一是尊重,二是威吓。在三道沟,基本上是刘、宋两大姓,加之两姓几辈联姻,论起来他们多是我的舅舅或姥爷,当他们打闹时,我就喊:姥爷舅舅们,别准为小外甥了!我这么一喊,他们多都有所收敛;如若个别人再闹,我就威吓:你不会的别来问我!有人还真怕这一招,书背不过要挨手板的。但无论如何我不会用“告诉老师”相威胁,那样会把关系搞僵,我也就不是他们的好外甥了。“大学长”和“小外甥”的地位,使我得到尊重和爱护,他们时常拿来饽饽或采摘的水果给我吃,先生发现了也从不干预。有位姓盛的小同学,和我最要好。在我没当大学长之前,他常挨欺负,一是个子小,二是外姓,加之他父亲盛子章长久外出无音信,孩子们常骂他“野种”。他真心和我好,我便处处护着他。万没想到解放后的1950年代初,承德地区冒出一位专治性病的专家名叫盛子章,当了地区中医院副院长,一细问,果然是盛的亲生父亲。盛来承德看望父亲时,也顺便到我家,那时我已调承德工作,我们笑谈那段童年友情。
姥爷,姥爷的家
现在回想起来,读私塾也并非死读书。尽管没有上下课活动时间和星期节假日啥的,也时不时穿插一些别的课间事项,譬如,写仿习练毛笔字或由老师领读吟唱《千家诗》等,以调节孩子的学习兴趣。记得上学没两个月,老师就回县城买来写仿纸,并给订成大本本,然后由他给写成“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的大字仿样,夹在本本里,让学生们照仿样书写。写仿与唱诗课目,多都留在下午放学前的一小时,恰是孩子们读书疲倦的时候,所以大家兴致极高,天天喜盼这一小时。再是,老师回县城或临时有事外出,也放假半天或一天;甚至两三天。这样我就常有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回亲姥爷家,有时跟随舅舅们上山,也有时帮助大舅家干点小活儿。
姥爷家原先住在小后沟,是日本人搞“集家并村”搬迁到这庄的,就住在庄西的道坎下。住房很窄,与别人合住三间屋,中间是两家合用的厨房,全家五口人只睡一铺炕。这五口人中除我姥爷外,还有我二舅、五舅的夫妇四人,我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睡?屋小炕挤,也许是爹不让我住姥爷家的原因之一?再是,姥爷家山地极少,日子紧巴,多半日子吃糠咽菜。尽管如此,爹不让我住亲姥爷家而去住远房的大舅家,无论如何是让我亲姥爷脸上无光。记得我第一次去姥爷家时,姥爷激愤地骂道:你爹缺人味!嫌我穷?怕我家抢了你的食!说得我脸颊火辣辣的,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姥爷虽然怨恨我爹,心里还是很疼爱我这个亲外孙的。我每次去,他必留我吃饭。其实,我很爱吃姥爷家的饭,虽说不是纯米净面,但那些莜麦面掺野菜做的“苦力”、豆角山药面条、煮嫩玉米等,我每每都吃得撑肚皮。我特愿意去姥爷家,稍一有闲空就想去,不单是血缘亲近,总觉得姥爷家比大舅家热闹,是消闲、凑趣的好去处;尤其到晚上,炕上、地下满屋子都是来串门的人。而且爱说笑、打闹的青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撺掇姥爷说书、讲古(姥爷能抱着三弦自弹自唱,能说唱成本的《瓦岗寨》、《杨家将》、《说岳》等),即便不说书,大伙儿也愿意与姥爷扯闲,天上地下、庄里庄外什么都说。给我的感觉是,这深山沟比我们大镇子语境宽松,山民们什么都敢说,狠骂鬼子、汉奸。在我们镇子,不单大人们说话谨慎,还嘱咐孩子们: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嘴”,小心被当作“思想犯”逮走。小铺子和店家,墙上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提示。镇里的敌伪人员多,除了村公所、警察署、协和会、鸦片组合里的无数双贼眼,还有化装成行商、小贩、乞丐等众多便衣特务,真不知哪句话犯歹被抓走。我的三舅和六舅就是从我们镇子被抓走的,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当劳工。六舅死在那里;三舅是苏军进攻东北时才逃了回来。我实在没想到深山沟说话这么随便,还常有个把新面孔,与姥爷神神秘秘地说些什么。有一次我偶然听他们说:“小后沟夜里被人们踩出一条新道,是有队伍北上开辟工作……”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只觉得姥爷在当地很有威望,直至日本投降两年后,闹“土改”斗汉奸时,姥爷当了本村的“人民审判庭”庭长,他在主审“犯人”时,幕后指挥他的我党工作人叫程超杰(后来是隆化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当地主武装“自卫队”突然来进攻,程带着工作人员跑进大山,当“庭长”的我姥爷被敌人抓走,五花大绑带到大营子,打得皮开肉绽。还是我爹托人送钱,才保住姥爷的一条命。当然,我更不知道我二舅是三道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直至他病逝,身份自然是农民。当时我只知道,姥爷在屋地的北墙角挖了个地洞,很深,很大,能藏下五六个人。冬季将土豆、萝卜也放在洞里。晚上我去姥爷家,没别人时姥爷就下洞给我取萝卜,个儿不大,挺甜的。
堂舅的家很温暖
其实,宋勋大舅一家待我不薄。虽说不是亲舅,但与我家相互走动得较勤,正像俚语说的:“亲戚不在远近,能常走动才亲。”大舅每年夏天去镇上鸦片组合交大烟干,就住在我们家。因为他抽大烟,总想少交点、多剩点,大烟里掺些假膏子,然后再托门子、送礼去交,交不了就住在我家等机会,转天再托人去交;有时候去找伪职员玩
牌,故意输给人家,借以交友。就这样,他在我家一住十天半月是常事,我爹就酒菜待承这位堂内弟。我念私塾所以住大舅家,想必是爹和大舅事先商妥的。
大舅家人很多。他们老两口之外,还有表哥表嫂三个表姐一个表妹两个表弟,共有十口人。我去之前,大表姐刚出嫁。我与表哥表嫂住西屋,余外七人皆住东屋,一铺大炕,齐刷刷一溜人头。不过两个表弟尚小,一个三岁,一个不满一周还在吃奶。表嫂虽然结婚有年,生育两个孩子皆都夭折。表嫂是大舅家最忙碌的人,也是我最同情的人。她那年二十四五岁,个儿不高,圆盘脸儿,不胖不瘦,特能干。一天三顿饭、喂猪、推碾磨面等全是她一个人干。稍有空闲,还为大舅妈抱孩子。我印象中,她总是小碎步走路,忙迭迭的,极快,像一个球满地滚。就这样,还常挨大表哥的打,公婆的辱骂;小姑子们很少帮她。有苦无处诉时,就和我叨叨;我也只能听听。大表哥小她四五岁,那年也就二十岁出头,精力十足又能干。听说他十一岁就会扶犁赶大车,庄稼行里没有他不会干的。白日死受一天,晚上还外出串门子,常是半夜才归。表嫂疑心他有外遇,我想多半是冤枉他。据我所知,晚间他多是在我姥爷家听书、扯闲。表嫂晚间睡不着时,就和我叨叨:你大哥又去××骚娘们家了!我说不会的。她说你太小,啥也不懂……说着说着就蒙头哭泣起来。她睡炕头,我睡炕梢,相隔一丈远,我心疼她,可不知该怎样劝她,不知啥工夫我就睡着了。当大表哥夜半回来时,又常常把我惊醒;可大表哥躺下时,总问一声:二兄弟睡啦吗?我就装着深呼吸不吱声,他俩就“忙动”起来。我弄不懂他俩忙什么?有时“忙”中表嫂审问起大哥,两人就低声争吵,有时还动起手,我仍然装作不知,还故意打起呼噜……
在我眼里,大哥绝对是好大哥,表嫂绝对是好表嫂。大哥很喜欢我,在山里干活时,采回野果或鸟蛋总想着我。我每次回镇子探家,隔LU隔河他不放心,总是借个事由陪伴我;他走路很快,我跟不上,他就扯着我慢走;过大河时他就背着我蹚水。路上,常讲他儿时不愿念书,逃学、贪玩,喜欢放牛或跑山、干活,没少挨我大舅的打。表嫂像疼爱亲弟弟一般疼爱我。总嘱咐我用心念书,别想家;正在长身体时,每天三顿饭都要吃好;常替我洗换下的衣服,说我:干干净净才是好学生。冬季日短,山村吃两顿饭,吃晚餐时,也就是下午四时左右,晚饭后要去学堂念两个多小时的“夜书”,大约晚九点我回到暖屋时,火盆里总温着满满一砂锅高粱米豆粥,柜边放着碗筷和一小碟咸菜,砂锅热粥别有香味,吃得我通身暖烘烘的。被褥早被表嫂铺好,当我钻进暖被窝,许久寝沉在“老嫂比母”这句温馨的乡间俚语中。只可惜,这位好表嫂应了人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命”。相隔十七年后的1962年的初春,我作为报社记者路过三道沟,痛获表嫂中年早亡的信息,我悲戚飞泪。她给大表哥留下两个儿子。我去看望了大表哥,他这时才痛心疾首地诉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表嫂。两年后我又一次回家,听说大表哥仍然独身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不过这时他真的有外遇了,村人都理解他,那年他才是三十七岁的汉子啊!他曾捎话说:挺想我的。可我没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至今心中有愧。他如若活到今天,该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二表姐大我两岁,三表姐与我同龄,在乡间都算是小丫头,她俩都尽心关照我。平时我并不觉得她俩对我怎样,一旦先生有事放假,我不上学了,她俩特高兴,总是找个因由陪我逛山。并说:成天念书脑子会累坏的,快出去散心放飞吧!我们就一起上山。仨人都挎个小篮子,有时是钻高粱地摘豆角,有时是沿地碣采野欧粒吃,或攀野坡采摘山梨,跑呀,乐呀,特开心。只是谁想“方便”时,总得跑得远远的,相互看不见,我对此十分不解。一次采山梨,硬是让我去坎塄下小解,我刚解完,晃见一条“大狗”站在沟畔,两眼直愣愣地盯我。我害怕了,岔声岔气地喊叫:狗!狗!狗!二姐三姐赶忙跑来,急喊:别怕!那是狼!野狼!说着,两人一齐猛然跳下沟坎。许是她俩纵身一齐猛跳,吓得那野狼调转头踅坡飞跑,很快消失在山半腰的荆丛中。二姐急忙凑近我身边,安慰我:吓着了吧?没事啦!狼跑远啦!我嗫嚅着说:我,我从小就怕狗。她说:别傻啦,那是狼!狼会咬小孩的!她并告诉我狗和狼的区别。狗常是卷着尾巴,狼总是耷拉着尾巴。狼的毛色也随山变化。夏天多是灰中偏青,秋后多是灰中偏黄。听她这么一说,我好后怕。假如我平时不怕狗,今天一定会去主动亲近那只老狼,后果一定很惨……那夜我真的做起噩梦,又在荒野里碰见那只老狼,可我并没害怕,因为老狼被二姐牵着,三姐骑着,老实的像只大绵羊……
来了马达子
想起两位表姐的好处,不能不说那次庄上来马达子(土匪杆子)。已进农历七月,天亮得特早。睡意蒙眬中,被表嫂喊醒。她急惶惶地说:二兄弟快起!来马达子啦!我禁不住一惊。
马达子是什么我是知道的,但我从没亲眼见过。常听娘说,我就是闹“二虎杆子”那年出生的。“杆子”也是土匪队的别称。那年日本鬼子占领热河,同时也闹起匪患。“二虎”是大土匪头子的字号,他的队伍上千人,竟然攻进隆化县城抢劫大商号。路过我们镇子时,娘生我正“坐月子”。土匪进我家并没抢什么,反倒扔给我家几件从县城抢来的衣服。当我长大后,土匪不再进大村镇,只在山沟小庄活动,他们不打鬼子,串山沟只为抢钱、抢大烟,鬼子也就不想消灭土匪。据说,我姥爷和二舅曾想联络一干土匪打鬼子,终没做成。现在马达子进庄,我虽吃惊,但并不怎么害怕。我边穿衣边四下张望,问表嫂:马达子在哪儿?表嫂说:这还用问?她抬手一指:南山后山全有持枪站岗的!我扒窗缝一看,南山最顶峰一丛枫窠旁,果然有个背着枪的便衣,似动不动地晃身。我又问表嫂:饭做好了吗?我吃点,好去上学。表嫂站在柜旁不动身:上啥学呀!一来“杆子”,先生就不敢开学房门了,他怕……我急问:他怕什么?表嫂说:怕担干系呗!万一谁家的孩子在学堂被“杆子”绑了票,家长得找他赎人。我们正说着,大表哥慌慌张张地进屋,说他本来扛锄去耪地,土匪在“部落”大门站上岗,许进不许出,下地干活也不准!一定是怕走漏风声。大表哥还说,部落警察的两条枪也让土匪扛走了;听说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怕土匪给裹走。他也想找地方躲一躲。他刚一出门,又回过头说:对了,西院四奶奶家住土匪啦,四奶奶让你过去帮她做饭;你可要长点心眼儿。
大哥、大嫂走后,西屋里静得疹人。我知道,这时东屋里也只有二姐、三姐。大舅前天去了我们镇子,还没回来;大舅妈和四妹并两个小弟去了梁西娘家。二姐、三姐听说来了马达子,急霍霍地跑过来。我问:咱咋办?二姐说:不怕的。她嘴说不怕,却去灶坑里抓一把草木灰涂了脸,随手又用沾满灰的手,把二姐我们俩的脸也给涂了。然后她又回东屋找来破旧衣服,让我俩换。我一看,衣褂很破,还都是有花的,真不想换。二姐说:不换可不行,就凭你这衣着,土匪兴许把你当成
财主秧子给绑了票,我家可没法向大姑父(指我爹)交差!她说着,就动手强行把我的上衣给换了。
亏得二表姐好心。那早我们仨刚吃过饭,就听得院门外有杂乱的脚步声。二姐说声不好,用力把我推上炕,又拉开被子给我盖上,并在我头顶上挡个枕头,让我阖上眼装睡。土匪们很快闯进屋,见东屋没有人,就扑奔西屋来。我眯斜着眼一瞄,至少有三个,都挎着大枪。为首的一个先问:大人们哪去啦?二姐、三姐齐声答:去西院给你们做饭去啦!许是她俩同声回答,匪头没再追问,转而指着我:他咋啦?二姐答:我老妹病啦,闹伤寒症哩!土匪们没有再问什么,立马转身又去了东屋,揭柜盖、翻桌橱,也没翻出值钱东西或大烟。“晦气!破大家!”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事后我才听说,那天土匪真的绑走两个学生。一个是刘甲长家的二小子;一个是东头李春家的大孙子。半个多月后,才托人花上百两大烟土赎了回来,险些被撕票。大舅、大舅妈回来后听说此事,都夸二表姐机灵。
欢乐、抱憾与思念
马达子在三道沟只住两天一夜,第二天深夜就撤岗溜走了。他们抢走了部落警察两条枪的事,镇警察署肯定知道,据说他们当时很犯难,既不敢派警察去追赶马达子,又不想向县警务科报告,可就在这两难之时,警察署忽然得到新情报,说我姥爷与“土杆子”有过勾连,决定缉拿我姥爷,并以此上报“匪情”。可老天爷护佑了大好人我姥爷:警察的日本爹突然宣布投降了!
信息是去镇上交大烟干的人带回来的,开头谁都不相信,很快又被从县城回来的人证实了,说满大街贴大标语,欢庆祖国光复。小山沟也立时沸腾起来。我二舅去东庙找来锣鼓和大鏊钵,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边敲边喊嚷:日本投降了!小鬼子完蛋了!满洲国垮台了!他这一喊,在家的女人、孩子们也都跑了出来,有的孩子跳着高呼喊。人们议论国事再也不是晚间扎在姥爷家的小屋里,偷偷摸摸的;而是站在庄街上或街中心的墙弯处,大呼小叫的,争说自己听得的最新信息。有人说东川过老毛子(即苏联红军)了,缕缕行行的不断线,已经进占隆化县城。欠大烟干、欠荷粮、欠税捐的都不用交了!转天,又有人从我们镇子回来说,咱西川过的是蒙古骑兵,进镇子里的百姓家都不下马,在镇街外扎帐篷,烧啃牛羊肉,带着血丝就吃;最诱人的信息是,在镇子、在县城,人们开始抢荷粮仓库、抢“大满号”(大满鸦片组合的简称)。苏军和蒙古军都不管,他们抱着大枪,坐在房顶上瞧热闹,见人们提着铁桶,为夺抢大烟打架,他们就拍着巴掌狂笑。有的满洲军和警察,竟然持枪抢劫,一再将人们抢到手的大烟劫下。还有的人怕别人半道抢劫,就只身跳进大烟缸里,蘸滚得满衣裤全是大烟浆,回到家再剐洗。我还听得,在我们镇子,就在我们家后院荣家,日伪的一座粮库,正好连着荣家的房墙,就在一伙人闯进粮仓抢粮时,老荣头急中生智,竟然把那隔壁墙凿开,官粮便自动流入他家的屋里。
听得镇子里这么热闹,我特想回家亲眼看看;可是,正赶上连雨天,半个月不开晴,几乎天天下雨,那雨时大时小,下得壕满沟流,镇边的大河涨水,浊浪超过半房高,姥爷舅舅们谁也不敢放我回家。可我心急火燎,总想看看蒙古兵啥模样,人们抢粮、抢大烟的红火热闹。我走不成,每天抱憾地叹息:嗨,这么热闹的日子,真该亲眼见识见识。家里的人咋样了?镇子里的洋学堂咋样了?同学们都在干啥?他们一定都很开心;我却猫在深山沟里,啥也见不到、听不到?闷死了;不过,鬼子一跑,再也不怕上边查私学的了,我们念私塾合情合理合法,更敢放声朗读了。还有,每晚都有外地传闻,听得很有趣,很开心。譬如,以往钻山沟的土八路,如今进了县城维持秩序,身穿便衣的县长,蹲在墙根下断案子(许是夸张?),让百姓们称他“同志”。我听着很新鲜,津津有味。不久又传来城镇都在搞“清算复仇”,斗争汉奸,枪毙伪警察署长……
开开心心的雨季过去,很快凉风徐徐,秋天来了。早熟的庄稼开镰收割。群山也开始变颜变貌,那原本青一色的灌木葱茏的岭坡,渐渐隐现出点点、片片的红黄橙绿,表嫂叫它虎皮色。这时刻,我不知为啥,最怕仰望窗外看南山,跟随先生吟唱《千家诗》;尤其那些“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朝来人庭树,孤客最先闻”、“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不知咋的,我一碰到“孤舟”、“孤帆”、“孤客”等词句,就悲戚自己只身在外的孤单,想念镇上自己的家,想念妈妈,想念哥哥姐姐和同学们,有时从学房回到舅舅家还闷闷不乐。表嫂见状,就打趣地奚落我:小小子,坐门墩,皱着眉头想媳妇……我就更不给她好脸子看。
随着天气变冷,学房里没有炉火,我就想:该放学生回家了;可先生又放出话儿:私塾学堂都要念冬书。冬天念书,首先要有暖和的屋子。先生的办法就是带领学生们上山,搜寻干柴和刨木头疙瘩。上山,是学生们最高兴的事,就像放出笼的鸟儿,撒欢的小狗。尤其那几个脑子笨、念书吃力的学生,跑山、拾干柴、刨疙瘩特显本事,也肯卖力。他们带的筐篓大,拾得干柴、刨疙瘩也多,有些半裸露的疙瘩,他们都下猛劲拽了出来,尽显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也博得了先生的赞许。大家连干两个白天,院子里就堆起了疙瘩山。先生找来两个铁火盆,由学生轮值拢火取暖。可我们万没想到,有不少干柴、疙瘩是朽木,光冒烟不起火苗,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呛得学生连声咳嗽眼流泪,根本读不了书。这时,先生只得将门窗打开,烟虽然腾上半空,也同时放走热气,屋子照样冰冷,冻得手脚麻木。我就在手脚冻伤的状况下,读完《孟子》的《万章》篇。这时,已进入腊月,学房里更冷了,老师还不放假,又让我读起《农用杂志》与《尺牍》,并且亲慈地对我说:看你爹的口气,过了年不会再让你来了,读读这些杂书,过农家日子都用得着。当然,他也不再提“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话。尽管杂书上面全是“锄镰镐杖,碾磨豆房,木锨板斧,汤匙瓢盆”等农家常用字,以及《尺牍》上那一篇篇很实用的书札范文,我深感冯先生的好意,这也是父母对我所希冀的:“识点庄稼字,记个工夫帐”;可我的心已经不在书上了,因为每天总能听到庄人杀年猪的嚎叫声,我读书时老想,我家也该杀年猪、淘黄米、做豆腐了……就这样,离年还有半个月,我就离开了三道沟。
如果说,伪满初小四年是我的正式学历,那么,在三道沟读的半年私塾,该算我少年外出的“留学”生涯。不过后来我时常回味:我在三道沟所学到的不完全是孔孟之道以及之乎者也矣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