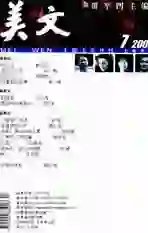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
2009-03-29桑麻
桑 麻
我们村张铜拴老婆从茅坑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消息传开,村里很快炸了锅。人们猛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时日没看见她了——那个平时不爱说话,术后更加沉默,说起来又开闸放水般收不住话头,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不着调儿的女人。他们大多知道她脑子出了问题,谁也不会想到说没就没了。
她是在进入那个公厕,突然发病一头栽了下去,还是蹲在条石上犯迷糊才出现闪失,或者已经收拾停当准备离开,却一脚踩空丢掉了性命,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了。除了他的家人、亲友会怀疑和追问现场究竟发生过什么,谁会过于在意呢。反正是死了,打发死者入土为安最要紧,何况村人了解她平素的情况,搞不搞清楚又有多大意义呢!
听说最早发现她的是一个路过的女人。她在树下支好自行车,匆匆走进了前墙刚能隐身的公厕。当她透过自己岔开的双腿,看到茅坑里还有两条岔开的腿时,想要轻松的念头一下子跑到了九霄云外。她叫娘杀老子般地窜了出来。她手提着裤子边跑边喊,吸引了过往的目光。那些爱管闲事的路人,还有马路两边的住户,闻讯纷纷跑了过来。他们进入厕所瞅上一眼,慌忙退出来,一路小跑着回去,找出了粪钩和铁筢子,有的顾不上多想,顺手掂来了铁锨和粪叉。他们神情紧张地挤在公厕里,一通忙乱,钩着她的腰带和衣服,把她从一米多深的茅坑弄回到了地面。
她的头上、脸上、手上、脚上和衣服上,全都是臭哄哄的粪便和蠕动的蛆虫。人们把她弄到路边硬地上,成群的绿头苍蝇飞了过来。有人从车马店掂来了两桶清水,朝她的头脸哗哗泼上去。她年轻苍白的面容露了出来。有胆大的歪着头上前,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指指戳戳辨认着,最终,都摇摇头失望地退下来。
一个胖呼呼的男人扒开众人凑了上来。他看到了地上软绵绵的尸体和湿淋淋的头脸。他倒吸了一口冷气,知道他们担心的事情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他是一家乡村精神病院的厨师。当医生发现住进来没几天的女病号又一次不见了时,再次打发他出门寻找。他顺着公路骑出十来里地,看到了人们正从公厕往外抬人的场面,很快,他吃惊地认出了那张刚刚熟悉没几天的面孔。
那天上午,我跟支书在乡里参加计划生育调度会。会议结束时已近晌午。我们在“一叶春”喝了两杯,随后到和平澡堂泡了半天,又放松地睡了一觉,才回到村里。我们刚在支书家的院子里坐下,张铜拴就找上了门来。
铜拴听到他老婆的凶信,是被从地里叫回来之后。他大哥带来的消息,让他半天回不过神儿来。他在五天前刚把她送到那家医院。院墙上“视患如亲”的字样,老医生的和蔼慈祥,让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的女人胆小自闭,不轻易外出走动,也不爱与人凑伙儿,时常一个人对着墙角儿、门旮旯发呆,偶尔嘟嘟囔囔的,好像有人隐身跟她对话。老医生的印象是,她患了精神强迫症,病情还在发展,但他保证,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完全可以让她恢复健康。
铜拴脑子里嗡嗡作响,乱作一团。他知道让她恢复健康,连神仙也做不到了。
他的大哥已经把家族中比较亲近的成员召集了起来。他带着几个中年人前往精神病院交涉。他的兄弟和几个年轻人,开着一辆三码车、三辆摩托车赶往出事地点。与医院的交涉还算顺利。医院没有看护好病人,导致出现意外,自知责任不可推卸。为了减小影响,为了声誉和以后的生意,他们忍痛赔付一笔钱以为了断。他的兄弟们行动更快,不到三个小时就拉回了尸体。
铜拴让他七岁的儿子给我们下跪磕头。我们少不了一番安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让他尽管说。铜拴红着脸,努了半天嘴,憋出两句话来,我老婆是后遗症……跟结扎有关。……乡里得赔偿。我跟支书谁都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吃惊地对视了一眼,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铜拴老婆是头年秋罢做的结扎,那天,是我安排车辆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他老婆迟了很长时间才过来。她裹着一件皱巴巴的枣紫色碎花缎面的夹袄,大概临出门才从箱子里翻找出来。我心里着急,没有给她好脸色。头天说好的事儿,还磨蹭这么长时间,让大家干坐着等你。她没有还嘴,低头上了车。
午饭过后,做了结扎的四位妇女又同车回来了。他们轻声说着什么,偶尔讥诮地开句玩笑。他们想笑又不敢大声,张开嘴,捂着肚子,一副奇怪难忍的表情。铜拴老婆闭着眼,紧锁眉头,仰歪在后座上叹气。我们挨门儿送她们回家。别人都是自己下车往家走。铜拴老婆格外小心,好不容易从车上下来了,没走两步坐在了大门口。她情绪低落,满面愁容,别着脸揉了一会儿眼睛,才由铜拴和她妹妹搀进了院子。
她感觉腹部不适,下意识地在衣服外面摁来摸去,结果真让刀口发了炎。别人很快恢复如初,她却因为输液推迟了几天才拆线,从此像瘟鸡一样打不起精神。
她的性格开始有了变化。她平日跟街坊来往不多,后来完全中断了;从前碰了面总要打个招呼,后来看见了就远远地躲开;再后来,出门也少了。多数时候寡言少语,偶尔又突然话多起来。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想三言两语打发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气儿诉说着。她说自己很长时间睡不好觉了,有时整夜做梦,有时刚一合眼,看见一个白布蒙面的陌生人,露着两只小眼儿,握着一把银亮的手术刀站在床边,要她脱光衣服,准备手术。她不敢不脱,胆怯地分辨着,我已经做了结扎。陌生人说,我们不管那个,只管手术。乡里把你送来了,你就得做。她蜷起身子瑟瑟打抖。陌生人不再说话,照她脐下三寸狠狠拉下。她大叫一声惊醒,冷汗顺耳而下。她心慌意乱,再也无法平静。她听到院子里有了响动,断定有人来了,连声喊铜拴起床,把他们轰走。铜拴经不住她一再吵嚷,披上衣服走到院里,把大门吱呀呀打开再关上。
我劝她放松一些,那些没影儿的事,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全乡二十多个村子,九千育龄妇女,一年少说要做三千例手术,从未听说出过什么事,到你身上就有问题啦!她一本正经地说,病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他们把我身上的东西拉掉了。我问拉掉啥了。她说肠子、肚子(胃)。他们给我结扎的时候,偷偷拉下来,卖给走后门的病号了。我笑她越说越离谱。她说你别笑,我一点也不骗你,肯定给他们挖走了,要不肚子里怎么总是像绳子拧着一样,有时候呼呼进风,几条被子都挡不住。我说,动了你的肠子、肚子,吃饭能没有感觉。她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怎么没有感觉,要不吃点儿东西,总是撑得受不了。他们切走一块,我的肚子变小了,容不下了。
我受不了她死缠活搅,竟也较起真来。我送人多了,手术上的事比你清楚。你知道啥叫结扎?说白了,就是把输卵管打个回弯,捆扎一下就完了。我弯下食指示范给她看。以前把回弯底部那一段切掉了,后来不切了,用手术钳夹一下,让它粘住。根本没有动别的东西……。该切的都不切,怎么可能切了其他。她将信将疑,很快又不以为然。这时,铜拴远远走了过来。我说回去叫铜拴问问医生,看切了没有。铜拴连呵斥带劝地把她领回去。
只字不提她的死与结扎有关。至于补偿的理由,可以说乡里出于人道考虑,从民政救济款中挤出一些,给予特别照顾。二是乡里跟你对口,你跟死者家属对口,双方互不见面。现在不见,以后更不见。人埋了,钱领了,就算两讫。三是你必须保证他们今后不找后账,不能以此为由上访,如果上访了,首先抹掉你的支村两委职务。提醒你一句,如果说话不算数,等于自毁名声,将来不会有人跟你打交道了。
书记的话我全都接受下来。其实,铜拴初次来找,我就有言在先,你上访的理由不充分。争取上了不必感谢,争取不上不能埋怨,更不能闹事。想要闹事,直接绕过去我们最好,我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了。铜拴答应说,争取不上只有自认倒霉,照样会埋人……。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第三天中午,随着一声老盆摔碎的脆响,拉着铜拴老婆灵柩的拖拉机开出了村庄。我长出了一口气。
葬礼结束,铜拴在院里摆了三桌酒肴酬谢忙客。我跟大家碰了几杯,吃了馒头、熬菜,骑上摩托车直奔乡里。
书记昕完汇报,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我心情愉快地去见乡长。乡长的微笑意味深长。我拿出铜拴写给我的保证书。乡长说,不看了,你留着吧。不过,你要给乡里写个保证。我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了保证,大意是我负责全权处理张银拴问题,保证他今后不给乡里找后账,如果找后账,本人甘愿接受组织处理。多长收起我的保证。我随手打下一张一万五千元的收条。乡长签下“准付”两字。他略微歪着脑袋说,顶一个正式乡干部十几年的工资了。
我后来才知道,听了我的汇报,书记非常重视。等县里的会议一结束,他顾不上回家,匆匆赶回了乡里。他跟乡长和张副书记沟通后,连夜召开了党政联席会,很快形成一致意见。他说正逢计划生育再掀高潮的特殊时期,他们真要抬棺上访,堵了乡政府、县政府大门,影响就大了。全县二十个乡镇,县四套班子,特别是县委领导会怎么看?他们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我们乡里出了大事,我们控制不了局势。这个印象一旦形成,将会影响县委对干部的使用。那样的话,大家多年的辛勤付出就白费了,就可能在政治上吃大亏。如果我们推卸不管,可能省下几个钱(很难说),但最终得不偿失。所以,应该主动介入,促使尽快解决。我们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虽说一两万块钱不是小数,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征收超生子女费时,适当提高一下比例就行了……又不是从自家拿钱,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乡财政所账上没有钱。书记让财政所长跟我一块去找制瓶厂厂长,让他提前预付了下年度的承包费。
我拿了钱回到村里。支书赶了过来。铜拴兄弟们搀着他们的老娘过来了。我说为了你们家的事,我给乡里立了状子,现在跟你们绑到一起了。你们已经答应了,以后绝不能反悔。我把丑话撂到前面,谁要是反悔了,先得经过我这一关,到时不要怪我六亲不认。他们没想到能得着这么大一笔钱,已是千恩万谢,立誓赌咒永不反悔。
铜拴拿到钱,打了一个收条,商量以老娘的名义存进信用站。临出门时,我对铜拴说,知足吧,确实不少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到时候再找个女人都花不完,还有长头呢!
他们被我这句话逗笑了。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今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在市里修车,碰上从此路过的老乡长。我们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乡长调离后,又走了两个乡镇,现在县直部门担任领导。这期间,支书退位我接班。十年后,我也退了下来。我跟乡长蹲在路边树阴下。对面四台重型机械正在作业。数尺高的瓦砾上,一派乌烟瘴气。
我们聊着,说到了张铜拴。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他告状了。乡长说没有,当时处理得挺好,说过永不反悔的。我心里平静下来。乡长问张铜拴后来怎样了。我说第二年又成了家,生了个闺女,已经十七八岁了。乡长说过得太快了,他老婆掉进茅坑这么多年,快要沤成灰了。乡长的话让我困惑,谁掉进茅坑了?乡长说张铜拴老婆嘛。我说他老婆不是掉进茅坑死的,是病死的。乡长露出不解的神色。她掉进茅坑可是你亲口对我们说的。你说一个过路的女人进去解手看见了她,好多人用粪钩、粪叉什么的把她捞上来,怎么又成了病死的?一句她本来就是病死的没有出口,我忽然想起什么,意识到刚才说漏嘴了,赶忙附和了一句,噢,对对对,是掉进茅坑淹死的,快二十年了,一时想不起来了。乡长奇怪地看着我。那些往事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我掂量着,事过境迁,要不要说出实情呢。
铜拴老婆确实不是掉进茅坑淹死的,而是死在了一家县医院里。这些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诚实的铜拴变得不诚实了,他和他的家人说了谎,一同隐瞒了女人死亡的真相。除此之外,一切倒是事实。做结扎后,她的精神不正常是事实,铜拴送她到乡下的精神病院治疗是事实,她从精神病院走失也是事实。她从精神病院出走后,医院没有及时通知她的家人,而是派人悄悄外出寻找。他们找了几天几夜都没有结果,后来,终于在另一座县城发现了她。因为饥渴,她已经严重脱水,昏倒在了路旁。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她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抢救。她在那里躺了两天,最终还是死了。非常凑巧的是,此时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个疯女人掉进路边公厕死掉了。铜拴家人合计,想要得到乡里的赔偿,就得排除不利因素,让她的死跟结扎发生联系,死在医院病床上,显然不如死在厕所更能引起关注。于是,他们瞒着支书,瞒着我,把那个疯女人死亡的事件嫁接了过来。
没有必要为他再隐瞒了。
乡长听完会心地一笑。
我也笑了,却难掩尴尬。
乡长说,其实后来我们也听到一些议论,跟你讲的大同小异。我们没做深究。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处理还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毕竟一个生命没有了,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撇不清的关系,毕竟铜拴是我们的乡民,我们没有亏待他。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掩盖了事实,错不在你,当时情有可原,现在更能让人理解。如果那件事儿发生在今天,恐怕不是一万两万的问题,没有十万二十万,不可能了结。我们应该承认书记料事长远,他拍板拍对了。不果断不行。随着死者下葬,一切风平浪静。我们成功应对了一起突发事件。我记得书记说过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
我问乡长是怎样的一句话。
乡长说,舍得花钱买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