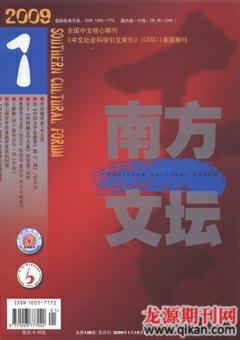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
2009-03-04孟繁华
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写作就死亡的时代。于是文学生产在当下的“繁荣”是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较的。在这种文学之外的竞争中,像吴玄这样能够持久坚持耐心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他的作品并不多,至今也只有十几个中篇一部长篇。因此他不是一个风情万种与时俱进的作家,而是一个厌倦言辞热爱修辞的作家。今天对这样一个作家来说不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时代。他们不仅要面对大众文学的激烈竞争,同时要与他们的前辈“战斗”。因此,他们的焦虑不仅来自当下的接受环境,同时还有大师经典的“影响”。但作为“异数”的吴玄似乎淡然处之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对现实生活和心理经验的感受,直至写出长篇小说《陌生人》。
当然,吴玄的创作还是经历了一个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生存到存在的变化,是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的变化。他初期的小说《西地》、《发廊》等,还是着眼于外部世界的表达,用现在已经形成潮流的文学现象来说就是“底层写作”。比如“西地”,这是吴玄几篇小说的地名。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来自本土的虚构之乡。吴玄似乎要接续回答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提出的乡村中国的问题,但吴玄面对的问题是他的前辈不曾遭遇的。前辈作家表达的是自己进入以都市为表征的“现代”后,发现了自己是城市的“他者”,他们遭遇了在乡村不曾遭遇的问题,于是便苦闷彷徨迷惘感伤,将只可想象不再经验的乡村神话或圣化,或将农民“民粹主义”化。这就是肇始于“左翼文学”,在延安光大的中国主流文学。但吴玄要处理的是乡村中国遭遇了“现代”之后,原乡农民的生存和精神状态。《西地》是一部中篇小说,叙事人“呆瓜”在这里似乎只是一个“他者”,他只是间或地进入故事。但“呆瓜”的成长历程却无意间成了西地事变的见证者:西地本来没有故事,它千百年来就像停滞的钟表一样,物理时间的变化在西地没有得到任何反映。西地的变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家庭的变故得到表达的。当“呆瓜”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一纸信函召回了远在城里的他,原因是他的父亲要离婚。“呆瓜”的还乡并不能改变父亲离婚的决心。如果按照通俗小说的方法解读,《西地》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吴玄要表达的并不止是父亲的风流史,他要揭示的是父亲的欲望与“现代”的关系。父亲本来就风流,西地的风俗历来如此,风流的不止父亲一个。但父亲的离婚以及他的变本加厉,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他偷卖了家里被命名为“老虎”的那头牛,换回了一只标志现代生活或文明的手表,于是他在西地女性那里便身价百倍,女性艳羡也招致了男人的嫉妒或怨恨。但父亲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他在外面做生意带回来的李小芳是个比“呆瓜”还小几岁的女人。父亲见了世面,和“现代”生活有了接触之后,他才会把一个具有现代生活符码意义的女人带回到西地。这个女人事实上和父亲相好过的女教师林红具有对象的相似性。林红是个知青,是城里来的女人,父亲喜欢她,她的到来使父亲“比先前恋家了许多”,虽然林红和父亲只开花未结果。但林红和李小芳这两件风流韵事,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父亲对“现代”的深刻向往,“现代”和欲望的关系,在父亲这里是通过两个女性具体表达的。
林红因为怀孕离开了父亲,李小芳因为父亲丧失了性功能离开了父亲,父亲对现代的欲望化理解,或现代欲望对父亲的深刻诱惑,最终使父亲仍然与现代无缘而死在欲望无边的渴求中。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在《发廊》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演。故事仍然与“西地”有关。妹妹方圆从西地出发,到了哥哥生活的城市开发廊。“发廊”这个词在今天是个非常暧昧的场景,它不仅是个美容理发的场所,同时它和色情总有秘而不宣的关系。妹妹和妹夫一起开发廊用诚实劳动谋生本无可非议,但故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先是妹夫聚赌输了本钱,然后又被人打成高位截瘫;接着妹妹在一个温情的夜晚不经意地当了妓女,妹夫不能容忍妻子做妓女,轮椅推到大街上辱骂妻子时被卡车撞死。这些日常生活事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是西地的后代们对无可把握的生活变动的态度。发廊因为可以赚钱,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开发廊,当做了妓女可以更快地赚钱的时候,方圆居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好。贫困已经不止是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它也成了一种生存哲学。妹夫李培林死了之后,方圆曾回过西地,但西地这个贫困的所在已经不能再让方圆热爱,她还是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方圆对“现代”的向往与《西地》中的父亲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是两代人,但现代欲望的引诱都使他们难以拒绝,时间在西地是停滞的。因此“现代生活”给西地带来的并不是福音,乡村有机会看到了“现代”的景观并部分地经验了“现代”的生活,但乡村原有的秩序、道德伦理、乡风乡俗彻底改变甚至崩溃了。
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描摹,是吴玄看到了“现代”的两面性,他的批判意图非常清楚。但是,文学诚如勃兰兑斯所说,“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因此说到底,文学毕竟还是处理精神和心灵事务的领域。表达社会历史变迁以及因此带来的震撼、惊恐或不适,心理经验应该是最真实和难以超越的。事实上,吴玄很快从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审察,从对外部的经验转向了内心的感受。这个转变大概从《谁的身体》开始。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不知身在何处的诘问。网虫“过客”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傅生,成功地实施了一次“网恋”行动,同时也成功地在现实中对一个女性诉诸了性行为。但当网上那个称为“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要从网上下来乘飞机见“过客”时,“过客”的朋友“一指”接替了“过客”的命名——“一指”就成了“过客”,然后“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就成了刚被命名的“过客”(其实是“一指”)的情人。这时,“过客”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虽然和李小妮发生过一次性关系,他们的分手没有给“过客”任何打击,但当“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真的来到身边之后,接触“鱼”的身体的不是“过客”却是“一指”,但“鱼”坚信那就是“过客”。两个“过客”同“鱼”的关系就是在命名中实现并倒错了。于是,接触“鱼”的身体是谁的身体就构成了问题。当“过客”试图重新在生活中找回“过客”的身份时,他永远失去了可能,这时的“过客”因对象的差错不再是“过客”而只是一个“嫖客”了。这个困惑不仅是当事人“过客”、“鱼”和“一指”的,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电子幻觉就这样把符号、身份和命名带到了日常生活,电子幻觉的世界就是符号帝国,真实的人反而不重要了,科技霸权就是这样改变了人性和人的社会属性。
《虚构的时代》可以看作是《谁的身体》的另外一种叙述:网虫章豪在网上是“失恋的柏拉图”,在网上他遇到的女性叫“冬天里最冷的雪”,他们兴致盎然地用网络语言在交流而对现实的男女之事失去了兴趣。当妻子需要温存的时候,章豪居然发现找不到身体的感觉了,而对一个符号式的人物“雪”产生了极大的情感甚至是身体需要。但他们真的见面之后,反而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必须生活在网上,生活在虚构和想象中。这个故事的有趣还与另一个人物“诺言”相关。诺言是章豪的老婆,但在《虚构的时代》老婆与网上情人比较起来是非常边缘的,诺言几乎采取了一切手段试图将章豪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她好言相劝、带他到迪厅跳舞,但一切都不能改变章豪对新生活——网上生活的盎然兴趣,迫不得已诺言最后只能对电脑诉诸暴力,她销毁了电脑才结束了过去的时代。
从《谁的身体》和《虚构的时代》起,吴玄开始转向了与内心世界相关的文学叙述。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吴玄所要表达的东西在思想上还是朦胧的,他只是隐约找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能够表达心理经验的文学入口。吴玄写得很慢,我想他可能是在等待那个朦胧的东西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我们读到了《同居》。这部小说最初被命名为《新同居时代》。这部中篇小说对吴玄说来重要无比,他开始真正地找到了“无聊时代”的感觉,何开来由此诞生。何开来这种人物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德国的“烦恼者”维特,法国的“局外人”阿尔道夫,默尔索、“世纪儿”沃达夫,英国的“漂泊者”哈洛尔德、“孤傲的反叛者”康拉德、曼弗雷德,俄国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床上的废物”奥勃洛摩夫,日本的“逃遁者”内海文三,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霍尔顿及其他“落难英雄”等,他们都在何开来的家族谱系中。因此,“多余人”或“零余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潮流过去之后,“多余人”的形象也没了踪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吴玄逆潮流而动,写出了何开来?
吴玄对何开来的家族谱系非常熟悉,因此,塑造何开来就是一个知难而上正面强攻的写作。哈罗德·布鲁姆早就讨论过“影响的焦虑”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和经典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熟悉的、在脑子里早就有的东西”,这种影响构成了巨大的约束和内心焦虑。能否摆脱前辈大师的“影响”并创造出新的经典,对作家来说是真正的挑战。但同时布鲁姆也指出,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没有一种令人烦恼的学习传统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的诞生。因此,“影响的焦虑”说到底还是一个传统与创造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继承与创造的问题。也许正是这个“陈词滥调”有力地区别了当下诸种时髦的理论批评。比如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这些新的批评理论被布鲁姆统称为“憎恨学派”。因为这些愤世嫉俗的批评话语就是要颠覆包括文学作品与批评在内的所有经典。吴玄对这些问题很清楚,但他一直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他说:“我写的这个陌生人——何开来,可能很容易让人想起俄国的多余人和加缪的局外人。是的,是有点象,但陌生人并不就是多余人,也不是局外人。多余人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物,是社会人物,多余人面对的是社会,他们和社会是一种对峙的关系,多余人是有理想的,内心是愤怒的;局外人是20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是哲学人物,局外人面对的是世界,而世界是荒谬的,局外人是绝望的,内心是冷漠的;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对陌生人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还有自我,甚至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见《陌生人·自序》,重庆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何开来和我们见到的其他文学人物都不同,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物对生活充满了盎然兴趣,对滚滚红尘心想往之义无返顾。无边的欲望是他们面对生活最大的原动力。但何开来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兴趣,生活仿佛与他无关,他不是生活的参与者,甚至连旁观者都不是。
吴玄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所理解的文学,大体上就是两种,—种是没吃饱的文学,还有一种就是吃饱了撑的的文学。没吃饱的文学,就是关于胃的文学,关于生存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吃饱了撑的的文学,自然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了。这儿,我们只谈后现代好吧,我以为,无聊就是存在的基本困境,就是后现代的关健词。我所说的无聊,是指零意义的生活状态,不是日常用语里的那种无聊。现在,我或者说我们,就是吃饱了撑的活在无聊的状态里面,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更愿意活在有意义的状态里面。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意义已经统统被解构了,我们除了面对无聊,还有什么呢?”(1)因此《同居》里的何开来既不是早期现代派文学里的“愤青”,也不是网络文化中欲望无边的男主角。这个令人异想天开的小说里,进进出出的却是一个无可无不可、周身弥漫的是没有形状的何开来。“同居”首先面对的就是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人紧张、不安也躁动的事物。但在何开来那里,一切都平静如水处乱不惊。何开来并不是专事猎艳的情场老手,重要的是他对性的一种态度;当一个正常的男性对性事都失去兴趣之后,他还会对什么感兴趣呢?于是,他不再坚持任何个人意志或意见,柳岸说要他在房间铺地毯,他就去买地毯,柳岸说他请吃饭需要理由,他就说那就你请。但他不能忍受的是虚伪或虚荣,因此,他宁愿去找一个真实的小姐也不愿意找一个冒牌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作为“陌生人”的何开来的原则是不能换取的,这就是何开来的内部生活。
长篇小说《陌生人》可以看作是《同居》的续篇,也可以看作是吴玄个人的精神自传,作为作家的吴玄有表达心理经验的特权。《陌生人》是何开来对信仰、意义、价值等“祛魅”之后的空中漂浮物,他不是入世而不得的落拓,不是因功名利禄失意的委顿,他是一个主动推卸任何社会角色的精神浪人。一个人连自我都陌生化了,还能够同什么建立起联系呢。社会价值观念是一个教化过程,也是一种认同关系,只有进入到这个文化同一性中,认同社会的意识形态,人才可以进入社会,才能够获得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何开来放弃了这个“通行证”,首先是他不能认同流行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更具有“新精神贵族”式的小说。吴玄是将一种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受和玄思幻化成了小说,是用小说的方式在回答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语言建构的乌托邦,一朵匿名开放在时代精神世界的“恶之花”。在这一点上,吴玄以“片面的深刻”洞穿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有思考的能力的人,都不会怀疑自己与何开来精神状态的相似性,那里的生活图象我们不仅熟悉而且多有亲历。因此,何开来表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症。如果从审美的意义上打量《陌生人》,它犹如风中残荷,带给我们的是颓唐之美,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苍茫、无奈和怅然的无尽诗意。因此,因为有了《陌生人》,使吴玄既站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最前沿,同时使他有可能也站在了文学的最深处。我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读到的最具震撼力的小说。
请允许我借用一个比喻:2008年在宣布钱永健获诺贝尔化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贡纳尔·冯·海涅手持一支试管,内装用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改造过的大肠杆菌。用紫外线照射后,试管发出绿色荧光。冯·海涅说,这种级别的发现“能让科学家的心跳比平时快上三倍”。我要说的是,读了吴玄的《陌生人》,我们的心脏可以比平时快上两倍。■
2008年10月10日于沈阳师大
【注释】
(1)http:∥www.novelking.com.cn/modules/article/txtarticle.php?id=13757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