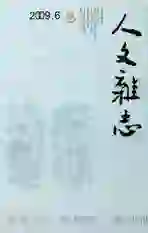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
2009-01-18张分田
内容提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而一些现代学者却力图借助一种牵强的解读方式予以回护。然而,《论语》词义研究不支持孔子没有愚民思想说,思想体系分析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说,儒家文献不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政治过程分析有利于采用传统句读的一方。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端正学风,改进方法,深化认识。而尊重历史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关键词 孔子 儒家 愚民 理想政治模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K203;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131-07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有一种现象司空见惯:有关某种思想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的笔墨官司大多围绕有限的史料展开,往往在同一条史料上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见。中国字的多义性,古今词义、语法与语境的差异,古代文献原本不使用标点等固然是引起争议的缘由,而背后往往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端正学风,改进方法,深化认识。
一、从“民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之争谈起
《论语•泰伯》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孔子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的译注是:“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①这种句读方式获得古今学者的普遍认同。许多现代学者据此判定:孔子将民众置于被统治、被支使的地位,他属于典型的愚民论者。
发明另一种句读方式的是康有为。他认为,古人对这句话的标点断错了,应当在两个“使”字后面各加一个逗号。在他看来,“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②康有为力图以这种方式排除孔学有愚民之术的嫌疑。
康有为的做法颇受一些现代尊孔者的青睐。在《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中有一段类似的说法:“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桀不谓其民必乱,而民有为乱矣。”③一些学者也沿袭康有为的方式,将其句读为“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依据这两条重新句读的材料力辩孔子没有愚民思想。
采用康有为句读方式的学者都将这句话做了正面的解读。例如,南怀瑾的解读是:“民可使,由之”,即人民懂得如何选举,就给予他们自由;“不可使,知之”,即不能达到这种水平,就先教育他们,使之懂得这个道理。④吴丕的解读是:在人民听从统治者的使唤时,只要加以引导就行了;不听从使唤就要对人民进行教育。⑤这些学者普遍强调主张“仁政”、“民本”的先秦大儒不可能有愚民思想。例如,张刚认为,愚民之说不符合孔子的“人本”思想,因而这句话应译为“如果民众得到很好的管理,就继续使用此种方法;得不到有效管理,作为统治者继续仔细地考察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注:张刚:《是“愚民”还是“民本”》,《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第115—117页。)商国君认为,杨伯峻的解读“显然违背了孔子的一贯主张”。这句话应当译为:“当民众懂得如何去做,并有能力去做时,就应该让他们去做;当民众不知道如何去做及没有能力去做时,就要采取适当措施并教诲他们如何去做。”(注:商国君:《先秦儒家仁学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有的学者赞成商国君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孔子的仁的学说,也与孔子的教育观相吻合,是孔子仁政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注:王保国:《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治思想视野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8BZS003)阶段性成果。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
② 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4页。
③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④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
⑤ 吴丕:《再论儒家“使民”思想》,《光明日报》,2000年6月13日。
康有为的句读方式显然有回护之嫌,具体说法则因人而异。近日读报又见到一种正面效应更明显的解读:“老百姓优秀的,让他去搞管理去做官;不行的,让他去努力学习。”在作者看来,“这样就和孔孟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宗旨一样了。”而原先的翻译和理解“与孔孟之道‘有教无类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注:袁小虎:《一直被误解的四句名言》,《天津老年时报》,2009年8月19日。)
杨伯峻的句读方式沿袭历来的一贯做法,因而在古今学者中通行,包括尊崇孔子的古代大儒。康有为发明的句读方式则博得一些现代学者的认同。实际上,古代学者并没有介入这类争论。句读之争的双方都是现代人,他们对同一句话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大多数学者视之为孔子愚民思想的明证,而一些回护孔子的学者则调动训诂学的资源,千方百计地证明另一种句读方式的可行性,以证明孔子压根就没有这类思想。于是两军对垒,相持不下。究其本源,这与其说是训诂译注之争,不如说是属性判断之争。因此,句读之争原本发端于现代批孔者与现代尊孔者之争。
在现有条件下,仅仅争论句读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它只能永远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步。原因很简单:即使在语法上足以证明“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具有可行性,也无法否定“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的可行性。因此,必须另辟蹊径。
二、《论语》词义研究不支持孔子没有愚民思想说
训诂之争大多可以通过与训诂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破解。依据许多文字词义学和文献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否定孔子没有愚民思想的说法。
宋永培的《〈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一书专门以“先秦文献词义”为研究对象。作者指出:“五经”及诸子经籍较为系统地保存了中国早期语言词义蕴含的形象特征及其凝聚的核心义,而孔子整理典籍体系为大规模解释古代词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系统考察《论语》的“民”、“人”之别,逐一分析各种用例,其基本结论是:“民”、“人”之别集中于“下”、“上”的不同。在《论语》中,单音词“民”出现47次。在同一语句或同一段话中,“民”往往与“君”、“君子”、“上”等表述在位者的词相对照。有的省略“君”而以“使民”、“教民”、“临民”、“莅民”、“务民”、“济众”表述君民关系。“人”出现134次,除了1次指义不明外,其余用于指称在位的仁人、贤人;不在位的仁人、贤人;善士、人才;君王、诸侯、卿大夫;人的泛指。由此可见,“民”的词义特点是“下”,而“人”包含着“上”的词义特点。“民”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道德知识处于下等。例如,《季氏》有“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雍也》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上述分析有可靠的文献依据,很有说服力。客观地说,这样的词义差别并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早已通行的。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孔子只是在遣词用字上更严谨,更考究而已。
关于“民”的本义及核心词义,学界多有争论。这一争论背后也往往隐含着与儒学属性之争相关的主观因素。一些学者为了提升儒家重民思想的正面价值,援引先秦文献中“民”字泛指人类、人群和指称君主、贵族的用例,力辩这是个褒义词。这种观点显然是靠不住的。在阅读古代文献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悟到:如果从政治文化符号的视角综合考察民字的形象词义、读音词义、描述词义、指称词义、评价词义和引申词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字有与生俱来的贬义,其核心词义是派生者、从属者、卑贱者、愚昧者、无德者。在数千年的词义变迁中,在中国古代主流政治文化中,民字的核心词义始终保持稳定。其中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最为典型。因此,在解读儒家经典及各种重要的古代文献时,特别是在解读“民为本”、“民为重”、“民为贵”之类的话语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很容易导致误读。(注:具体理据参见张分田:《政治文化符号视角的“民”字核心词义解读》,《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
《论语》以地位低下、心智愚昧、道德瑕疵为“民”的核心词义和常用词义。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对“民”有清晰的定位。在他的心目中,在下之“民”通常是有道德瑕疵的一群。在先秦诸子中,儒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不仅讲究尊卑、贵贱、君臣等社会政治地位的上下之别,而且强调上下之别与人性、智慧、道德之别的密些关联。在“君子”与“小人”从政治等级范畴向道德价值范畴转化的过程中,《论语》等儒家文献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与孔子思想的特质和取向有直接关系。
由于孔子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思路从整体规模上系统地、深刻地影响、制约后世汉语词义的发展。在经典文献及其注疏中,凡人与民对称时,二者往往有地位或道德的上下之别。例如,《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毛亨传:“宜安民,宜官人也。”朱熹注:“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这与《论语》的用法是一脉相通的。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儒家经典注疏和《说文解字》等“小学”著作,就不难发现大力鼓吹民本思想的历代儒家传人常常把民说成无知无德、追逐利益、亟需教化的一群,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民”的词义中原本就有这类义项。“庶民愚昧”是儒家对民众群体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显然是祖述孔子的产物。
三、思想体系分析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说
康有为发明了一种最费解的句读与解读。他清楚地知晓“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仅是一己之见,只能从其他角度为自己寻求理据。于是他采用了一种典型的“儒术”,即先假定孔子“不可能”有某种思想,然后在标点符号上做文章,设法让这句话摆脱负面解读。
显而易见,凡是采用“不可,使知之”句读方式的都预先有一个设定,康有为预设孔学并无愚民之术,南怀瑾预设孔子主张民主选举,更多的学者则预定“仁政”、“民本”、“人本”不应有愚民思想,有的还将孔子的教育命题作为宗旨性预设。
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容许主观预设。研究者通常都事先获得一定的知识、经验、方法和尺度,因而在面对一个课题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形成主观预设。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做到毫无预设。因此,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预设,甚至也不在于预设是否恰当,而在于是让预设服从研究结论,还是让研究结论服从预设。
孔学的宗旨究竟是什么?这原本就是很容易导致见仁见智的话题。以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仁”为例,在《论语》的记载中,倡导以礼治国的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内涵确定的“仁”的定义,而是讲了很多以礼界定仁、以仁论说礼的名言,诸如《颜渊》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于是礼与仁何为孔学宗旨便成了千古之争。孟子张扬“仁”,荀子发挥“礼”,于是儒家内部历来有重仁、重礼的学理之争。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看,汉初学者将尤为讲究“君臣父子之礼”作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显著特征,没有提到“仁”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强调“仁义”这个尺度。随着《孟子》提升到经典的地位,仁的理论地位也显著提升。但是,如果仔细梳理一下《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等朱熹的著述,就不难发现:这位博大精深的理学大师并没有简单地判定礼与仁何为至高无上的范畴,甚至可以说两者是相互定义、同体异名的范畴。现代学者深受“专制与民主”预设影响,于是相关争论由学理之争转化成属性之争。一般说来,极端尊孔者一味强调“仁学”中心说,极端批孔者一味强调“礼教”中心说。大多数学者则在全面考察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认同“礼仁”中心说。
《论语》的篇幅不大,却多有经典性名言供人赏析、援引。因此,判定孔学究竟以何为宗旨,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由此可见,各取所需的“宗旨”说不足以为句读之争及相应的解读提供毋庸置疑的理据。因此,更合理的方法是全面考察思想体系,深入剖析思维逻辑。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做过扎实的工作。由此而形成的学术成果显然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的观点。
从《论语》的记述看,孔子以性近习远、上智下愚,论说人类本性;以王权至上、独掌大政,论说权力主体;以天子专权、庶民不议,论说天下有道;以上贵下贱、不得僭越,论说等级差别;以上行下效、风行草偃,论说道德教化;以见利忘义、小人难养,论说世风民情。他还多有轻视民众的言论。在孔子看来,就天赋而言,人类中的一些人天生就是“不移”的“下愚”;就后天而言,人类中的许多人由于习染的缘故沦为“喻于利”的“小人”;就政体而言,人类必须实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而“庶人不议”(注:《论语•季氏》。)是最理想的政治状况;就道德而言,普通民众往往欲壑难填,见利忘义,很难与之相处;就治道而言,由道德完善者教化道德缺失者是当务之急;就教化而言,治者如风,被治者如草,风行而草偃。依据这类说法,很容易推导出这样的思路:由“天子”治理“庶民”,由“上智”管理“下愚”,由“君子”教化“小人”。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施政模式是圣者为君,贤者主政,为政以德,教化民众。这种思路的逻辑前提是:广大民众有智能、识见、道德、品行等方面的缺陷。
实际上,那些依据孔子教育思想“宗旨”而反对传统句读方式的学者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在教育宗旨之上还有更具根本性的“政治纲领”。标示本质的“纲领”才是全面理解整个思想体系和各种“宗旨”的关键之所在。就思想的主旨、主体而言,孔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就连教育也属于“为政”的范畴,而治国纲领是“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在特定的政治纲领制导下,任何具体的“宗旨”都会被注入特定的政治内涵。
就本质而言,“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属于同义命题,其内涵具有一致性;就理论功能而言,二者可以看成一对命题组合。前者侧重国家体制的法则,强调维护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后者侧重政治操作的艺术,强调实施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这种治国纲领的思维逻辑是:民众不仅政治等级低下,而且道德水平低下,有必要通过实行一系列德政,构建理想的政治秩序,使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注:《论语•为政》。)显而易见,政治等级的上下之别旨在界定统治关系、主从关系,确认支使者与被支使者;道德水平的上下之别则旨在确认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并为这种统治关系、主从关系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主要理据。如果不对民众的整体素质做出贬义性的价值判断,孔子的政治纲领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因此,“民众愚昧”是孔学不可或缺的公理性预设。如果剔除了这个预设,孔子的政治学说及相关的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就会被釜底抽薪,甚至导致其整个学说体系无所凭依。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现代新儒家是从“孔子民主”的主观预设出发,来解读其思想体系的。这种预设与事实完全相悖。其实只要列举《尧曰》的君之位为“天禄”说,以及《孟子》和《礼记》记载的孔子的“民无二王”或“土无二王”说,便足以断定赞赏西周政治体制的孔子是天赋君权和天子集权论者。主张严格区分君臣上下之别的孔子不可能构思实行民主选举的政体。这里再举一例,即“庶人不议”说。据《季氏》记载,孔子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等列为“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条涉及政治制度中的权力主体和政治过程中的决策控制权。孔子显然主张将决策权托付给无需民选的天子,因而无法归入民主范畴。所谓“庶人不议”,即“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注: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这就是说,理想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天子在上,大权在握,决策英明,臣属从命,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以致普通民众无可非议。这种政治过程设计,显然符合“民可使由之”的说法,而无法支持南怀瑾的“民主选举”解读。
上述事实表明,即使仅凭《论语》来研究孔子思想,也可以断言: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含有愚民思想。句读为“不可使,知之”的各种解读难免牵强。
四、儒家文献不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
事实依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思想史研究既要擅长概念分析,又要重视历史解释,而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事实依据的缺失和错误。事实的错误最具有颠覆性,它会使貌似精彩的分析变得一钱不值。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决定考察一下历史事实,更为支持哪一种观点。检索历代名家的《论语》注疏之后,得出的基本印象是:在中国古代,不仅没有人使用康有为的句读方式,而且人们大多从民众愚昧的角度来解读这段话。换句话说,只属于某些现代学者的“不可使,知之”句读方式无法在古代的《论语》注疏中找到支撑点。
古代注疏者普遍认为,民众的认识能力低下。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不可以、不可能、不应当使民众知之。具体说法很多,或百姓不能知,或百姓鲜能知之,或百姓日用而不知,或君无为而民不知,或不可使之知,或不必强使之知,或不必使之知所以然,或民众无权知之,或百姓知之反而生迷惑乃至起机心等。一批著名思想家均持此类说法。例如,东汉的郑玄认为,“民,冥也。其人见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注:郑玄:《论语郑氏注》卷四《泰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三国的何晏认为,“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南朝的皇侃认为,天道玄远,百姓“虽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注:何晏集解、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四《泰伯》。)宋朝的邢昺认为,“圣人之道深远……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注:《论语注疏》卷八《泰伯》邢昺疏。)程颐认为,“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与知也,不能使知之尔。”(注: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二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朱熹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⑨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卷四《泰伯第八》。)陆九渊认为,“非圣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义则彼民之愚,盖有所不能知也。”
(注:陆九渊:《陆九渊集》外二九《使民宜之》。)张栻认为,“此言圣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注:张┠臼姜:《癸巳论语解》卷四《泰伯》。)上述注疏无一例外地属于“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许多儒者的确反对从权术的角度解读孔子的思想,而他们对民智的估价并不高。显而易见,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孔子之语的理解更接近以杨伯峻为代表的解读方式。这种现象是无法用孔子的真经被歪嘴和尚们念错而简单地加以了断的。
在理论上,许多儒家传人不赞成使用愚民之术。例如,程颐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注: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二五《伊川先生语十一》。)但是,他又认为,“圣人设敎,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⑨在宋元明清,程颐的这个思路具有广泛的影响。从字面上看,程颐并不主张玩弄“朝四暮三”之类的愚民之术,却认定民智低下,必须由“圣人设教”,而民众“由之”。这个思路为论说一种圣贤主义政治模式及其治民方略提供了依据。
在儒家文献中,有关涉及愚民的思想材料不胜枚举。历代名儒大多从“民者,冥也”的角度论说民本思想和治民方略。孔子及其后学的政治思想以注重教化为特色。《尚书》及其注疏的“天作君师”说、《左传•襄公十四年》及其注疏的“勿使失性”说、荀子的“化性起伪”说、董仲舒的“天立王以成民性”说、宋明理学的君师教民复性说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思路。儒家有关教化的各种理论的基本前提和主要思路是:世风浇漓,民智低下,小人好利,芸芸众生不能自成其性,他们需要圣贤的教导与矫正。在民众无法体察大道的情形下,只要使他们顺从圣人王者立下的规矩就可以了。就实质而言,这是典型的愚民思想。
儒家常常以“王道”自诩而抨击其他学派为“霸道”。与公然鼓吹权术的道家、法家相比较,儒家具有排斥权术的倾向。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但是,如果据此断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没有权术的存身之所,就大错特错了。许多儒家重要文献显然包含权术思想。《周易》是中国古代权术思想的渊薮之一。《易传》的一些内容很可能源自孔子。其中《周易•观卦•彖辞》有“圣人以神道设敎,而天下服矣”,即主张治者有意抬出一些神明,令无知愚昧的民众因畏惧神的责罚,而老老实实做人,恪守道德纲常,服从国家法律。这个思路体现了儒家的教化型愚民思想的特色。在《周易》注疏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注:《周易正义•革卦》王弼注、孔颖达疏。《温公易说》等一批注释《周易》的著作有类似的说法。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民难与虑始”的说法很常见。)这种思想的基本导向是:民众没有能力做出或理解正确的政治判断,只能让他们遵循治者的正确决策,并称颂这些决策带来的繁荣。在《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记载的据说是孔子的言论中,甚至有这样的比喻:国家犹如构件齐全的车乘,君主犹如手持鞭策的驭手,民众犹如驾车服御的马匹。在孔学传人中,阐释上述思想的现象并非罕见。这些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儒学基本取向的旁证。
一些学者断言倡导“仁政”、“民本”、“人本”就必然不主张愚民,这种说法颇有武断之嫌。一般说来,历代儒家都是倡导“仁政”、“民本”、“人本”的,而公开主张愚民或实际上主张愚民的大儒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倡导“仁政”、“民本”、“人本”的并非“必然”不主张愚民。既然“仁者必然不会愚民”的断语并不可靠,而“仁者往往主张愚民”的判断又得到儒家文献的支持,那么“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又丧失了一个重要理据。
五、政治过程分析有利于采用传统句读的一方
至迟到汉朝,孔子已经被统治者尊为圣人,孔学已经成为官学,《论语》已经列入经典。因此,孔子的话乃至一切被认为是孔子的思想也就成为朝堂议政的权威性依据。后人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从政治过程中的实际功能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愚民之术的经典依据。
在古代文献中,许多人援引孔子的说法论说民智低下与政令发布的关系。在朝堂议政和政论文章中,引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现象很多。在《后汉书》、《魏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等文献中多有这类记载。人们都是在不可、不必、不能、不应“使知之”的意义上理解孔子的思想,许多具体政见可以明确无误地判定为愚民之术。根本找不到可以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及其各种解读的例证。在朝堂议政和政论文章中,“民难与虑始”之类的说法就更为常见。“庶人不议”更是判定盛世的重要尺度。使用这类说法的人大多尊崇孔子,信奉儒学,主张民本。
如果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的话,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愚民”与“民本”相对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翻检了大批古代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凡是留下比较完整的政治论著的著名思想家,无论属于哪家哪派,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认定为民本论者。在任何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文献中都有重民、爱民、利民、使民、制民、愚民的提法和思路,都可以找到从争取民众、怀柔民众,到管制民众、愚弄民众等各种治民手段。思想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点有所不同,诸如儒家礼治仁政的“教民”色彩更浓厚,道家无为而治的“愚民”色彩更浓厚,法家刑名法制的“制民”色彩更浓厚。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旨在维护并完善君主制度的思想家都会将各种治民手段兼收并蓄。
不仅如此,“仁政”、“民本”等明明白白地写在历代官方学说的各种载体中。历代统治者,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也可以大体判定认同民本论。如果浏览一下记载历代朝堂议政和政府文告的文献,便可以知晓:自秦朝以来,历代朝廷都标榜“仁义”之政,而“爱民”、“富民”、“教民”、“利民”、“制民”、“愚民”政策原则及相关具体政策主要是在儒家经典指导下形成的。其中,在论证和制定相关的治民政策时,出自孔子之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具权威性。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愚民”与“民本”相对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些学者断言:孔子以仁政为最高理想,以惠民为基本宗旨,因而绝对不会提出愚民之策。这种评说方式显然有简单化之嫌。
六、尊重历史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在现代学界,有一类学术方法似乎越来越流行,其基本特征是:试图将孔子的形象修饰得完美高大,从而使之摆脱各种负面的价值判断。一些人甚至将孔子描绘成民主思想的原创者。于是有的人千方百计地要将原本容易句读、不太令人费解的孔子之语,弄成即使精通古汉语的人也觉得很别扭的样子。“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便是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例。更有甚者竟然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解读为:“唉,女子嫁给道德败坏的人,可就难以生活了。”难道语言文字水平极高的孔夫子,偏爱用这么费解的方式表达的思想吗?表达如此简单的思想,何须如此模棱,何必如此拗口?
具有这类旨趣的著作及其评介者还往往张扬一个宏大宗旨,即弘扬传统文化,“重新发现”孔学要义,使之“充满新意”,乃至“儒学现代化”。这就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摆在人们面前:怎样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如何恰当地弘扬传统文化?……
自冲破传统社会的躯壳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重建新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进行文化反思,认识文化缺陷,强化文化自觉,完成文化重构,实现文化复兴,这不仅是一个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要想解决这个课题需要全国人民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努力,长期探索。限于篇幅,这里仅表达一个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论点,即尊重历史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受西方现代学术的一些预设,特别是“民主与专制”预设影响,一些学者以为只有将孔子思想判定为“民主”、“民权”、“自由”、“平等”,才能提升孔子的地位,弘扬中国文化。这种思路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最低也要被批评为“好心办坏事”。
由于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很强的孔子谈论一些包含性别歧视、等级歧视的说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使在有民主之风的古希腊,维护父权、歧视妇女、丑化奴隶也是通行的社会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不难找到这一类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如果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没有这类思想,反倒相当怪异了。因此,依据现代价值观,实事求是地批评孔子或亚里士多德的这类观念并不会贬低他们的历史成就。如果将他们的相关说法统统解读成现代观念,反倒成了弄虚作假。
试想:孔子为人正直,恪守其道,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明确主张君位得自“天禄”,理应“土无二王”,严守“君臣之义”。可是一些现代“弘扬”者却偏要说他主张民主选举、人人平等,将许多现代观念强加在孔子身上。如果孔子在天有灵,肯定会责备这种做法曲解了儒家政论的纲领、灵魂、精髓,悖逆了圣道、王制、名教。至少也会道出像卡尔•马克思批评他的许多追随者一样的话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对孔子最大的尊重就是让孔子回归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而实实在在的孔子无愧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一场社会大变革露初端倪的春秋时代,面对权力结构的紊乱,孔子主张中央集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完全符合欧亚大陆帝国化的历史趋势。面对贵族权力世袭的旧制度,孔子主张选贤与能,“学而优则仕”,这完全符合政治制度创新的大方向。面对官学垄断的局面,孔子首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为那个时代培养了一批不可多的人才。面对传承历史文化的任务,孔子收集、整理、改编、阐释经典文献,形成一批流传千古的原典文本。面对文化创新的时代需求,孔子主张损益周礼,革新道德,大力张扬仁论,构思和谐的礼乐文化,以弥补传统礼论之不足。面对富国强兵的课题,孔子主张足食足兵,取信于民,为后来的变法运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孔子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人,堪称先秦诸子之首。孔子地位后来的提升,也与他的全面的历史贡献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的理性思考、文化创新和社会实践,当其他古代文明纷纷走向衰落的时候,华夏文明却因为缔造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而获得了强韧的生命力。我们只须对此做出客观、全面、准确、公正的评价,便足以表达对这位先贤崇高敬意。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为孔子涂抹现代的油彩,更无须将只有现代才有的思想附会到儒家经典上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