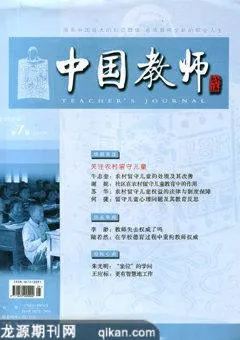汉字与古代田猎文化
2008-12-29王立军
中国教师 2008年7期
《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这是对远古时期先人生存环境的描述。当时,天下一片洪荒,野草丛生,乱木成林,鸟兽大量繁殖,对人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即使在中原地区,也都布满了鸟兽行走的印迹。这些印迹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正是根据这些印迹来判断鸟兽的类别,如果是凶猛的鸟兽,则提高警惕,或者隐藏躲避;如果是弱小的鸟兽,则设法捕获,用以充饥。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区分的事物越来越多,光靠鸟兽之迹已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人们在鸟兽之迹的启发下,发明了汉字。这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知道据此可以辨别不同的鸟兽,因而开始模仿鸟兽的足迹创造文字。可见,汉字从一产生起,就跟田猎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骨文有一个(biàn)字,后来演变为,正像一个野兽的脚印。这个字小篆字形作,楷书字形作“釆”。《说文》解释说:“釆,辨別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古人造字时,正是用鸟兽的足印来表示辨别之义的。后来,这个字分化成两个字,即“釆”和“番”,其中“釆”专表辨别义,“番”则专表兽足义。《说文》:“兽足谓之番,从釆,田像其掌。”“番”金文写作,其下部不是田地的“田”,而是像野兽圆圆的脚掌。由于“番”字和脚有关,后来便又加上了“足”字旁,作“蹯”。《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是一个无道之君,有一次他的厨师做饭时没有把“熊蹯”煮熟,晋灵公一生气就把他杀了。这里所说的“熊蹯”就是熊掌。其他一些从“釆”、从“番”的字,也往往有“仔细观察”、“分析”之类的意义,如“審”(“审”的繁体字)义为“仔细辨别”,“释”义为“分别物类”,“悉”义为“详尽明白”等,这些都可以看出“兽足”和“分别”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田猎在汉字构形中留下的痕迹。《周礼》中有所谓的“迹人”之职,其任务就是专门察看鸟兽的足迹,以判断它们的藏身之处。《左传•哀公十四年》:“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就是说,迹人来报告,在逢泽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只孤身的麋鹿。
田猎的“田”和田地的“田”本为一字,甲骨文像田地阡陌纵横的样子(见图1)。那么,为什么田猎和种田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前面说过,由于草木丛生给野兽提供了藏身之地,于是古人采用焚烧的方法,驱赶或者围捕野兽。野兽赶走了,野草也烧光了,留下来的空地正好可以开垦出来种植庄稼,这样,农田便出现了。
除了火猎之外,古人还使用弓箭、网、陷阱等多种狩猎方式。如 (罹难的“罹”)是用带有长柄的网把鸟罩住,(罗网的“罗”)是用张设的大网把大象围住,(陷阱的“陷”)是用挖好的陷阱把鹿困住,(表示野猪的“彘”)则是用箭将野猪拦腰射穿。这些生动形象的字形,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狩猎活动惊心动魄的场面。
狩猎的“狩”与野兽的“兽”本为一字,楷书繁体写作“獸”,甲骨文有等多种写法(见图2)。在这些不同字形中,右边表示动物形状的部分,无论繁简都是“犬”字,没有出现其他动物,说明在这个字形中“犬”不是被猎获的对象。因为如果“犬”是代表猎获对象的话,它就应该可以用其他动物来代替,很多汉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罗网的“罗”既可以写作(网住大象),又可以写作(网住鸟)、(网住鹿)、(网住老虎)、(网住兔子)、(网住野猪)等,最初造字时并无定形,在能够用网捕捉的动物中,选一个代表就行了。而甲骨文“狩”字中的“犬”,没有被别的动物替换的用例,说明“犬”在构成该字时,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说文》:“狩,犬田也。”所谓犬田,就是用犬去打猎。田猎的“猎”字从犬,很多可以充当猎物的动物也从“犬”,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开始使用犬进行捕猎了。犬的嗅觉灵敏,又通人性,可以帮助人们找到猎物的藏身地,因而成为古人打猎的好帮手。可见,甲骨文“狩”字中的“犬”,不仅不是捕猎的对象,反而是以捕猎者的身份出现的。
图2:甲骨文的“狩”字
除了“犬”字之外,甲骨文“狩”字的另一半作、,或作、、,对于这部分字形究竟代表什么,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一般认为,写作、的,后来演化为干戈的“干”字;写作、、的,后来演化为“單”(也就是后来的“彈”)字,其实它们最初都是一个字,像一种捕猎工具的样子。这种工具刚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树杈,可以用来捶打或戳刺野兽,后来逐渐在树杈的两个顶端,分别绑上圆形的石块,以增加打击的力量。这种捕猎工具,不仅可以在考古发现中找到证据,而且可以在现代民俗中得到证明。半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经过琢磨的圆形石块;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放映厅里,也艺术再现了石器时代北京人用树杈和石块捕猎的场景;甚至远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曾经使用过这样的工具;而更为鲜活的例子,就存在于云南纳西族不久前的田猎活动中。据瑞典人林西莉《汉字的故事》描述:纳西族人在半公尺长的绳子两头各栓一个石球,中间做一个绳扣,或者用绳头结一个把手,然后手执把手,让石头在空中旋转,待达到一定速度时,朝野兽的方向飞速抛出,击中猎物的身体或者缠绕猎物的腿脚。甲骨文中又可以增加一只手,作,正像手执长柄抛掷石块的形状,这更证明了这种田猎方式的推测并非臆想。只有树杈时作“干”,增加石块后作“單”,发明弹弓后作“彈”,用于打仗时作“戰”。这一系列汉字表明,古老的石块虽然在不断地演进,但其原始的踪迹则一直保留在汉字字形中。
随着田猎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进,古人捕获的猎物越来越多,在满足人们食用之外开始出现盈余。怎么安置剩余的猎物,成了当时人面临的新问题。人们逐渐摸索着对猎物进行圈养,甲骨文的“牢”字正描述了这一过程:圈的是牛,圈的是羊,圈的是马。这些动物不怎么凶猛,可以圈养起来,以备食物缺乏时食用。圈养动物的做法,也标志着古人由田猎时代过渡到畜牧时代,由居无定所转变为有了相对固定的家。“家”的构形是房子里面有一头猪,意味着饲养动物才是“家”的真正开始。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说:“中国初民时代的‘家’大概是上层住人,下层养猪。……现在云南乡间的房子还有残余这种样式的。”现代民俗学的考察证明,不只是在云南乡间,在其他不少地区,都可以看到“家”字所勾画的“人畜同舍”的情景,如傣族的竹楼、羌族的碉房、苗族的吊脚楼等。
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动物不仅可以养来吃,还可以通过驯化,使之成为劳作的工具。在古代汉语中,表示劳作的意义常用“为”字,甲骨文写作,像用手牵着大象的样子。那么,劳作和大象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我国远古时期中原地区气温较高,湿度很大,十分适合大象生存。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大象化石。直到商代的遗址中仍然可见大象的遗迹,而且在甲骨文中,还有关于商王田猎时“获象七”的明确记录,说明在那个时候,大象在中原地区依然常见。只是到了西周时期,由于气候及其他原因,大象才被迫南迁。据文献记载,古人很早就开始驯化大象。如《论衡•书虚》记载,传说“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这是用大象耕种的较早的记述。据罗振玉推测:“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后来,大象在中原地区逐渐为牛马所代替,但在南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用象的历史则一直沿用了很久。如《史记•大宛列传》把当时的滇越国称为“乘象国”,唐代的傣族用象耕作,元明清时期用象作战等,都是对甲骨文“为”字所表示的古老劳作方式的传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