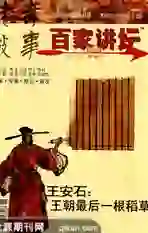江冲真的是“大奸”之人吗
2008-04-28李国权张家清
李国权 张家清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他是“大奸”之人。唯有康熙皇帝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整个事件中,他不仅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出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名齐,字次倩,赵国邯郸人,本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即中小商人阶层。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赵国敬肃王刘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汉书》记载,敬肃王彭祖是一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一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深怀疑忌,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大者死,小者刑”,弄得后来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们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八个字:先发制人,陷入于罪。每当中央派新的官吏到来,他都恭恭敬敬地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诱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了触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
这种豺狼式的凶狠与狐狸式的狡猾,使彭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一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做到“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春风得意,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一个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所以他时刻提防着别人告发自己的隐私。又由于关系密切,很多事情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太子丹怀疑的邪火就烧到了江充的身上。被太子丹的使吏追捕时,江充机警地变名潜逃,但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连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这样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江充逃入关中,诣阙状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但江充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仅见到了汉武帝,还告御状成功。其状子中所列太子丹的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并将他投入魏郡诏狱判了死刑。
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的罪行申辩,反诬江充乃“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并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想法,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然而,赵王彭祖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感动皇帝,武帝最后还是废掉了刘丹的太子资格,但免其一死。
江充最终斗垮了赵王父子,以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成为皇帝的近臣,很快又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中武帝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不只是江充魁梧的身材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令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他为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即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这一战略十分高明,比起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它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靠谄媚阿谀侥幸得势之辈。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最后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
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是因为江充的努力,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
在与贵戚的斗争中,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正是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江充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乃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
当时,景帝后宫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而获得宠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识短善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长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长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被拒绝的长公主恼羞成怒,把目光转向了王夫人的儿子,即后来的汉武帝。王夫人许婚之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因为馆陶长公主是汉武帝继承皇位的主要推动人,所以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甚至敢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力和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只有江充对此不屑一顾。
有一次,长公主的车骑在驰道上横冲直撞,碰巧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敢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长公主来说是大不敬的行为。馆陶长公主有恃无恐,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鞍具。
另一起事件是对戾太子的制裁。
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官,遇见戾太子家人乘车马行于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由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大为惶恐,派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以免被皇帝知道。但是,江充却并不理会,如实上奏。汉武帝对江充此举极赞赏,认为“人臣当如是矣”。
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巅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
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有充分的了解。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的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透了汉武帝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长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因容貌衰减,过分骄妒,更由于没有生下儿子,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被幽禁于长门宫中。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就曾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皇后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使人潸然泪下。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传统宗法关系的约束和昔日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长公主年老而内行不修,五十多岁了,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找了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做面首,声威已一落千丈。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但却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卫皇后虽然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但汉武帝“独悦子夫”。后来,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并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虽然卫后得宠,但一旦她色衰而爱弛,那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其一生,武帝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他对长生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愈加强烈。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用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接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时刻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因对权力的迷恋而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了所谓的父子之情。况且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拖延交班时间的诱惑和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汉武帝对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寄予厚望,为了将其立为储君故意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14月乃生的奇迹。
中国有句老话叫“疏不间亲”,江充敢于离散人间骨肉,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江充深通人情,他认为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诸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而在权力的诱惑下,更无骨肉亲情可言。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
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当权者怀有刻骨的仇恨。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虽然他扳倒了赵王父子,但赵王彭祖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只不过是武帝的眷顾罢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地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也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源泉。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用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明察秋毫。
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此时,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就只能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
他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在位50年的汉武帝,这时已经66岁,离他归天只剩4个年头了。
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很迷信。虽然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仍然确信冥冥中的巫鬼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的蔓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品。
“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合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因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所以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他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青云直上,并封侯,最后竟被提拔为丞相。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让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惶惶不可终日,但公孙敬声却更加骄奢、肆无忌惮。征和中,公孙敬声竟擅自动用北军钱1900万,最终因事发而下狱。
公孙贺爱子心切,不忍将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打算立功来赎公孙敬声之罪。
这时,朝廷刚好下诏捕拿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不久即大功告成。
但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拿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由于游侠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在他们之中早已广为传播。朱安世非常了解公孙父子的罪过,说:“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在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公孙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官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得深究外,第二、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入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虽然古人规定了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
他本人的感情。卫后失宠之后,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之时,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江充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且已稳操胜券。
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木偶人阴影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史书记载:“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常常恶梦不断,直至最后竟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种隐患,武帝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
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血腥大比拼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中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他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
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人都被弹劾为大逆不道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高达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无奈之下,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左袒右顾都难逃被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许可以转祸为福。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江充太过于自信,对武帝和自己的力量过分依赖,以致没有听从帏说的建议,行动迟疑,最终束手就擒,韩说也破格杀。江充被捕获后,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亡归甘泉(宫)言状。”
一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城监狱中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发动了军事叛乱。
此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麓。刘屈麓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120多个儿子中的一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不合适。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挺身而逃”并丢失了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骑马跑到甘泉官,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给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I临战布置,表明武帝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逾10万人死亡和不少大臣被诛杀,一场新的清洗也随之而起。
戾太子兵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一农户家中。“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
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但太子的兵败身亡,却让武帝更加焦躁不安。他虽然贵为皇帝,但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愿做无骨肉之恩的残忍之人,所以难怪他以后的行为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
太子逃亡生死未卜之时,壶关的一个叫令狐茂的老臣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篇上书中还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
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上书中感觉到人言可畏,他很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对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建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白自己的心迹,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车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人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江充把一生献给了汉武帝,并为他担当了全部历史罪责。但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他仍然是一个牺牲品。
汉代以江充为代表的出身于商人平民的酷吏,与那些皇亲权贵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随时都准备以卵击石,主父偃的“大丈夫生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正表达了这些人的人生目的。
在以帝王将相家谱为主的正史中,江充以“大奸”而遗臭万年,连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之内。但只要通读过汉代典籍,就会了解到,江充并非“大奸”,亦非“贼臣”,而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复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