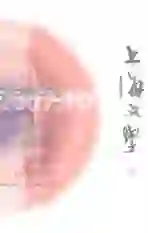白斑阿黑
2007-12-29石方能
上海文学 2007年10期
知情知义,狗命挨踢。
——乡谚
狗的屁股揩不得,一揩,它就叫,还咬人。不过那时我太喜欢它了,一点都不计较它。我和二姐是清早到余家塘一户养狗娘的人家把它买来的。那狗娘下了一窝狗崽,人都说种好,劝我父亲去捉一只。父亲打铁不得空,就派二姐和我去。我们一进狗老板家,就见一条狗娘张开四腿站在堂屋当中,肚皮上的奶子长长地吊着,就像城里肉食店挂的两排诱人的红香肠,一群狗崽你争我夺地伸嘴吊奶子,争得唧唧唔唔,时不时地掉下一只来,毛茸茸地在地上打一滚,再爬起来往上咬吊。旁边,蹲着几个人,把头探到狗妈妈的肚子边,那样子也好像想争着吸一口狗奶。原来是几个先到的捉狗崽的人在看狗牙。二姐和我急了,把扁篓一放来不及进行太多的选择,就捉了一条腿最粗的家伙。当我的手抓住它的后颈皮,提起来,迫使它松开了妈妈的奶子时,它在空中蹬腿挣扎,嗷嗷叫。狗妈妈喉咙里也发出“哼——”的生气的声音。我们慌忙把它往篓里一放,盖上杉木皮,绑好,付了钱,匆匆就走。一颗心高兴得快要蹦出喉咙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们遵照父亲的吩咐,把它提出来揩屁股。父亲说(大家也都这么说),这样它今后才不会把狗屎屙在家里。我把它提出来,捧着,二姐则用早已准备好的竹篾片刮它那个小小的肛门。想必是刮痛了吧,它大叫起来,咬了我一口,有些痛。我想打它,愤愤地扬起手,又忍了。我知道它想妈妈了,就像我离家做客时想妈妈那样。“喂,小黑狗,黑狗崽子,你莫想妈妈了,今后前边那个铁匠铺就是你的家了,你快认认屋后边的山,屋前边的禾场和路,屋边上的梨子树,今后可不要搞错哦!”
到家了,父亲停住锤子。“什么样的狗?”“一条黑狗,脚粗哩。”父亲要我们打开看。“好多钱?”“三块半。”“你们捉时还有好多吗?”“还有好多,我们照您的话选脚最粗、最逗人爱的。”可是父亲说:“去退掉,换一只来。”“为什么?”“它头上这块白斑——”
这我知道,它头顶上有一丛方形的白毛,就是我爹说的白斑。它全身毛是黑的,头顶白出这么一块,就像一个头顶白帕子的乖媳妇(它可不是女的)。我喜欢我的狗儿有这么个好认的标记,已和二姐商量给它取名“白斑阿黑”哩。“长白斑不好?”“嗯,只要不是黑狗,不是长在狗脑壳上,没事。”“黑狗脑壳上为什么长不得?”“……”爹不肯说的样子,只要我和二姐去退换。不久我们只得又去了。“换了?”“没有,那些被人捉光了,老板不肯退。”于是只得养起来。
“我家有只大黑狗哎,骑起狗来当马走……”我也可以骄傲地这么唱了。那年我四岁。
然而还并不能当马骑,它还小,我们的白斑阿黑还很小哩。最多把它夹在两腿中间,用手捧住它脖子,弯着腿同它一块走路,算是骑马马了。然而这样玩久了腿会累,需要变出法子玩。
我家门前的禾场很宽,上边有一层浅浅的草,绿得很,干净得很,在上边追逐、打滚是件开心事。我弓起身子,两手着地,模仿四腿狗的样子又蹦又跳,逗得阿黑高兴,让它以为它有了个狗伴。它把那对黑黑的眼睛盯住我,然后把头那么一撇,撒腿就跑,那是想逗引我去追它。可是我到底不是狗,四肢着地走不快,追不上它。它没办法,只好主动来进攻我了,一口咬住我胸前吊着的衣襟,像吊它那狗妈妈的奶子一样,不松,小狗头还往两边一甩一甩。我怕妈妈骂我撕烂了衣服,急了,“嗥——”,喉咙里模仿一声虎吼。黑狗一惊,松了。
黑狗还喜欢听白话。我和它玩累了后,就面对面坐在草坪上歇息。对面山上呢,这时候就有一长条白云,卧在半山腰不动,也在懒洋洋歇息。我问:“你爱听白话吗?”它竖起两只小耳朵望向我,屁股着地,两只前腿笔直地撑着,那认真的样子好像是说:“爱听!”于是我就把祖母讲给我的一个白话故事讲给它听:“好久好久以前,桃源洞里有那样两兄弟……”它静静地听着,好像我和它也成了两兄弟。但不等说完,它就耐不住性子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面山上。这时对面山上往往有人在砍柴唱歌,咔咔的砍柴声伴着歌声:“太阳出山哟四山明,唱支山歌吔把姐听。不唱那个山歌咧冷清清,唱得那个山歌来姐骂人……”它两耳尖尖地听着,眼睛专注地望向对面山,并尖着嗓子生气地叫几声,好像它真是头蒙帕子喜欢骂人的“姐”一样。正在打铁的父亲和徒弟甫田哥见我同狗在扯白话,就笑。其实那时的我除了它还有谁听我扯白话呢?三个姐姐都比我大,且有她们自己的兴趣,比我小六岁的弟弟那时又还没出世。别人家的孩子也隔得远,不常来。阿黑填补了一个山里孩子的寂寞。
近年关了,家里要杀过年猪,请来了毛屠户。毛屠户本不姓毛,只因为杀起猪来毛手毛脚,猪肠子都翻不干净,就被人叫做“毛屠户”了。尽管我小小年纪,也听人说起过毛屠户还有个特点:爱打狗,吃狗肉,一餐能吃掉一条大狗,所以也有叫他“狗屠户”的。毛屠户提着杀猪刀、挺着胖肚子进了我家,我小小的心子吓得怦怦跳,慌忙暗唤来黑狗,一把抱起进了里房,关上门,藏它在一个箩筐里,盖上盖,以为妥了,想不到它自己不争气,急得在里边乱叫,以为是我要害它。这时外边正好传来猪被杀的哀嚎了。我一急,又一把将它掏出来,抱到妈妈的床上,用被子罩住不准它出声。想不到它在里边挣扎叫唤得更凶。它的叫声引来了妈妈的敲门声,“能儿!能儿!”我以为是要来杀我的狗了,护住被子大喊:“不准杀我的狗啊,不准杀我的狗啊!”我哭了。
一年多后,阿黑长大了。它是那么黑,黑油油的,就像每一根毛尖都渗出黑而亮的油星;它头顶上的那块白斑呢,更白了,像一层雪;骨架结结实实的,像牛崽。我的白斑阿黑啊真漂亮!
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在火炕边烤火,听上边屋来的白天师扯白话。白天师被划的阶级是地主——那时候“地主”是倒霉的,在生产队被管制劳动时老挨干部的训,一声“你这个地主分子还想翻天哪!”他就头低到了胯裆里。但他一到我家火坑边就恢复成了天师,白着两眼大讲山海经。这时候,木柴火冒出一丝丝青烟,柴缝里时不时炸出一个小火星,火苗苗像好多条狗的红舌头,在顺着铁炉罐的底部往上舔。窗纸在老北风里呜呜地叫。阿黑这时不知是受不住寒冷呢还是耐不了寂寞,也从门外挤进来,火炕边蹲下,装着听白话的样子凑热闹,两只亮晶晶的狗眼讨好地看看这人,又看看那人,里边燃着两堆小火。但突然,也许是外边有动静,它耳朵转一个弯,向外一张,喉咙里随即鼓出一声“护”的音来,身子腾一下就射到门外去了,在阶沿上站得像个炮架,把“汪汪”声放炮般地推送到那边的山湾去。这之后它就不再进来烤火了,好像自己失过职一般,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一无遮拦的冰冷的阶沿上。
“唉,是条好狗啊,只可惜这头上的白斑——”白天师说。
我不服。我找来一个最大的箩筐,在里边垫上稻草,给它做成一个暖窝。“有白斑又如何的?您老的顶上不也是白的吗?”我冲着天师那一头白发问。
“你这家伙,没大没小的!”爹出来教训我,“人的头是老白的,你敢扯到狗脑壳上去!——你没见邻家老了人孝子头戴白孝布?要是大年初一问这些,看我不敲你一‘丁公’!”父亲屈起手指,凸出指节骨来威吓我。
我把狗窝放到门外,让它睡到里面。我想不清它头上的白毛和孝子戴孝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到它冷。它摇摇尾巴,舔舔我的手,躺进去了。夜很静。
我上学了。
学校在芦家坊,离我家有四五里。上学的第一天我就险些遭了殃。那是个大村子,百多户人家,人多,狗也多。我提着一碗饭(当中饭的)随一个叫文举的同学一块走,还没进村,许多狗就朝我们叫起来。我正慌,想绕路,不想一条大黄狗呲着牙不声不响地窜上来了。我撒腿就跑,不出两步,裤脚就被“呼”地一下咬住,一挣,裤脚“嚓”地撕破了,手下提的饭碗“当”一声跌在地上。大黄狗得了实惠,低下头美餐一顿去了。我虽然免了一咬,却饿了半天肚子,回家后对父亲哭诉,要大人送才敢上学。“要大人送?都不得空啊!这样吧,明天让黑狗送你,它胆大身大,保得了你的驾。”我却替阿黑担心……
第二天,我唤白斑阿黑出门。平时它是很少出门的,因为爹规定只让它看家。看到正在炉旁打铁的那个最大的主人同意它出门,阿黑就兴高采烈上了路。它一会子窜在我前面,一会子又落在我后面,不停地用鼻子嗅地上的新鲜气息,遇到电杆之类好记的标志物就撒几滴狗尿——据说狗行千里而能自己回家,就靠一路闻它自己留下的尿骚味儿。就这样,它轻轻松松、我忧心忡忡地到了芦家坊。
“汪汪汪……”潮水一般,白的,黑的,黄的,花的,数不清有好多条,全像听到了警报,聚拢来了!
它们要把它们的猎物围在中间。
那些恶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放过了我。我偏在一边,替阿黑捏一把汗。我听说过,这些恶家伙不光咬伤人,还咬死过不少过路狗!
阿黑从容地稍退几步,退到一堵断墙边,确保了背后无敌以后,就镇静地等待它们。它四条结实的腿站得笔直,像四根房柱;粗壮的尾巴也竖得笔直,尖梢还稍微向前卷曲,像一把朝天举着的钢刷子。它把它那有白斑的头昂得高高的,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气势汹汹想逼过来的狗群,像一个戴白盔的将军在巡视他的士兵。那些恶狗都埋着头,列成阵,眼里露出绿荧荧的光,一齐发出低低的“哼——”声,像是商议着欲扑过来。然而过了很久,它们还没有扑过来。
僵持着。我不知道会僵持到什么时候。
忽然阿黑动了,一步步走上前去,逼近恶狗去;我一惊,只见它昂首阔步,背脊上的毛也竖起来,微微发怒的样子,向最高大的一只(就是昨天追咬我的那只)逼近,把阔大的嘴顶过去,像是嗅对方的气味,又像是要开口咬了。我想,这一下会咬起来了,咬起来了!但——那坏狗这时竟然后退一步,竖起的尾巴像风中的毛竹一样弯下去、倒下去了,最后紧紧包了屁股。其他狗见状,也纷纷后撤。真奇怪。
这之后,阿黑天天送我上学。那些恶狗知道了我是阿黑的主人,一望见就像折断了喉咙似的停止吠叫,对文举也不敢逞凶了。路上若有高年级学生想欺负我们时,阿黑就会扑上前,露出一副凶相,吓得人家喊爹叫娘。一帮小伙伴羡慕我有这么只狗,跟着唤它“白斑阿黑”,还敬称它是“白盔将军”,恨不能让他们的狗也头长白毛哩。
“白盔将军警卫员哎,伴我打仗上前线,上前线……”我放学路上这么得意地乱唱时,文举却悄声告诉我:“你明天不要带白斑阿黑来了!”“为什么?”“听说芦家坊有几个大人打了商量,说你这狗是条戴孝狗,不吉利,进他们村会给他们带来霉气,他们要……”“他敢打!”“要提防啊。”于是我无言了,我只得从书包里拿出一瓶刚买的墨汁,泼在阿黑的头顶上……
然而这不是长久办法,隔几天那块毛又变白了,它毛里有油,不听染。于是我只好向妈妈求助。“哎,这狗是好狗,只是这一块白斑……”妈也这样说。
第二年,我得了一场急性黄疸肝炎。病来源于和我同桌的阿吉。开始是我发现他眼变黄,一上课就垂下脑壳睡大觉。接着我也一身软起来,一丝力气也没有。据同学说,我也成“黄眼狗”了。家里人急了,叫我休了学,用副竹轿子抬着我往区医院送。从家到区医院有二十多里,走完二十里路后,就搭船过资江,再走五里才到区医院。父亲和甫田哥抬着我,出家门时,阿黑要跟我走。“回屋里去,”父亲对它发令,“在家看屋,这回不要你送!”它于是退到门口,从门槛上伸出头默默望我,直到我们转过了山坳。
轿子在慢慢移动,那个铁匠铺家屋在离我渐渐远去。三里,五里,七里……我忽然变得伤感起来,觉得这一回离开后,好像难得再回来,或回来难得再见到家中的谁了。我擦了一下眼角,仍向后望。后来,视野里出现了一点模模糊糊的黑影。那黑影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慢慢地向前移动,我们停下它也停下,我们开步它也开步。我一惊,再揉揉眼,仔细望去,我望见那熟悉的身影了,我还模糊地看见了那头上的一点白。我知道是谁跟来了,心里热起来。
它走得很慢,很慢,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惟恐被我父亲发觉。山路弯弯,路两边是高大的山峰,山峰上是郁郁苍苍的树木。它在两山夹峙的山路上显得那样小,那样淡,有时完全被淹没了,好久好久没有跟上来。这时我就想,它回去了,这次它真的不再来了。
到了资江边,搭船了。我请求父亲慢一点上船,父亲不同意,只得上了船。开船了,它没有来;船到河心了,还不见它出现;快靠岸了,还望不到它的影子。一直到我们离了船,上了岸,我才望见家乡那边的河岸上,慢慢出现了一个黑影,怅然地抬起一个带白点的头,痴痴地向这边凝望。然而立即模糊了,是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你哭什么?”父亲问。我用手一指河对岸。随即,我父亲的眼里也泛出泪花。
一个月后,我病愈出院回家。当我呼唤我的阿黑时,却不见。
我连忙问妈妈。妈妈告诉我,我住院后,奶奶也忽然病了好几天,父亲也头痛得像挨铁锤砸,家里的鸡瘟了一半,大姐踩缝纫机时被机针扎了手……几件事一齐来,上边屋的白天师就说这和黑狗头顶的“戴孝”有关——“戴孝”就是“戴灾”“戴凶”呵,过路人也这么议论。我家本不信这一套的,我奶奶信基督,不准后人信这一套的,但不知为何,家里还是把狗卖给毛屠户了。
阿黑!白斑阿黑!……
天暗下来。对面山上黑黢黢的。我呼喊着,声音撞着对面山,像找不着路折转来的游魂,跌回那空了的狗窝里。
一夜中我几睡几醒,似在忽明忽暗的路上走,找它。后来全亮了,原来阿黑就在家门前的禾场上,还是刚进家时那么小,仍然竖着两只小耳朵要与我讲白话。但这一回是它讲,我听,我学它的样子坐着听,看它的嘴一开一合:“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对狗兄弟,两个的毛都是金颜色的,被人当作金狗宠养着……”我耐不住性子了,问它:
“你既然晓得,那为什么不长金毛呢?”
它两眼黑黑的发痴了。
“你为什么不长成人,能安然活着的人呢?”
它发了一回痴,忽然“呜——嗷”地哭了,那意思是这事由不得它自己。忽然一只大肚子罩过来,它不见了。“呵,我要拿把刀来剖开这个大肚子!”——我一举手,醒了……
是的,我直想把它救出来,还要为它辩个清白。它一定是蒙了大冤。我体会过被冤是什么滋味。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学期的一个下午,家里有五元钱不见了,妈妈怀疑是我偷去买糖吃了,骂我是一贯的“馋舌头精”。那一次我分明没偷,就分辩,但越辩越辩不清。我又悲伤又气愤,一口气逃到对面山上,躲在树林里不肯出来。天黑了,山里黑森森的,风吹着树林叶子,沙沙啦啦响,像鬼拍手。这时爹妈在到处找、喊,我却不答应,只是嘤嘤地哭,脸上、衣襟上、手上都是泪。这时我忽然感到有一个热热的舌头在舔我的手,一个熟悉的身子在拱我的腿。我知道这是谁找我来了,孤寂和恐惧的感觉立刻消失。我捧起它的脖子,感到它送过来一股暖烘烘的气息,我就情不自禁地把带泪的脸贴过去,让嘴吻在它的鼻尖上了。我随后跟它回了家。后来,阿黑用爪子狠命地掏仓房下的一个老鼠洞,竟然掏出了一张被咬缺了边的五元币……
然而现在的它在哪里呢?也在对面的山上哭泣么?如果我能找到它,救出它,帮它洗清冤屈,像它找我帮我一样的,那该多么好呵!
白斑阿黑!白斑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