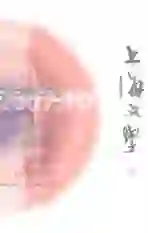乡村小说:时代之变与文学之难
2007-12-29施战军
上海文学 2007年10期
中国的乡村小说,在专业研究者那里,备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创作:一种是依托于现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而构织乡村想象的长篇小说,具有史诗性的时空架构和寓言式的意义世界,而且习惯上,作家倾向于认为乡村史诗便是要写乡村之“变”。无论是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与彼时意识形态关系较为密切的作品,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也可以包括新时期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等等,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以“人性”观念重建乡村历史并反思和反拨以往意识形态影响的作品,如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及至晚近的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等等,从广义的角度看,它们都在集中体现历史之“变”。只不过前者“过去”和“现在”构成“黑暗”与“光明”的二元对立,所要凸现的是其政治语义——社会结构发生的“翻天覆地”,结果一定是农村生活的改善,让人们明白“是谁改变了乡村”;而后者所要揭示的是在历史强力作用下本来应该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被异化为客体的过程性真相,所要探究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由大事年表构成的顺时针的“历史运动”,而是“人心”和“世道”的复杂关联,有的甚至倾向于富有激情的“历史批判”,成为呈现“礼崩乐坏”历程的史诗和饱含忧愤的“人心”挽歌。后者跟前者比,视角的位移,带来追问方位的相异,“科技理性”发展观那种关于历史的无所畏惧光明向前的信条遭到了质疑,“人文魅性”的关于人际的关爱怜悯和人对命运、环境及未可知的事物的敬畏感有所浸润和加深,于是在“变”的历史中探寻可能“不变”的东西,渐渐成为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等艺术要素背后的文学意志。
重识王润滋
其实,在面对历史运动和世风之“变”,某种人文性的自我生活追望和内心自律的“不变”这一主题的真切把握方面,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也很大。高晓声在20年前写的《李顺大造屋》就是在表达这样一种乡村人“不变”的顽固意志,他用短短的篇幅维护着百折不挠的农民本能——乡村的生活传统里对“屋”的生存性信仰。而在笔者看来,1980年代上半期,在王润滋短暂的创作生命历程中,他以《鲁班的子孙》为代表作品,对乡村生活变化中的人文性的自觉体察,尤其是对乡村的新的人文本份的危机的捕捉和深度映现,更有着特别的文学史意义。
王润滋的小说可谓出手不凡,他的《孟春》、《孟春辞职》、《卖蟹》、《寒夜里的哭声》、《亮哥和芳妹》等在1979年至1981年期间无论从时代内涵还是叙事艺术看,都是上乘佳作,它们能够在现实变革的亮色表现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展示人性和生活的复杂层面,尤其是在对人物性格和主体情绪的挖掘中,能够给沉浸在政治、经济的解冻喜悦里的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隐隐的忧思,而这一切都是饱含人情和希望的,这样的一种贴地写作姿态,包容着大量丰富的生活信息和精神信息,因此作品所呈现的“世道人心”是可信的。这为他以后写作《鲁班的子孙》这样相对更具时代道德反思力度和人文内涵的优秀作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道”与“人心”一直是王润滋的小说所要表现的基本主题。而这个时候已经和1940年代的仅仅以土地诱导农民的时代有了不同。那时候沈从文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学者对于农村言改造,言重造,也就只知道以财富增加为理想。一个政治家也只知道用城市中人感到的生活幸或不幸的心情尺度,去测量农民心情,以为刺激农民的情感,预许农民以土地,即能引起社会的普遍革命。”①时代不同了,可是“只知道用城市中人感到的生活幸或不幸的心情尺度,去测量农民心情,以为刺激农民的情感”这种认识和对待乡村和村民的态度和做法没有变,“全想不到手足贴近土地的生命本来的自足性,以及适应性”这一点人文性认知更是没有任何改观。到了新时代,对农民利益诱导的实物已经再一次使用过土地,新的实物是样式渐多的生财致富之道。
正是在那由政治权力化的社会向经济自主化的社会转换的初始时期,“世道”与“人心”产生了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形成也较为深刻地告诉人们:对于生存于底层的百姓来说,世道的新变中,政治的力度往往并不能彻底地对人心构成颠覆的危险,而经济的杠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撬开人际观念和心灵传统的防护网,而对“人心”的持守,在少数年轻人这里有所坚执,在没有见过“世面”的老人的身上更有顽强的自足的表现。也就是说,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才固守这颗使大家都感到温暖亲和的“人心”。《卖蟹》所展示的风情画一样充满美与善的场景中,具有活泼人性美的小姑娘对精于算计只顾一己之私的胖买主的嘲弄,就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人心”的判断。隐在的世情描绘藏在显而易见的德性褒贬背后。这类小说还有关于选队长的故事《孟春》、《孟春辞职》等,“世道”里孟海与孟春的较量,是精明自私者与憨厚实干者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拉据战,而“人心”的指向即是普通农民怎样过上好日子。人们对于“能人”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这里时代的要求似乎与人心的选择取得了一致,但是孟春的辞职更有震撼力,因为这里既有作家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也有对于世风转变的人文态度。也正是这样,王润滋的小说具有主体的单纯性和现实的复杂性相缠绕的特色,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更具有客观、实在的品质。
到了《鲁班的子孙》,世道与人心的悖论开始得到自然的显影,并以代际之间的冲突方式表现出价值判断的倾向性。首先一个层面,本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农民集体观念与现实发家致富的个人发展欲望产生了激烈的冲撞,这种冲撞首先来自时代的悖论性设置:大集体的生活模式已对集体生存本身构成了难以为继的局面,而个人致富的实现又须以丧失其他人的拥护甚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于是“人心”成了一种遭到质疑的对象,时代和世道带给两种生存观的道德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接下来的第二个层面则是更为具体和深在的代际观念冲突,黄老亮祖传的手艺人的道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一方面过去以慢工出细活的精湛的手艺让人满意佩服的尊严感不再被推崇,一方面那种以对得起良心的劳动而获得幸福的生活也正在萎顿甚至濒临绝境,而后代的机械化复制性的规模经营则是唯一对路的生存之道。手艺的失传和无从施展,说到底,这是乡村传统的人文危机的表征。
王润滋在描述传统的良心时,故事和情绪显得饱满而游刃有余,而在针对舍义取利的人物与心理行为的叙写时,则常常不能深入到内部,这也是作家面对变革时的惶惑,尽管他的小说客观上对于呈现了生存悖论的时代的揭示是最有认识价值的贡献,但在艺术上,对于矛盾的另一面则显得力不从心。
王润滋小说所展现的民间理想境界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在生存界面,农民过好自己的日子是作家所最为钟情的主题,这是孟春们的理想也是鲁班的子孙们的理想,一代代中国农民苦难的生存也生出摆脱苦难的渴望,王润滋所有对于贫苦的底层农民的描绘,都是为了表达对于脱贫的向往;二是在伦理层面,在贫穷的阴影下中国农民道德上的质朴和高尚,是王润滋下力最多倾情吟唱的主音调,那种相互取暖的精神欣慰尽管是含泪带血的,但它表现出不可或缺的价值。这两方面,王润滋是极其真诚的,无论在世道人心的变化中,还是在生存信念的守护中,作家都以一颗赤子之心歌咏属于农民的理想,“自己的日子”与“他人的日子”同等重要,《鲁班的子孙》中黄老亮就是这种乡村人文理想的化身,他的理想不在于高高在上的人类大悲悯,而在于具体地生存于时代变革途中的普遍百姓的生活中间。百姓的人性观念只有两个字:良心。而面对良心的安慰/忏悔、爱/恨、功/罪也是民间人文理想的派生物,农民的宗教就是对得起良心,良心的缺失即是他们的原罪。黄老亮认为“人都有罪。有的人罪重,有的人罪轻;有的人罪在行为上,有的人罪在心里面。谁心里有罪,谁自己知道……”这种充满宗教感的道德自审,使具有传统人性的农民形象在宽与严、忍耐与忍无可忍的道德空间充满了艺术张力,那种有错一味往自己身上揽的襟抱,是民间坚强而无奈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必然反映。即使无力回天也要用尽心力,即使生存失据也持守本分真诚,千百年来的乡村就是靠着这朴素顽强的人文性的生存理想,生息和喘息下来的。于是我们从这支悠长的乡村人文挽歌里面,听出了不甘和不弃。
王润滋的小说在哲学的层面上表现了对于自然与生命的高度尊重。他的批判是绵软的。是一种不忍下手的轻轻击打。他的人性赞美显然大大多于人性鞭挞。正是这样的情感态度,也展示了一种乡村人文精神因为宽容而导致的复杂,这种复杂是在一种向往健康、生气和美好的生存境界的主体情绪中自然流露的。他的小说从姿态上是对生他养他的母土的报恩报德,因此具有相当丰富的情感因素和伦理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王润滋的小说尽管写在一个变革时代最为剧烈的当口,却回避掉了许多因历史尤其是政治的动荡所带来的普遍变异的人性现象,而且他决不把负面的东西作为批判与反思的主要对象,而倾重于具有传统人格美的人物的自审方面。由于这种自审是内敛而趋后的,于是面对世道人心的变化就只能到自身的“惶惑”为止。
“十七年”时期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里老接生员与《鲁班的子孙》里老木匠的“惶惑”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两代人之间的不理解其实都是发展中的时代的附带物。只不过,黄老亮多出来的是对“良心”的忧虑而已。在时代变迁的背后,潜隐着的是对封闭的观念、价值的重新估定,《鲁班的子孙》只好以黄老亮对儿子生母的善待作为最后的“良心”寄托,实际上已游离了对于小说主题进一步开掘。小说在道德伦理的层面是感人的,但留下的遗憾是对乡村人文遭遇的深层开掘的回避和对人性新的变数的不忍细察。
王润滋以《鲁班的子孙》为代表的小说,对“变”是敏锐而知情的,但又决不愤怒,乡村手艺人敦厚的襟怀其实是古老中国积淀下来的人文理智的显影,有一种内在的持久的感人的劲道,令人难以平静相对——就像我们看见自己一生按规矩生活而晚年沉默无语的老父亲,他心里的隐痛和不安,令人不能不心疼和亲近。
“立场”的变异与“写实”的需要
从建国后十七年的乡村小说,一直到1980年代,乡村小说一直是一种“立场”彰显的书写,而且几乎都是代言性的,是作家通过人物甚至自己的议论,在作品中代“时代”和“人民”在说话。变革、爱情加上乡土风情、民间文艺表现形式是乡村小说所常用的乡村符码。张宇的《乡村情感》、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给这种创作风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但基本的立场没有什么变化。在这里,我们不予细述。
这种代言性的立场写作情形,在1990年代以来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其中较为“另类”的表现,是立场隐形书写,让乡村世界自现其身,在“立场”上和主体叙述上近乎完全隐形的乡村小说。这在晚近的《妇女闲聊录》、《秦腔》这里,有着不言自明的表现。这样的长篇小说让我们想起遥远的乡村小说初创时期和“丰收”时期,茅盾对彭家煌和叶紫的评论,已经透露出乡村小说的要素之一所在:方言和农事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小说,似乎决定了作家对乡村的客观度的把握和对趣味、风物、习俗的态度。这一切在今天,它们不能不通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文课题——写作中对乡风礼俗的客观描摹和方言的使用,便是文学对民生和民瘼的客观呈现,也是乡村小说与实在的乡村相洽的通道。当然也会带来另一面的问题:叙事的力量有所减弱,语势变得相对懒散,思辨的内在力量置换为某种过渡性的原始呈现。
自从1996年出现了以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写作现象,这一类写作,其深刻性在于呈现了在乡村企业化进程中,工商意识形态的利益驱动所导致的乡村情感和道德的被迫出让,客观上展示了乡村文化不得不走向与城市文明同化的历史趋向,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最基层的村民利益代表者的内心冲突和尴尬无奈的举动,让人们感知到了人的“异化”这个原发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已经大举传染到了中国乡村的生活中间。从这以后,乡村写实题材小说的醒目程度就一直没有减弱过。但是大量的乡村小说,艺术上粗劣的问题相当严重,而且多数小说在对新的变化的敏感度和乡村结构的深度探掘上用心用力不够。生存浮面上的悲与喜在农民身上已经足够活灵活现了,可是农家所赖以生存其间的乡村世界的秩序性结构性变动的深在内容却更是罕有触及。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所必备的人间关怀,我们并不欠缺,由“五四”而来的对乡村人群的集体启蒙传统也没有丢弃。但是,相对薄弱的是对表相背后人的意识、性格、心理的新发现,不仅如此,新的国家观念和时代生活给乡村的风俗社会所带来的伦理动荡和价值体现方式的激变,作家们几乎没有提供相对深刻的文学性呈现和思量,使得乡村小说整体上显得轻飘油滑。
面对新变
近几年来,专事对中国乡村现状以一种“写实”的笔调进行叙事的创作依然没有减弱热情,还是以中篇小说为主,但是已经和十年前有了新的嬗变。乡村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为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现实资源,除了“农民工进城”给乡村带来的冲击,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新变,即村一级民主和法治社会建设。与此相关,敏感的作家已经创作了意味深长的佳作,比如乡村“民主”(“村级干部选举”不同于城市礼堂的划票,而是光天化日下的互动“喊选”)之于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乡村“法治”之于李辉的《村官》。
李洱曾以对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的写作见长,但是,他在作品中对乡村的打量和体验由来已久。农家子弟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乡村是他们的“原乡”所在,李洱小说里的人物也概莫能外。孙良,这个人物先后出现在李洱的《喑哑的声音》、《悬浮》和《光和影》中,在《光和影》里,掌握了现代技术知识的孙良,只是城市里面的底层小人物,原乡的史志典故和属于城市文明的电脑网络语汇、英文、星座、光碟等等“知识”在打斗推搡、媒体曝光、生计压迫种种具体生存困局面前,都成了新的“知识无用”的注脚。孙良的回乡饱胀着复杂的乡土情感,回乡的意图在于感恩,也是寻求混乱生活之下的安慰——这和典型的“乡土小说”在初衷上多么近似。然而回乡的路恰巧就是被追赶的尴尬之旅。作为“侨寓者”其实是流浪者的他,所到达的故乡却是面目可疑甚至着装滑稽的样子,如今的乡村实情,只是对大款的赞助(引进外资)、夸饰的标语口号和符号化的“现代化”摆设感兴趣,乡村情感被看不见的手武断地切割和蹂躏,乡村这个最后的栖息地已被偷梁换柱。被城市追赶放逐捉弄的孙良,又被乡村遗弃,霉运连连,险象环生,尴尬不断,乡村与城市给这样的游子准备了几乎相同的待遇。他自卑又不愿放弃自尊,身心不得安宁,生存和情感欲望无着无落地漂浮着,这简直就是他的宿命。
《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李洱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龙凤呈祥》的加长版,200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面对实在的乡村,李洱卸掉了知识分子的固有的“乡土情怀”,也告别了知识分子对乡村已成习惯的认识:“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脑子里的乡村是有固定化模式的,是已经符号化的。暂时不接受不要紧,只要你意识到乡村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这部小说写的是当代的乡村生活,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乡土中国的现实。”②小说围绕着村级干部选举,作者把乡村现代性的驳杂繁富因素多角度探照并轻灵地描摹出来。他以往“知识分子”叙述中“炫智”的成分得到了有机的克制,效果是,呈现的美学特质却显扬出主体审视参与审美对象的激情。今日中国乡村的动静在孔繁花的窗下生机盎然亦飞流短长。小小的官庄村与大中国和大千世界的距离忽远忽近,“全球化”和传统乡村意志互相渗透胶结,真正的农民和农民的日常劳动生活被悬置一边,权变和人际关系、控制欲和经济指数盖过了“乡土风情”,孔孟(请注意两大家族的姓氏)两家的权柄之争不再指涉宗法礼教,权谋凌驾于民主和建设之上,于是喜剧发展为闹剧,事情走向了原初愿望的背面。
李洱以超群的叙事能力,将本可大肆渲染的悲情立场的正义直书,转换为“颠倒歌”这种民间自得其乐的言语游戏的转喻,巧妙地回避了乡土抒情状的矫饰,自然而然地留出了相当充分的张力空间。生民思虑与阴性谋略的关系,通过一个小小的权变机缘,揭开的是热闹得有些折腾的一种生存实景;有了一个关乎生存的关节,形形色色的人就暴露出了一种潜隐在内心的明争暗斗之“瘾”,在乡村的日夜,人们为此而生出莫名的兴奋。在李洱貌似日常的叙事中,带出的是可以向无限广阔的现实人生和复杂的人性生存延伸的焦虑。这里有气魄,驾轻就熟地讲述农家大事;还有聪敏,将这一切布排在人的活动、表情、言语的细部,播种在乡村土坎的皱褶里,生长在房前窗下的密谈甚至叹息中。他们活着的目的是那样明确,对未来的意义又似乎存而不论。我们说这是一篇“乡村小说”,莫如说他写的是没有丝毫暗示却兴味深藏的“乡村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李洱以人际及权力呈现生存样态的审美视角,和《红楼梦》这样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关系更为亲近,巧合的是两部小说都以女性争权者的故事出彩。作者自己也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写作,应该说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营养……这几年,我经常想怎么重新检索并利用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他将这种审美方式运用于乡村写照,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的诗意的“乡土想象” 自觉地拉开了距离,“有些读者可能还想从中找到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写到的那种桃花源式的生活。很抱歉,我没有这样写,让一些朋友失望了”③。
中国现代对乡村以小说形式的观照由鲁迅领起,早期小说几乎都以乡土启蒙和传统意识批判为核心意向,从《故乡》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以台静农、蹇先艾、徐玉诺等为代表的作家,修复了“乡风民俗”的正当地位,弥合了批判和认同的边界,乡民的生存样态成为文学表现的合法性内容,使得区别于“启蒙乡土小说”的“乡村小说”(茅盾称之为“农民小说”)得以显形。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京派作家领衔的“精神乡土文学”阶段,地域风情和人际关系又如童话或禅境,乡村民瘼被乡村怀恋所放逐,直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师陀那里,寄寓于乡村的知识分子的诗性情怀达到了极致。四十年代以来的另一翼作家则投入到乡村运动史的抒情描写,从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到柳青、李準,乡村长篇小说大致上总是顾及环境大于人物,观念压过命运。对当世乡村予以直感的触摸和真切的探询(而不是先验概念的制导、抒情化的偏爱和居高临下的启蒙)的乡村小说,却一直是现代以来乡村小说被抑制的创作态度,虽然在实践层面曾有李劼人《死水微澜》、《大波》及赛珍珠的《大地》程度不同的少数成果,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前中国式的乡村文学主流所暴露的规避正面切入的偏执倾向。
从真切的维度判断,对今日乡村真相的关切,用传统的人际权力视角,的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要比现代的诗意想象和当代的革命豪情更能关乎乡民的痛痒和生死。关键在于是否还有未被探照的乡村死角,而它并不是边角余料,其实可能正是现今乡村光天化日下的真相。
而在我的阅读中,2006年李辉的中篇小说《村官》较有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村官》里的次要人物村长身上,还是延续了已有的乡村写实小说的特点,没办法,大概想突破也难。不过在主要人物金水旺还有他的帮助教育对象麻老三那里,却呈示了弥足珍贵的份量。如果你先自以为它跟泛滥的“乡村写实”一样,是专写乡镇长的喝酒骂人招商引资强权蛮横和不得已实行性贿赂那些老套的故事,那就真是你的错了。原因是,这个中篇小说,在叙事风格、人物塑造特别是对迁变中的乡村社会的新矛盾新症结的发现方面,体现了创作者应有的机敏和洞察力,在目前的乡村文学平面上,它对主人公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发展中的乡村的本质性变异的深度揭示,非常引人深思,甚至带有刷新乡村小说的意义。
所谓“村官”,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是指村治保主任。这个写实的形象及其常见的人事中所承载的几乎就是“新农村”隐秘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于是这个金水旺老汉的“公安”活动就显得不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作者经由这位“村官”的工作和心理遭遇,对当今乡村生活的真相和实质进行了一次方位新颖的艺术观察。老汉既谨慎细心又豪侠仗义的性格活现于纸上的过程,牵扯到乡风民俗、传统文化心理和乡民自尊感等诸多方面,所以视线穿透了深藏于普通的乡村生活面貌之下的名声和荣辱观念等更为坚固的精神层面。他对“执法”的理解更在于“情理”层面,他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些像为乡间人际的稳定平安作调解保障的权威,它的身份作用类似于长期在乡民社会里掌控奖惩和公平的族长。这一类人物(还包括能够张罗红白喜事的“能人”等等)也许是乡村难以缺少的角色,他们以某种仪式感让人们有所敬畏,从而保持相对安稳的乡间生活秩序。正因为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他质朴地认着死理,虽然心理上身体上连连受伤,但韧性却也愈发强劲,艰难不屈地把麻老三和秋英的老“案情”变成了新“姻缘”。小说最给人心灵震撼的地方是小说的最后,水旺老汉付出极大心血意欲重造“新人”的心意被彻底作废,麻老三故伎重演,权力与暴力角斗的生活重蹈覆辙。作为乡村“执法”者的水旺老汉抑制不住兴奋的成就感,只是来自终于使得麻老三和秋英成了婚这个乡间“大事”。沉醉的主人公像漫漫的乡村新生活长夜中曾经晃来晃去的手电筒一样,电量耗到了尽头。这个悲怆有力的“豹尾”,发生在热闹的结婚喜筵之上,钮支书的哆嗦似乎并不可怕,麻老三的“成熟”才是真正令人心生恐怖之所在。
小说通过治保主任金水旺老汉与体制、与乡村阶层上下的关系和他执拗的性格也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这个不尴不尬的小角色,它牵动着乡村的每一根敏感神经,也牵涉权力结构、村民生计、社会公平等等复杂而切要的现实问题。最普通的民众,他们的生存理想无疑只是安稳富足地过日子,而上述那些问题对稳定生活的撕扯,就纠结于这个负责最基层民众的安宁的治保主任身上。相比于那些村支书乡镇长,治保主任的视角也许更加便于我们探照到藏在这个时代乡村生活的暗角里的奥秘。
这部小说无论语言还是人物性格都有活生生的土味,阅读起来很容易进入情境,没有任何造作编排之感。同时,更明显的是,这部中篇小说自有它的现实认识价值,它让我们思索乡村内在的变化中所蕴藏着的许多待解的难题。一个是最基层权力的消解,从承包到取消农业税,基层干部的权限越来越小,老百姓完全可以不买账,发家领头羊的身份又不甘丢弃,一些基层干部只能摆着某种架势利用工程招标等机会捞取好处,于是最基层的腐败开始滋生,但也同时被另一种野蛮的力量所挟制;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动,是介入乡村的“法治”与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规约在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碰撞与合并,出现了用于调解和管理秩序的手段的软化甚至双重失效,以致于像《村官》写的那样,本想学好的麻老三循环回黑老大式的生存之道,水旺老汉的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感化均告失败。
在乡村,从宗族社会的伦理廉耻观念的规约到政权意志行政手段的介入,再到法治社会的提倡,这个历史链条上,乡村人无不带有混合型的生存策略,而且,如何让乡村社会走向稳定发展而不是畸形混乱的轨道,我们无从知晓。我们知道的是,目前文学创作整体上对乡村现实明显缺乏深度探知的迹象。
法治社会的建构与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的社会结构的矛盾;村民与生俱来的情理认同方式及其复杂的生存经验和法理的矛盾;中国政府对农业税的取消所带来的农民对基层权力不甚依赖甚至国家公民意识的淡薄;加上因基层权力阶层的腐败现象而导致农民对之厌恶甚至抵抗;尤其是来回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它们抽空了乡村基本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城市生存观念的冲击,它们见证并甚至以血泪感受到了城乡差别,同时又使得乡村世界的人生观念变得夹生和离奇……这些都是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状态。对这些“乡村的乱麻”,我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足够地予以艺术化的梳理,确实还有待于中国式的乡村小说对此进行“风俗史”般繁富的写照。
“变”与“不变”
城市对乡村的全面入侵已经成为时下写实性文学的新母题,近年还有一种描述极端反应的“乡村立场”的小说出现,以王祥夫的《五张犁》为代表。主人公五张犁的地被城市征用,成了园林的一部分,但是他找到了那块地,用莳弄庄稼的方式种花,春天播种夏天锄草——入秋还要收割。真的在城市里做起了庄稼把式,这样的小说更像“传奇故事”,“人文”一旦立场化观念化,就成了故作坚持的“不变”,就会不仅削弱了它而且可能走向它的对面。这和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那样的城市乡土小说所展现的决绝地弃乡进城的信念在可信度和丰富性上相比,显然是逊色的。
从水旺老汉这里回望,我们能够隐约地看到在现代以来的小说史上一个奇特的村民形象系列——那些农家老汉们。或者倔强或者在倔强中不失狡黠但总归是有些不识时务、认着过日子的老经验老规矩的死理的他们,牢牢地镶嵌在不可磨灭的中国式的乡村小说人物画廊的主要位置。从1930年代年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叶紫《丰收》里的云普叔,到1940~1950年代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二孔明、糊涂涂们和周立波写出的老孙头、亭面糊,再到柳青《创业史》里更加典型的梁三老汉,甚至也包括文革期间浩然《艳阳天》中的韩百安和弯弯绕,新时期以来还有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所写的刘三老汉、高晓声刻画的李顺大、周克芹写出的许茂、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里的福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所塑造的黄老亮,直至1990年代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中的封大脚以及新世纪李辉《村官》里的金水旺……迄今七十多年来,他们几乎是中国乡村小说史得以成立的支撑性的人物。历史的潮涌总是以时代“雪浪花”的方式,来“咬”这些老礁石,从“丰收成灾”到“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建设新农村”,这些老农所处的时代环境不甚相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各有所异,但共性更明显,他们显然是被作为一些“时代”的“落后分子”而设定,他们的老脚总也穿不好被“大他者”化的观念所模塑的“进步”鞋,在对待自己所在的世道的变化上,他们都有举棋不定或者挪移缓慢的性格和心思。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非敌非伙之间,他们接二连三地比“新人”更为醒目地站在了文学史之中。
时代求变,乡村小说的艺术样式也在求新,这并不意味着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也会机灵地随之成为时代的变体。
1 沈从文:《虹桥》,1946年6月《文艺复兴》第1卷第5期。
2 《李洱:文学从来不是蒸馏水》,载《新京报》2005年3月7日。
3 《李洱:文学从来不是蒸馏水》,载《新京报》200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