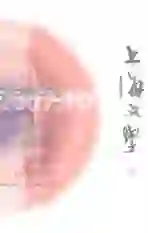美如缤纷的礼花
2007-12-29李元洛
上海文学 2007年10期
有一年远游西湖,湖光山色固然美不胜收,苏东坡早已有言在先了,许多与山色湖光比美的联语也惊艳了我的眼睛。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就有这样一幅对联:“三面湖光,四围山色;一帘松翠,十里荷香。”我对同游的朋友说:“十六个字中就用了四个数字,本来枯燥的数字忽然如灵珠四颗,使全联生辉啊!”朋友点头称是,并说中国特有的联语就是诗的分支,至少也是诗的近亲,西湖就有许多中含数字而溢采流光的联语。他见我是湘人,就举同是湘人的清代湘军名将彭玉麟《题杭州岳庙联》为证:“史笔炳丹书,真耶?伪耶?问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泣血;暮门栖碧草,是也?非也?看此一双顽铁,亿万世奸臣贼妇,受几多恶极阴诛!”
表面上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并非只在理论数学与实用数学中才不可一日无此君,而是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在经济范畴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周易》早就提出了有关数的观念:“参(三)天两地而依数,观变阴阳而立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认为“万物皆数”,“通晓数,可知万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今日社会数字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如身份证、老年证、门牌号、电话号、手机号等等,都一律实行编码,芸芸众生无一不是呼吸甚至喘息在数字的天罗地网之中,真是“数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过,数字虽说是地球人的共同财产,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夫利特曾说过的“人不能同时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一警语箴言,就颇得力于“两”与“一”的数字的妙用,然而,数字似乎更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语言,乃至数文化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当它们和诗缔结美满姻缘之时。
除了联语这一别系旁支,正宗的诗歌就是诗词曲了。“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这里王维《送梓州李使君》开篇四句,且不说每一句的第一字连读为“千山万树”,其中的“万壑”与“千山”又互文见义,“一夜”与“百重”复多寡对比,明人王士祯赞之为“兴来神来,天然入妙”,《古夫于亭杂录》清人纪昀美之为“起四句高调摩云”(《唐宋诗举要》)。“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中,如果“三”与“九”两个数字不前来凑兴并助兴,庐山的壮观与李白的豪情之表现,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同样,在杜甫的《绝句》中,如果“两”、“一”、“千”、“万”四个数字缺席而不上岗,如何能构成点线与大小相反而复构成的既优美又壮丽的图画?至于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除了每句第一个字连读为“万千孤独”而暗寓全诗的主旨之外,如果少了“千山”与“万径”的烘托,恐怕也难以表现渔父也即柳宗元寒江独钓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即以写西湖的诗词而论,白居易的七律《春题湖上》的“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颗珠”,正是由于“千重翠”与“一颗珠”的大小反形,才动人地表现了“湖上春来似画图”的西湖之美,而柳永的《望海潮》是咏西湖的名作,其中有许多数字组成的美妙词组,如“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之类,此词一出,不但喧传众口,而且引发了金主完颜亮的觊觎之心,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就记载说:“此词流播,全主亮阑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这种负面作用,大约是本意作正面宣传的柳永所始料不及的了。
数字,在诗词中发挥了它们的妙用,而在曲中则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因为曲除了小令之外,篇幅一般较诗词为长,而且曲本就来自民间,体裁与格调都偏于俗,数字入曲的机会就更多。例如“一”这个数词吧,《史记·律书》早就说过“数始于一”,“一”,应该是数词家族中的长老或元老,以“一”起始的词语、俗语与成语不知凡几。清代的清官张伯行有《禁止馈送檄》一文,可以为今日官员们的座右之铭,其中的“一”字真是一线贯穿:“一丝一毫,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 我为人不值一文。虽云交际之常,清廉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通篇五十六字,“一”字就有八个之多,他言行如一,可见一片冰心。“一”,在诗词中的踪影也无处不在,最早它在诗经的《王风·采葛》篇中出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由此而来的成语“一日三秋”至今仍有很高的引用率。“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写旅人念远怀乡之情,得益于“一”字不少;温庭筠的《更漏子》写秋夜的思妇怀人,“一叶叶,一声声,空阶调到明”,“一”字的重复状写风声雨声和梧叶之声,真是声情两至;“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词人贺铸的《青玉案》写愁情,其博喻中的首喻也曾借助于“一川”的荒烟蔓草。
然而,“一”字贯串全篇,而且反之复之,回之环之,这却是元人独特的创造。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伙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
——无名氏:?眼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演
无名氏叹老嗟卑,伤离怨别,六十个字之中,“一”字竟然出现了二十二次,密度甚高,可称罕见,而汤式对“一”字的运用,却别具一番情味:
冷清清人在西厢,叫一声张郎,骂一声张郎。乱纷纷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絮一会红娘。忱儿余,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牀。风儿轻,月儿细,开一扇纱窗,掩一扇纱窗。荡悠悠,梦绕高唐,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
——汤式?眼双调·蟾宫曲?演
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之后,张生与莺莺成了热门人物,元曲家也多所借题发挥。汤式此曲,就是借《西厢记》第四本张生与莺莺月下幽期密约的故事,对莺莺形象作艺术的再创造。全曲的“一声”、“一会”、“一半”、“一扇”、“一寸”五个数量词的重复贯串,加强了主人公感情的激动性和全曲结构的完整性,全曲好比是一座美仑美奂的楼台,但如果没有这些数量词的支撑,这座楼台恐怕早就坍塌了。
“一”如此,“七”也是这样。由“七”而曼衍的“七十”,大约是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过“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成为经典名言之故吧,宋人王观的《红芍药》就曾经写道:“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岁,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这一生命的数字,在元代卢挚的?眼双调·蟾宫曲?演中得到进一步的运算和发挥: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明,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年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鸟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只图自己“快活”,未免只顾利己而不利人,但宇宙永恒而人生短促,这本来是人之常感常情,也是中外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何况卢挚生当那个注定让人无所作为的时代,我们对他看破红尘享受人生的“快活主义”也就不必多所责备了。
别绪离愁,闺思春怨,是古典诗歌永远也不会厌倦的传统母题,不同时代的诗人,都纷纷以自己的体验和才能,对这一母题作出了不同的诠释,如同现在的电视荧屏的“同一首歌”节目,不同的歌手演唱同一首歌可以作出各不相同的表现。薛昂夫也是如此,他是西域回鹘(今新疆维吾尔族)人,但他的?眼正宫·端正好?演《闺怨》表现的却是汉民族诗歌的“闺怨”母题,这组套曲写闺中少妇与外出求取功名的丈夫离别之后的思念与忧愁,尤其动人的是第五曲的?眼二错煞?演:
料忧愁一日加了十等,想茶饭三停里减了二停。白日犹闲,怕黄昏睡卧不宁。则我这泪点儿安排下半枯井,也滴不到天明。
深愁苦恨与时俱进,情怀苦闷茶饭不思,作者通过数字对此作了具体感人的表现,特别是一之半的“半”字的运用,即安排半个枯井之深,眼泪也滴不到天亮时刻,堪称无理而妙。
西域人兰楚芳,元末为“江西元帅”,这位纠纠武夫却彬彬文质,其现存小令九首多以《风情》与《相思》为题,而套曲?眼黄钟·愿成双?演的题目竟然也是《春思》。不过,这组套曲写的是爱情的悲剧而非喜剧,在这一悲剧的歌哭中,数字又挺身而出,担当起表意传情的重任,特别是见之于其中的?眼么篇?演:
看看的捱不过如年长夜,好姻缘恶间谍,七条弦断数十截,九曲肠拴千万结,六幅裙搀三四折。
柔肠不是普通所说的百结而是千结万结,六幅裙也因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宽大了一半以上,正由于“七”、“十”、“九”、“千”、“万”、“三”、“四”等数字的联手操办演出这一爱情悲剧。更显得局内的主人公柔肠寸断,如果是多情种子,局外人的读者读来也不免会黯然神伤。
嘉兴人氏的徐再思,因性好甜食而号“甜斋”,时人将他与贯云石(号“酸斋”)相提并论,称他们的作品为“酸甜乐府”。徐再思之曲,好用数字。其实,历代许多诗人都喜欢在诗中用数,骆宾王就是其中的一位,唐代张的笔记《朝野签载》说:“骆宾王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天’,时人号为‘算博士’。”言下有讥嘲之意。问题不在用数与否,而在于“数”用得好不好,如果想得也妙,用得也妙,当然作者与读者都会皆大欢喜。徐再思的作品中,数字用得比其他曲家更多,不少都恰到好处,由生活而过度到诗,数字架设的是美丽的彩虹,如?眼黄钟·红锦袍?演套曲的第四首:
那老子觑功名如梦蝶,五斗米腰懒折,百里侯心便舍。十年事可嗟,九日酒须赊。种着三径黄花,载着五株杨柳,望东篱归去也。
全曲四首,在先分别写了严光、范蠡、张良等三位历史上著名的退隐人物之后,第四首便到了陶渊明的名下。此曲先引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典故,表现陶渊明对功名的态度,然后连下“五”、“百”、“十”、“九”、“三”、“五”共六个数字,写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弃百里侯之彭泽县令如敝履,不再为“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的红尘世俗所累。九月九日重阳节,独坐宅边菊丛之中,有王弘派仆人前来送酒:“三径黄花”,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而“五株杨柳”则源于诗人自传的《五柳先生传》。如同山泉自山中涌出而流淌,以下的数字都是从陶渊明的行事和文章中来,自然而贴切,中国诗歌史上这位“隐逸之宗”也就如闻纸上有人了。
徐再思写前人如此,写自己浪迹江湖十年的?眼双调·水仙子?演《夜雨》,其数字的运用之妙,也出自他的慧眼与灵心: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半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如果说赞美陶渊明是表现隐逸之思,叙写自己是抒发飘泊之苦,那么,描状他人的爱恋之情呢?徐再思也调动了数字来供他驱遣,如?眼双调·水仙子?演《春情》:
九分思爱九分忧,两处相思两处愁,十年拖追十年受。几遍成几遍休,半点事半点惭羞。三秋恨三秋感旧,三春怨三春病酒,一世害一世风流。
几乎每一句都用数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相思成病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明代的杨慎对唐诗人杜牧的喜用数词曾有微辞:“大抵牧之诗,好用数目垛集。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清代诗人王渔洋反驳他说:“唐诗如‘故乡七十五长亭’,‘红阑四百九十桥’,皆妙,虽‘算博士’何妨?……高手驱使,故不觉也。”我想知道杨慎读到徐再思上述曲作的感想,但可惜其人已杳,无从问讯了。
数字本来是用于计算的,单纯的算术题与高深的数字题,恐怕只有勤学的学子与专门的专家才会有兴趣,但诗词曲中的另类算术则是诗意的算术,在诗人的灵心巧思之中,平日枯燥的数字有如鲜花含苞而放。同是徐再思,他的上述《春情》本来就已经十分精彩了,但比较他的另一首?眼双调·清江引?演《相思》,则不免显得有些平铺直叙,像一道没有多少曲折的流水,在构思的巧妙上还略逊一筹:
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想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面时才算得。
他将相思比为负债,既沉重又高压,这种将无形之愁化为具形的债务的比喻,是创造性的,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用过。而“一”与“三”的数词与量词“担”以及“分”的综合运用,更设想新奇地表现了抒情女主人公相思的殷切与痛苦,而结尾的与恋人相见时算清本息的超前预想,更是将相思揭示得刻骨铭心,有过恋爱经历和相思经验的读者,读来当会更加感同身受,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说有人编纂了一册《中国历代诗词数字佳句集锦》,在层见叠出的有关诗词的书籍中,可谓独具一格,可惜我至今无缘一读,不知其中的“诗词”中是否包括了“曲”和曲中的“元曲”?其实,用数字而使全篇生色的,岂止是古典诗词而已,在新诗中也屡见不鲜,如郭小川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望星空》,其中就有“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的妙句,而在他的《祝酒歌》中,也有“三杯酒,三杯欢喜泪;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且饮酒,莫停杯!七杯酒,豪情与大雪齐飞,十杯酒,红心和朝日同辉”的豪语。叶文福歌颂建设青藏铁路的宏伟而悲壮的工程,写有令人荡气回肠的组诗《向拉萨》,铁道兵七师在修建青藏铁路的第一期工程中,牺牲了一百零八位指战员,诗人在《唐古拉》一诗中写道:“二十多年前/为把铁路修到拉萨/一百零八个战友/倒在了你的脚下/一百零八条枕木/扛着铁路——向拉萨/一百零八行诗/在讴歌这壮丽的图画/每一条枕木都在喊——向拉萨/每一颗石子都在喊——向拉萨/每一条钢轨都在喊——向拉萨/每一块路碑都在喊——向拉萨!”豪情如火,浩气如虹,从这些数字中,你难道看不到火焰的燃烧,彩虹的绚丽和江潮的澎湃吗?
数字如果与诗结成美好的姻缘,婉约的诗就好像待嫁的少女,豪放的诗就有如凯旋的壮士,而诗化的数字就是那缤纷的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