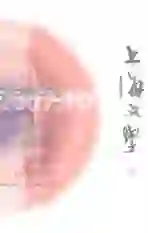尝鼎一脔
2007-12-29刘绪源
上海文学 2007年10期
胡适的白话文风,那种极度的平白、明晰、清浅,外加耐心、亲切,而又充满叙说的兴趣——亦即带有近世西方儿童文学叙述特征的风格,几乎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文章的共同特点——除却仍坚持用文言写作者,以及文字个性特别强的那几家外。更长期地看,这种文风一直延续至今,恐怕,只要还有中文白话,这种风格就不会绝迹。
且让我们试看几家——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
这是五四时期著名学生刊物《新潮》第一期第一篇傅斯年的文章《人生问题发端》中的话,写于1918年11月13日。从文风上看,也是平白而有孩子气的趣味,只是作者年纪更轻,更容易喜欢那种排比的句式,同一期上罗家伦的文章也有这一特点。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
这是著名的《语丝》周刊的《发刊辞》,刊出日期是1924年11月17日。虽然胡适也为《语丝》写过稿,起草《发刊辞》的事则是不会请他做的。然而,如果有谁断言这是胡适的手笔,光从文字上看,却也很难否定。事实上,自胡适独创了那一清如水的文风后,当时许多教授一下笔,常常是这样的口气(至于它的真实的作者,我们放到下回揭晓)。
我生平有一种坏脾气,每到市场去闲逛,见一样就想买一样,无论是怎样无用的破铜破铁,只要我一时高兴它,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钱。我做学问也是如此。……我已经整整做过三十年的学生,这三十年的光阴都是这样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地过去了。
这是朱光潜1934年为《文学》月刊“我与文学”征文所写的《一个失败者的警告》的开头。再看一位也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潘光旦的文字:
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国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国以往的文物起来,也许要到外国去才行。现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国去不可;将来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国去不可。现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经很可怜,将来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怜咧!
这是他写于1930年的《中国人与国故学》一文的开头。如果说,朱光潜、潘光旦,以及傅斯年、罗家伦,加上朱自清、顾颉刚、贺麟、罗尔纲、邓广铭,再加上辈分更低的费孝通、季羡林等等,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辈的人物(有的干脆就是他的学生),文风上有所传承,这都不难理解;那么,再来看两位资历比胡适老得多的古文大家,他们一旦写起白话来,会是什么模样:
对于新诗,讲起来很是惭愧,因为我的资格比旧诗更浅了。胡适之的《尝试集》出版,我没有感到兴趣,因为这时候,我还是反对新文学的。现在的新诗坛,据我儿子无忌的朋友罗念生讲,可分为郭沫若徐志摩和闻一多三大派;他说郭诗是一条疯狗,徐诗是一个野鸡,闻诗是一匹猫。不过,我是宁愿赞同疯狗的……
这段文字的作者,是前清秀才、曾为南社社长的诗坛名耆柳亚子。这是他1933年6月为《创作的经验》一书而写的《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他所用的正是胡适似的“平淡的谈话”,而且,“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胡适语)。再来看一位大国学家马叙伦的文章:
我自己觉得我的过去,可以自信的还在做人,总算十不离九,此外算读书还勤的;可是,学问的成就也微细得可怜。本想时事太平,有补读十年书的福气,再得成就多些;不想胜利到来,偏又把我驱上民主运动的队伍里,一忽儿快两年了,一本书也不能从头到尾看它一遍……
这是写于1947年5月的《〈我在六十岁以前〉校后记》中的话。柳亚子的信口而谈,马先生身为南方人而尽可能“儿化”的努力(“一忽儿快两年了”),他们那从容平白的语态,都暗示着,他们其实都在追随(尽管多半是无意的)胡氏文章的风范。
再来看看胡适的对手。在哲学观点上,胡适和冯友兰意见不合,两人都做《中国哲学史》,为老子年代问题曾起过论战,对立了几十年。然而,在白话文章上,冯友兰却不可能不受胡适这位“开山祖”的影响。我们且看他晚年《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的一段话:
西方有一句话说,哲学家不同于哲学教授。哲学教授是从文字上了解哲学概念,哲学家不同,他对于哲学概念,并不是只作文字上的了解,而是作更深入的理解,并把这样的理解融合于他的生活中。这在中国传统的话中,叫做“身体力行”。例如,对于“大全”这个概念,如果仅作文字上的了解,那是很容易的,查字典,看参考书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要身体力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多么清浅明白,不慌不忙,而又是十足自信的,并隐含一种内在的兴趣。这是在述说很深的理论问题,读着仍叫人愉快,奥秘就在作者的从容与兴趣上。现在因这样的文章读得多了,我们一般不会再追根寻源,就像吃惯了米饭不会觉得希奇,但如没有最初的草创者,没有当年胡氏文风的几乎无所不在的大普及,今天的中国文章很可能不是这种形态。
我们再来看冯友兰一段早年文章,取自“贞元六书”中的《新事论·评艺文》:
对于有些事物,所谓各民族间底不同,是程度上底不同,而不是花样上底不同。例如就交通工具说,一个民族用牛车,一个民族用火车;就战争工具说,一个民族用弓箭,一个民族用枪炮;此是程度上底不同。交通工具的主要性质是能载重致远,而且快,愈能载重致远且快者,愈是好底,即程度愈高底交通工具。战争工具的重要性质是要能杀敌。愈能杀敌,即愈是好底、愈是程度高底战争工具。……但自房子之为房子的观点看,则希腊式底建筑与中国式底建筑之差别,则是花样上底差别。
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举例和阐释(我们已略去了一些),是为要说明,各民族之间“程度”上的差异是需跟进的,不然“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而“花样”(文化)上的差异却可以“各守其旧”,不然“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他的论说的从容和耐心,于此可见一斑。最奇的是,他竟拈出“花样”二字,以这最普通的俗词作关键词,以说明复杂的文化理论问题,其表达力却是惊人的。当然,文中“的”“底”的用法,以及少量文言虚词引入口语,使它与胡适的文体有一点表面的距离;但恰是“花样”二字,透露了胡氏“谈话风”的精魂。
胡适当然还有更严峻的对手,那就是左翼文人。可偏偏是两种人,学他的文章最为努力,其一是他的学生辈,后来多成为大学教授的;其二就是左翼文人中的佼佼者。
我们先来看一位大理论家、《枣下论丛》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批胡适的主力之一——胡绳先生的文章。这里且摘抄两段,都写于1940年春天:
我看林则徐到底还是民族英雄,他主张战就主张到底,并没有叫饶,而且他在战争中的经验使他知道必须自己力求进步。蒋先生(廷黻)要我们不要崇拜前一个林则徐,而要崇拜后一个林则徐,这也可以说是对的。……
中国古来对数字实在是太少关心了,从古籍中就难找到什么可靠的数字,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人增加了极大的不便。比如言土地的兼并,则“富者连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一类话虽也供给一个大致的概念,然而没有更精确的数的表现,也就使得这概念不能成为十分明晰与具体。
前一篇题为《林则徐》,后一篇为《关于数字》,均收入作者《夜读散记》一书。前一篇的语气更有胡适式的“简单味”,而后一篇连观点也与胡适相近,试将胡适“文学革命”前后的论述找来对读,颇能发现行文节奏上的相通处。作者直至晚年所写的史学论著,始终未改这一文风。
当然,左翼文人中,有些本来就是胡适的学生,最典型的就是吴晗。吴晗不仅学业上得益于胡适,文风上也学得惟妙惟肖,虽然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胡适则一直对他寄予厚望。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朱元璋传》传到台湾,胡适看了兴奋不已,到处向人推荐(当时令胡适兴奋的另一部大陆学术作品是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试读《朱元璋传》及吴晗的一切杂论、史著,都可看出那种娓娓而谈、从容澹定、平白到可让儿童阅读的风格来。中国的史书本来是很艰深的,而现代的白话的史著却一反此态,大抵“一清如水”,这不能不归之于胡适的开风气之功。当时还有一位与吴晗一样出名的“进步教授”林汉达,走的也是胡适的学问路数,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出白话《东周列国志》,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此书在五六十年代又经再版,几乎影响一代文风。以后,凡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与寓言故事,行文多是平白、清浅、徐缓、有味的,其实都是仿照林汉达体,而这也就是胡适之体。林汉达后来还有《前后汉故事》,《三国故事》及《上下五千年》(由他的学生续完)等作品问世,至今重印不绝,在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上已臻于化境。
另外,上世纪60年代与吴晗合写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的邓拓(三家中的另一家是廖沫沙),系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多年,他读书兴趣极广,为文喜广征博引,似有知堂散文之趣,但细按文心,却还是胡氏文章风范。我们试着来读一段:
如果学习欧阳修的办法,我以为大家很容易都可以写文章。因为欧阳修的“三上”,除了马上只适合于骑马的人以外,其余二上(按指枕上、厕上)人人都能用,而我们即便不能在马上构思,却无妨在路上、车上、船上等空隙中构思。这既能锻炼思维能力,又可以忘掉路途的疲劳,真是一举两得。
这是邓拓的代表作(也是后来的获罪之作)《燕山夜话》第二集中的最末一篇《新的“三上文章”》。读这样的文字,能感到一种静气,不急不缓,不温不火,内在理路明晰,并伴以淡淡的幽默,感觉就像一个含笑的长者在同孩子说话,但决不是“蹲下来说话”,自然而然,落落大方。这样一种美感,正是我们读胡适文章时得到过的。
更能体现左翼文人受胡适文风影响的例子,是哲学家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那种从容、平白、耐心,而又处处注意叙述的趣味,一如与孩子说话般的口吻,都可以上溯到胡适。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愚公移山》的语气,看看对于《列子·汤问》中原文的白话译说,活脱脱就是《尝试集》时期的胡适之体。事实上,毛泽东早年很自觉地学过胡适的文风,也曾得过胡适的称赞。而因为毛泽东文章的影响——中间还经过延安时期的“反对党八股”——致使许多革命者悉心模仿,所以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文风就更普及了(就连写过幽深奇诡的《画梦录》的何其芳,到这时也以类似胡适的文风写作了)。当然有些模仿会因过于刻意而失去内在的灵气,这正如江青写字亦学“毛体”,像则像矣,细看却总是一种赝品模样。而学毛泽东文章的平白、清浅、如对孩童般的多方取喻,最刻意者,莫过于张春桥,他甚至也学了一点毛式立论的大胆放辣,但因生性阴鸷,他一点也学不来毛泽东那种暗藏机锋的滑稽与调侃,于是,他文中的孩童气也就显出了做作与虚假。
为什么革命者和教师最易于接受胡适的文风呢?这就要说到“谈话风”散文的一个本质的特征了。谈话,总是有对象的,可以说,“谈话风”的各个流派,各种风格,归根结底,都取决于这谈话针对什么对象。而胡适的风格,很明显,是面对最广义的学生的,他要清清浅浅地把事情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正如他在《四十自述》中所说:“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革命者要普及自己的理论,要发动群众,这就不能不浅显,不能不耐心,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最好的例证,而它当年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毛泽东常爱称自己是“teacher”,这也可说明他与胡适在文章上的相通相契。而鲁迅、周作人在文字风格或曰“谈话对象”上,与胡适就有明显的不同,这我们以后将会详论。
然而,每一种文字风格,落到不同的作者身上,总会有渐变,有微调,所以细加分析,还是不会相同的,所谓“墨分五色”,正同此理。天长日久,由“渐”入“顿”,积微成巨,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毛泽东尽管学胡适,但早年文章,由于血气方刚,也由于更早的时候曾受康、梁影响,所以不免常有排比的句式,有“新民体”的痕迹,并时有慷慨激昂振臂一呼的姿势,这在胡适的文章中是不大看得到的。毛的中后期的文章,则又肆意调侃,了无顾忌,天马行空,涉笔成趣,比之于胡适的谨慎的学者风,自然又有很大不同。所以说,胡适的文风渐渐成为许多白话文章的底色,在这底色上,不同的作者会画出不同的图画,但笼统地说,他们仍是一家,那就在于他们的平白、清浅、耐心、有趣上。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老舍为例。老舍行文,一味幽默打趣,年轻时更是如此,这和胡适当然很不同。虽然胡适也说“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但那是清清淡淡、含而不露的滑稽,与老舍在文中不时插入相声式的玩笑口吻,有明显的区别。但老舍文章的底子,还是清浅的口语,所以,一旦他不开玩笑了,好好地说事了,马上就能看出胡氏文章的底色来。他有关《小坡的生日》的自述,坦陈自己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试读《小坡的生日》的第一章,那和胡适的文风,的确是相当接近的。
我们甚至还可以钱钟书为例。当钱钟书以文言写作时(例如《管锥篇》),他在“谈话对象”上更接近于周作人;然而,他的白话文章,尤其是胡适所说的“长篇议论文”,却分明也有胡氏文章的底色。比如:
这个道理,前人早懂得。狄德罗说,诗歌里可以写一个人给爱神射中了一箭,图画里只能画爱神向他张弓瞄准,因为诗歌所谓中了爱神的箭是个譬喻,若照样画出,画中人看来就像肉身受重伤了。我在不是讲艺术的书里,意外地碰上相同的议论。倪元璐《倪文贞公文集》卷七……(下略)
这是《旧文四篇》里《读〈拉奥孔〉》一文中的话。由于钱钟书的文章常有很密集的创见和引文,又时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妙喻或反话,有的读者就记住了这些特征,却忘了阐说他的那些创见,连缀那大量妙喻或引文的,其实还是十分平白、清浅的口语。他甚至不爱用专业的术语,而宁可用“我在不是讲艺术的书里”这种近乎儿语而十分准确的句式。他译述狄德罗的话,也颇有胡适之式的白话趣味。从这里就不难看出他的文章的底子了。事实上,在杨绛的文章里,这样的底子就更明显了。
那么多专家、教授、学者,那么多大文化人,写文章都有意无意地学胡适之体,而这样的文体居然还有西方儿童文学的趣味(参见上一篇《一清如水》),这样说,会不会让专家们脸面无光?我以为,决不会!这非但不丢脸,还实在是五四以后中国文章的一种光荣。正因为有胡适的开风气之先,能把白话文章写得一清如水,大家就都往这一方面努力,一定要写得清晰易懂,一定要保持最好的耐心,而且一定要有趣有味,这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办得到!由此形成的新传统,是中国文章史上的奇迹,也可说是文章史的辉煌一页。在那几十年里,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人大多能写一手清浅有味的好文,他们不卖弄才学却竭尽全力让学问传播开去,他们总能使自己的文字达到极清浅而极深刻。所以,那一代学问家的文章,大多可以当作上乘的散文来读——他们的论文就是广义的美文。我不知道,除了五四后的中国,还有哪一国的教授们(我不是指哪个个别的教授)能做到这一点。
此刻,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内文坛正为《读书》杂志的文风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对近十年来的《读书》,黄裳、舒芜、范用、朱正、何兆武、沈昌文、陈四益等,都提出了批评。此前,我还曾亲耳听到过柯灵、冯亦代等老先生的相似的批评。虽然我至今认为《读书》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杂志,这一地位并未因文风而动摇,但我对它后来的文风演变,也是颇为不满的。本来,这本杂志创刊之初,一是领思想界风气之先,二是以其美文著称。但十年前,自从换了年轻的主编后,选题上逐渐加重了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探讨,文章上专业论文的成分日益加重,专业术语多起来了,叫嚷“看不懂”的读者也多起来了。而趣味性、文人气,被编者看成是与学术性不易相容的东西,被逐步淘汰,老一辈文化人的隽永的美文也明显减少了。面对批评,辩之者称,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和世界性的问题推到面前,它们不同于那些文艺问题,它们本来就是迫切的、艰深的,怎能要求他们再像过去那样去做好看的文章?
于是,我想到了五四以后的那几代学人和他们的文章论著,他们又何尝不是面对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种种迫切的难题?他们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大量艰深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现在随手即可举出的,就有:胡适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吕澂关于印度与中国佛学源流的梳理,赵紫宸的基督教研究,任鸿隽的科学史研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古建筑学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理论,顾颉刚、江绍原与钟敬文的民俗学,费孝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贾祖璋的生物学,陈原的地理学,自赵元任到周有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知堂以至舒芜的妇女问题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问题研究,马寅初的经济学与人口理论……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这都不局限于文学艺术,但这些作者无一不有“文人气”,他们的文章也无一不具真性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自如地运用“谈话风”,把学术文章写得“一清如水”——事实上,他们都是“文章家”,他们的文章都能当作散文读。
这样看来,新一代的不少学人,之所以不能写出像前辈那样的美文,主要还是未能充分认识五四以后中国文章优美可贵的新传统。他们多为留洋的博士(其实老一辈学人中也不乏西方名校博士),他们所学的是国外学院派论文的论证方式,但他们“入乎其内”,却未能像第一代学人那样“出乎其外”。在面对中国大众,面对像《读书》那样的非专业的杂志时,如果还只习惯于以课堂讨论、论文作业的方式说话,那就不能不留下遗憾。
至此,我们就更能体会胡适那“一清如水”的文风的可贵了。
附记:
本文介绍了与胡氏文章相近相关的各家文体,也引用了他们的文章片断。这样做有个危险,就是从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的书里,也有可能挑出几句你所需要的文字来。所以,我时时警诫自己:一定要在大体把握了这位作家的风格之后,再去寻找较有代表性的引文。作为文题的“尝鼎一脔”,与成为笑柄的“瞎子摸象”,其实是颇有相近之处的,即都想取其一点而略知全局。我所做到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但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都来探究文体和文心——这与任何艰深或迫切的研究都不相矛盾——有了这样的关心和探究,中国文章的优美的新传统,才不致在我们手里黯然消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