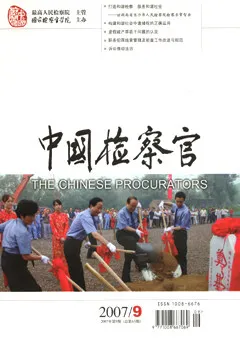遏制刑讯逼供 张扬保障人权
2007-12-29刘建华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7年9期
内容摘要:目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仍存在,对此应在追求实体正义的同时,注重程序的正当性。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提高人类文明和人类之福祉。
关键词:刑讯逼供 沉默权 无罪推定 保障人权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迫其供认犯罪事实的非人道行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联合国早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对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是对刑讯逼供的具体规定,其内容和涵义十分丰富,具体言之:
一、刑讯逼供现象呼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与量刑的根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规定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的证据规则。诉讼当事人要保护自己的实体性权益就必须用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的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证据在程序方面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证据规则的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合理的举证规则和质证规则来保障当事人能够行使收集证据、使用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在美国的《证据法》中“毒树之果”原则是在1920年的西尔夫索恩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的。在该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当被用来获取其它证据,因为最初非法获取的证据已经腐蚀、污染了所有随后获取的其它证据。此原则要求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不能使用,就是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进一步取得的证据也作为“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在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是由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规定。因为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保障,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得到明确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同时应完善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加强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1]
二、刑讯逼供现象有违无罪推定的理念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刑讯逼供也是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它与无罪推定的理念格格不入。通说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即在判决前的侦查、审判阶段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而在法院最后判决阶段如果控方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罪则应判其无罪。具体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但这条规定与国外的无罪推定还有不同。
其内容包括:疑罪从无规则、控方举证规则和建立沉默权规则等。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人类文明和民主的重要标志。沉默权规则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紧密相连的,具体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沉默权,面对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讯问,有不说话的权利。从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沉默权最早渊源于英国,无庸质疑,沉默权是一项重要的自然权利和人权的重要体现。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法律、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中存在很多不足,如刑讯逼供未能杜绝,口供为证据之王的观念依然得不到根除。无罪推定的理念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必须确立,具体说来: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违无罪推定的理念,因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而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有关犯罪事实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无权保持沉默,应该在中国特有的法MQXurd7dqo1jL4sbThQyt6mcVS4DHSZf7d9w6Wg44q0=治语境下渐进的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确立类似“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s)的警告制度。确立无罪推定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和顺应国际民主化潮流发展的需要。以适应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领域国际化潮流的需要。
第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中,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适用和其宪法地位。因为无罪推定原则不仅是刑事诉讼法原则和刑法原则,更是宪法原则。
第三、侦查活动中,要善于利用高科技等先进工具,同时政府应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一方面要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刑讯逼供的处罚力度,切实杜绝刑讯逼供。
第四、“命案必破”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造成刑讯逼供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司法必须独立与新闻媒体和行政权。
第五、加大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的参与度和事先监督权和事后监督权,严厉惩罚刑讯逼供,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刑讯逼供现象有违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诉讼价值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维护人的尊严与自尊,从而促进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揭示了刑事诉讼的内涵,反映了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文明社会所追求和张扬的。具体说来,刑事诉讼中,要确立无罪推定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确立沉默权制度,杜绝超期羁押现象、保障人权,重视程序正义等都是刑事诉讼价值的生动体现,任何侵犯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都有驳与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也有驳与人类文明理念和违反人权的。
四、刑讯逼供现象有违“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追诉、审判与惩罚犯罪,用以行使刑罚权的程序。因此在整个程序中必须符合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力制衡原理,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所谓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指整个刑事程序必须依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规范,而且所有的法定程序内容必须公平而正当合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首先要求所有的刑事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性原则,侦查、起诉、审判必须依法,依法定程序进行。程序正义体现了公民个体被尊重的程度及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
程序正义的观念源于英国,那里的人们称程序正义为“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自然正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1、任何人不得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从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解读出控审分离、控辩对抗和审判中立的理念。
在美国,罗尔斯认为程序正义可分为纯粹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程序正义三种。因此,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其实就是罗尔斯所谓的完全的程序正义,即有实体公正的标准,又有实现这个实体公正的程序。而控审分离、控辩对抗和审判中立,其本身就是程序正义的题中之义。
而我国法学家也认为:现代刑事诉讼不仅追求实体正义,而且注重程序自身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程序正义是指诉讼的过程应具有程序正义理念所要求的品质,追求的是过程价值。它体现于诉讼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价诉讼程序自身正义性的价值目标。评价诉讼是否具有程序正义价值的标准,是其能否保障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应有的待遇。[2]
因此,法定的追诉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并且具有独立价值,程序本身具有内在优秀品质的价值,实体正义不能独立于程序正义而存在。法律程序有其功利性和工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