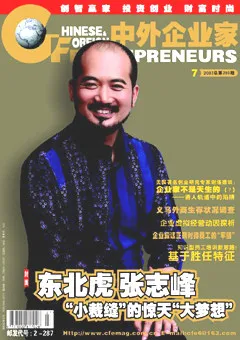企业竞争的制高点:战略弹性
2007-12-29张贵友
中外企业家 2007年7期
一、战略弹性的主要内容
企业面临经营环境的快速变化,促使其必须具有快速的经营反应能力。而要获得这个反应能力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弹性。战略弹性是企业依据自身的知识能力,为应付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情况而具有的应变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由人员、程序、产品和综合的系统所构成。战略弹性来源于企业本身独特的知识能力,而企业人员知识本身的构成和其组合方式是构成战略弹性的关键。
战略弹性由资源弹性、能力弹性、结构弹性、文化弹性、技术弹性和生产弹性所组成。资源弹性是指企业现有资源的灵活性、闲置资源的可利用性和潜在资源的可创造与积累性。能力弹性是整合资源以完成特定任务的适应性,它不仅涉及资源的支撑,而且也触及企业的学习、探索、创新及调整的力量。结构弹性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对环境变化和组织内部情况改变的延展性,由于结构决定了企业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模式,所以结构弹性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中具有框架性作用。文化弹性是企业文化对各种致变诱因发生变化时的重塑性,它影响闲置资源的利用和潜在资源的创造和积蓄。技术弹性是技术创新机制面对致变诱因发生变化时的适应性,它对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技术水平和资源的利用程度基本匹配时,技术水平越高,资源的利用程度就越深。生产弹性是企业的生产系统在致变诱因发生变化时的灵活性,包括机械、产出、协调、人力资源、产品市场等维度,它是公司战略实施的依托。企业战略弹性的强度即取决于此六种弹性的各自强度。
二、战略弹性的实质
战略弹性的实质是通过战略管理机制整合企业内部情况或外部环境变化的新知识。由于整合知识既需要企业基础知识的支持,也需要对企业内外部新知识的处理,所以可以认为战略弹性是一个有机的企业知识系统。一方面,有效弹性的形成需要支持性学习系统的开发,尤其是信息收集功能和信息处理功能的开发,这有助于企业洞察与挖掘环境机会,确定变革时机和明确所需的各种企业能力;另一方面,战略弹性和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即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基于原有知识基础对新知识的获取(产生)、存储、传递、共享、应用、更新的能力。企业战略学习机制的活性程度决定战略弹性的强度,而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是战略学习机制活性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从根本上说,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决定了战略弹性的强度。
三、战略弹性的作用机理
在了解战略弹性作用机理之前,我们要清楚企业战略管理机制的含义。企业战略管理机制是指企业如何制定、实施和变革战略。战略弹性的作用机理体现在企业战略认知、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三个阶段对代表企业战略变革诱因的新知识的整合。在不同的阶段,企业战略弹性有不同的主导性整合元。在企业战略认知阶段,能力弹性是主导性整合元,主要包括鉴别、分析和预测动态性的环境机会与环境威胁、企业优势与企业劣势、洞察和判断竞争规则的变化、评价战略创意的重要性的能力。在企业战略制定阶段,结构弹性、文化弹性和技术弹性是主导性整合元,因为这三种弹性主要以战略形成的方式综合性地整合新知识。同时,这三种弹性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知识创新而具有内在一致性。在企业战略实施阶段,资源弹性和生产弹性是主导性整合元,它们根据新知识对生产的要求,改变资源配置和利用模式。
四、提高战略弹性的主要措施
一旦企业建立起自己的战略弹性,企业便形成了组织的活性化、功能的综合化、活动的灵活化,也就是构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也就从而建立起别人无法复制的战略优势,竞争能力将会得到很大提高。因此,战略弹性成为企业竞争的制高点。为提高战略弹性,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创造和积累知识性资源以增强资源弹性。知识性资源不仅是企业资源中最具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且是弹性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知识性资源的创造与积累有利于现有战略与将来战略的替换。
各层级管理者要及时学习新知识,增加知识容量,更新知识结构和提高知识转换能力,据此增强能力弹性。同时,高层管理者要增强基于企业家知识的战略企业家能力。
构造有机的企业组织结构以增强结构弹性。减少管理层级,增加管理幅度,促进金字塔型的垂直官僚式组织向扁平型的水平网络式组织转型。
建设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以增强文化弹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成员的一种知识共享体系,具有自觉的调节群体行为的内源性作用。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培育鼓励尝试、容忍失败的氛围,而且确立了在创新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价值观。
做好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使技术和公司战略高度整合,据此增强技术弹性。选择市场主导型的技术创新路径,保持创新的主动性,着重抓好市场进入时机,把握好产品与市场定位,培养技术能力并使之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密切结合。
提高制造系统、服务系统和协作系统的各自弹性和相互间的协调程度以增强生产弹性。
本文受到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2006jqw086)和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6SK15)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安徽农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