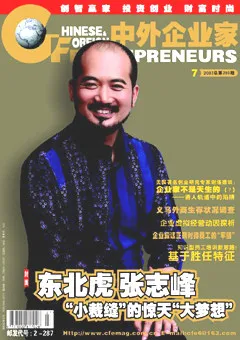社区矫正:罪犯处遇新趋势
2007-12-29廖培坚魏玉铭邹郁卓
中外企业家 2007年7期
一、社区矫正产生的背景及其含义
世界刑罚史是以肉刑和生命刑为主导转向以监禁刑主导,然后发展到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过渡的历史。它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非人道到人道的折射。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主要形式是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顾名思义,就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即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矫正。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中的所有犯罪矫正措施。我国的社区矫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将其定义为: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个定义是经过研究人员与国家有关机关工作人员认真研究之后提出的,应该说是一个表述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全面,并且考虑了国际社会的做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定义,比较恰当地体现了社区矫正措施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
二、社区矫正是中国刑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社区矫正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思想,符合国际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
刑法的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它是指刑法的适用必须慎重、谦虚,包括刑法的补充性,即刑法只能是保护法律的最后手段;刑法的不完整性,即刑法不能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刑法的宽容性,即如果行为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就不能处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刑法理论的进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刑罚尤其是监禁刑固有之弊病,对刑罚的启动持更为审慎的立场,将其作为保护法律的最后手段和补充性措施,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其他手段来代替刑罚。社区矫正就是其中有效的手段之一。与此同时,在人权问题日益彰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日趋严重的犯罪及监狱严重负荷的形势,非监禁刑在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加重,刑事制裁逐步向非监禁刑过渡。刑事执行和罪犯处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行刑社会化成为国际司法的潮流。正如联合国在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所倡导的“我们应当寻求在‘狱外’或‘不用监狱’来改造罪犯的方法”。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推行了行刑社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也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先进的司法理念和文明制度之外。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进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二)社区矫正避免了监禁刑的弊端,适应了恢复性司法的需要
近代以来,监禁刑成为刑罚体系之核心,具体做法是将犯人关进监狱,剥夺其再犯能力,以防卫社会,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但监禁刑也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标签理论认为,贴标签是违法犯罪的催化剂。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过程,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合理化”而演变为行为人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将罪犯判刑入狱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这种对罪犯心理上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带着罪犯的深刻烙印回到社会,作为人所需要的自尊及社会归属感将难以得到满足,这就有可能增强其反社会的心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另外,在一个集中了犯罪人环境的设施内,罪犯的交叉感染不可避免,这将大大耗散罪犯改造的效应,增加新的犯罪源。社区矫正却恰恰消化了罪犯的标签色彩,并能有效地防止犯人的交叉感染,具有监禁刑所无法替代的优点。同时,社区矫正也是发展受害人、社区、刑事司法系统与罪犯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的需要,适应了恢复性司法的需要。
(三)社区矫正能降低行刑成本,提高刑罚效益
行刑是一个社会资源损耗的活动,国家刑罚机器的运转需有相当的资源做后盾。本着保护人权的需要及保证监狱的正常活动,国家不得不在监狱的建设、设施的改善等方面投入巨额的花费,社会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行刑经济化,讲求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的最大社会效益。这一观念与社区矫正有密切联系,尤其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法学领域以后,经济分析法学成为当今法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经济分析学派代表人物波斯纳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精辟地论述了监禁刑的不足之处,认为“在用其他可选择的惩罚替代徒刑的作用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 。行刑的经济化成为当今社区矫正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是监狱普遍超载,人满为患,而犯罪率又居高不下,监狱行刑能力有限,而国家财力又不允许大幅度投入。在这种现实的压力下,寻找其他方式惩罚和矫正犯罪是必然的方向。以社区矫正代替监禁,能够减轻监狱压力,节省开支,这样既保持了定罪量刑的严格标准,在客观上又减少了入狱人数,降低了监禁刑的副作用,有利于将罪犯早日改造成功,重返社会,这样既体现了行刑经济原则,还体现了刑罚效益,节约了矫正资源。
(四)社区矫正有助于罪犯回归社会,塑造罪犯的社会化品格
传统的监禁刑将犯人与正常社会隔绝开来,人的社会化将被杜绝或者被大打折扣。作为社会人而言,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将罪犯置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群体之中乃是促进其社会化的最根本的途径。20世纪60 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思潮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对国家和社会提出了崭新的要求,要求社会必须承担使罪犯重新返回社会的义务,而非排斥于社会之外,国家应该尽力协助个人潜能之发挥,提高个人生活之素质,包括应加强对罪犯在内的缺陷者的辅助,使之能“再整合”到社区中。社区矫正着眼于罪犯的回归社会,让罪犯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发展与自由社会的联系,罪犯不脱离家庭共同生活,参加工作,参与社会生活,在这种常态的环境下,罪犯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同时,社区矫正运用的指导、援助的方法能使罪犯感到社会的温暖,有助于提高罪犯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培养社会化的品格。
三、我国完善社区矫正的对策
(一)更新观念,培养民众特别是司法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意识
制度改革有赖于观念的更新。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关于社区矫正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使社区居民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一制度,能积极主动配合完成这项工作。司法机关必须根除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的思想,“在重刑主义的氛围下,只有徒刑才是刑罚。” 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文明的刑罚理念,培育社区矫正健康发展的土壤是我们提高社区矫正适用的根本,否则社区公众与执法部门对此抱怀疑态度,要提高社区适用只能是奢望。
(二)提高社区矫正的适用率,限制监禁刑的适用
我国现今刑罚适用的模式仍是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可谓可怜,我国90%的已决犯是被关押在监狱内的。而目前西方国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刑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模式,社区矫正在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与监禁刑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仅在适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监禁率,且还有取而代之之势。与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高适用对照,我国明显偏低,应该扩大其适用范围。与此同时,还要限制监禁刑的适用。联合国《减少监禁人数,监外教养办法和罪犯的社会改造》决议指出:“监禁只能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要考虑到犯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以及与法律有关的社会条件和罪犯其他方面的个人情况。原则上不应对轻罪犯实行监禁。”本着这一精神,在刑罚的适用中,能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行为尽量不要用较重的手段调整,监禁刑只用来惩罚严重的犯罪行为,以减少监禁刑的滥用。
(三)完善原有的五种社区矫正制度,增加社区矫正的种类,以便能在不同情况下加以适用
我国目前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和监外执行五种社区矫正都存在一定弊端,必须针对弊端加以完善。同时,相比于外国,我国的社区矫正种类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够适应实际多样化的需要。外国的社区矫正的种类有缓刑、假释、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家中监禁(Home Confinement)、电子监控、赔偿、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因此,我们可以在透彻对外国社区矫正种类进行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比较、借鉴、整合,依法增加社区矫正的种类,以适应司法实践多样化的需要。
(四)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培养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不完善很大程度归因于矫正机构的缺失和矫正队伍的不完善。在国外,多数国家的社区矫正执行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将社区矫正的执行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的做法。同时,由于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强、比较复杂和具有挑战的工作,西方国家对矫正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工作经验都有一定要求,必须由专业人员担任矫正的工作者。鉴于此,我国可以在我国司法行政机构内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每个街道,每个社区再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负责缓刑、假释、社区服务等监外执行的犯人的教育管理工作,并开展帮教工作,依靠社区力量,着力对社区范围内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治。同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人员队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是至关重要的。社区矫正工作者要体现出专业化的分工,需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学习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刑事执法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充实这一专业队伍,建立培养和吸纳专业人士的机制,以期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厦门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