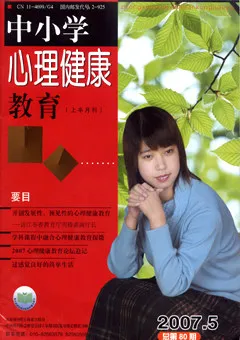2007心理健康教育论坛追记
2007-12-29钟志农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07年5期

2007年3月24日~26日举行的“2007心理健康教育论坛——台湾心理辅导技巧展示与工作坊”落下了帷幕。这次我赴京参会,感想多多,追记数语,写成随笔,愿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向教育部领导代表面陈三点意见
3月24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刚一结束,出席会议的教育部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海东先生就立即和各省、地市心理健康教育负责人进行座谈,我也应邀出席。在周红五老师第一个发言之后,我向陈主任面陈了三点意见:
我认为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解决三个“地位”问题:
第一,辅导教师的地位问题。许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满腔热情而来,心灰意冷而去,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角色、地位、贡献均处于模糊状态,名不正言不顺,干得不明不白、窝窝囊囊。从身份上说是心理辅导教师,但是没有这个编制,一所两千人的中学,应该配几个在编心理辅导教师也没个说法;“持证上岗”,持的不是国家统一的“学校心理辅导教师证书”,而是杂七杂八的“地方粮票”,难怪许多老师纷纷去考“心理咨询师”的“国家粮票”,但“心理咨询师”和“学校心理辅导教师”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职称系列,一个高级教师拿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您说他是高级职称还是中级职称?角色上,说是专职教师,但却被校领导看作是“工作负担轻”的人而被派去兼做教务员、文秘、档案员甚至文印员等等;地位上,奖金最低,收入最少,晋升职称却不知道归何系列,评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等等荣誉大多无缘;贡献上,心理辅导教师做起工作来真是无底洞,但是有谁看得见、说得清、认得准?一周的工作量应该如何计算?如何考评心理辅导教师的优劣?都是一笔糊涂账。
第二,心理辅导课的课程地位问题。如果承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和预防,那么就应该名正言顺地开设心理辅导课。但是一提到开课,就好像成了“黑五类”,学期课时计划里没有,课程的教学大纲没有,周课时表里也没有。然后就可以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你,比如说“已经列入综合课程里了”。而综合课程是什么?是二十几种教育内容的大拼盘,于是心理健康教育就和“人口教育”、“预防艾滋病”、“禁毒教育”、“安全教育”等等混在了一起,由一位说不清是什么学科的教师去执教,而且还要考试!再比如说,思品课、历史与社会课里面加入了心理健康的内容,于是说“已经列入课程”,不必再另开课了,但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与预防功能是这些课程的功能所能替代的吗?因为课程地位不明,所以,即使有时间,也不会让你去开心理健康活动课。
第三,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在学校里的地位问题。心理辅导工作到底归学校里哪个部门管?现在是谁有兴趣谁管,或者谁的工作量轻谁管。所以有的是教科室管,有的是教务处管,有的是政教处管,有的是校办管。那么,到底应该归谁管?尽管我们做不到像台湾那样在学校设立独立的中层机构“辅导处”,使“辅导处”与“教导处”、“训导处”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但也要有个明确的说法,让此项工作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
以上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不可再拖延,否则会使一项新兴的事业遭遇“倒春寒”。直率一点说,现在是“政策滞后于实践,领导滞后于群众”。无庸置疑,教育部基教(1999)13号文件和基教(2002)14号文件对于当时“打破坚冰、指明航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2002年《纲要》发布以来,五年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急需从宏观上制定相应政策来加以解决。因此,建议教育部尽早出台第三份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对上述问题作出操作性的明确规定。
陈海东主任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并详细作了记录,表示回去一定向领导反映。
我觉得会议主办者能邀请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到会与各地代表座谈,听取基层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是本次论坛重要的收获。但不足的是第一线的教师代表少有参加,否则还会反映出更多的实际问题。
台湾辅导技巧展示与工作坊一瞥
据我观察,这次会议的与会者都是冲着这一主题去北京的,若是单看会议的计划安排表,应该说承办方照顾了每个人对四个工作坊的全面需求,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去参与这四个工作坊,包括:周光昭老师主持的“房树人测验(HTP)的基本理论及应用”、韩正雄老师主持的“情绪管理气象台”、张德聪教授主持的“探索教育:班级辅导活动设计”、吴晓蓓、谢月英老师主持的“个案辅导技巧”等,这无疑满足了大家对台湾心理辅导技巧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我因为第一天下午参加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召开的全国心理辅导优质课联评的筹备会,结果只参加了第二天的两个工作坊,现就这两个工作坊谈一点感受。
第二天下午的前半段时间(约一个半小时)是谢月英、吴晓蓓老师主持的“个案辅导技巧”工作坊。
台北建国中学(高中)的谢月英老师首先做了一个“走进生命的旅程”的个案分析,这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高中生自杀干预案例,我感觉谢老师做得十分专业、十分细致、十分扎实,有理论依据,有操作措施,仅从她采取的10项辅导策略中,便可“窥豹一斑”:
① 努力建立辅导关系(依据“当事人中心”理论);
② 提供好的系统环境(依据“特质情境论”和“系统观”);
③ 提供舞台发挥当事人专长及潜能(依据“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发展螺旋论”);
④ 建构学习及生活目标(依据“发展螺旋论”);
⑤ 同辈辅导,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依据“需要层次理论”);
⑥ 个案相关人员辅导及策略联盟(依据“系统观”);
⑦ 导师(即班主任)家长群的咨询辅导(依据“系统观”);
⑧ 与校长沟通(依据“系统观”);
⑨ 个别咨商(采用积极接纳、尊重、同理、支持、肯定、保证、自我觉察、情绪管理、认知调整、人际技巧、成功经验、叙事治疗、性取向探索与认同等辅导策略);
⑩ 医生咨询与治疗(依据“危机干预”处理策略)。
谢老师的个案介绍使我比较具体地了解了台湾同道的个案辅导模式及专业化水准,颇有收获。但可惜的是,完全没有互动讨论的时间,乃至一些具体问题难以作深入的探究。例如,谢老师自己总结这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没有对象的辅导,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值得珍惜的生命,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她的辅导甚至深入到个案的生活中、茶室里,其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对这类非自愿求助的个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辅导的基本架构而不突破专业界限?再如,台湾社会特别是家长,是如何看待学生的性取向问题的?等等,都没来得及做互动式的研究。虽说当晚有一个半小时“答疑”(后来似乎被“联谊活动”替代了),但“答疑”毕竟不同于“工作坊”。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紧接着是台北市立诚正国民中学(初中)的吴晓蓓老师做个案分享,她被我们与会者誉为“美女辅导教师”,因为还兼做学校的行政工作,所以她的发言经常会带有一些中观层面的思考。她介绍的是一个初中15岁少女未婚先孕的个案,案例相当典型,它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与震撼:
——在台湾的国民中学里,未婚怀孕的学生是不应该劝其退学的,否则当事人可以上诉。这是制度上对保障性失误学生受教育权的支持。
——当动员这个女孩子做人流手术的努力失败之后,学校就开始研究:请总务处考虑调整怀孕学生的课桌椅之间的距离,以便于学生进出座位;请体育老师考虑该生上体育课的安全措施;学校甚至考虑到当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否需要在校内设立临时的哺乳室。
——当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学校辅导室鼓励“小妈妈”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养育好自己的孩子;“小妈妈”不愿意到学校里来上课,于是教师不辞辛苦,到这位15岁的“小妈妈”家里为她补课,包括考场都设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里。
——学校辅导室还协助“小妈妈”做好生涯规划,引导当事人今后如何使自己有能力来负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
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学校“以人为本”的理念,说明“以人为本”并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些措施在大陆地区的可行性如何,我只觉得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是: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我们应该向台湾的同道们学习哪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同样感到可惜的是,“工作坊”并没有开展互动的研讨,我当时想到的一些问题如“台湾的父母对子女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有何变化”、“台湾社会舆论对出现学生未婚先孕的学校是何态度”、“教育行政部门如何评价学校对待当事人的以上做法?”至会议结束时也没有机会向吴老师当面讨教。
下午前半节“工作坊”休息之后,应该是本次论坛的重量级人物张德聪教授上场。我此前并未见过张教授,只是由于近一年来同在海峡两岸合作出版的一套丛书中担任执笔,所以在编辑与作者的文书来往中知道彼此。而我自己因为这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班级团体辅导的研究,因此也就特别期待张教授在带领“探索教育:班级辅导活动设计”的工作坊中能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加之在当日上午的半个小时左右的主题报告中,张德聪教授已经展示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及独特的个人魅力,全场与会者当然对他翘首以待。
下午4点左右,张教授悄悄坐在会场的后面,我一眼看去,便已经察觉他的满脸疲惫。果不其然,在一个小时左右的工作坊中,张老师声音沙哑,发音甚为艰难,在游戏活动的过程中,我想,如果再请他作深度引领的话,那就是太欠体谅之心而欲强人所难了。当晚我才知道,原来前一天下午的工作坊因场地更动,没有扩音设备,张老师的嗓子不得不超负荷运作,所以出了“故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过程,我觉得会议组织单位在内容及日程的安排上应该吸取一些教训:
第一,既然是“工作坊”,就应该按照“工作坊”模式来进行操作。“工作坊”的特点是多操作、少理论。许多一线的教师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就是想多学一点实际的操作技巧;当然,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少的,但在每场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工作坊”中,无论是“讲理论”还是“练操作”,恐怕都只能是“蜻蜓点水”,起不到什么太大的实际效果,这恐怕就是培训班内容设置上的问题了。此外,有的“工作坊”主题基本上以报告形式出现,与大会报告无异,只不过人数比较少而已,这些则是操作上的问题。
第二,根据我自己在参与或者主持“工作坊”时的亲身体会,“工作坊”必须主题单一,目标明确,学员参与实践的时间至少在2~3日左右,方可取得一定的效果。这次活动组织的“工作坊”,若能对每个专题都安排两整天,将4个专题并列“菜单”,由学员自选,而不是让学员到4个专题都去匆匆“转一圈”,是否就可以做得比较从容、比较深入一些,效果就会好一些?当然,如果每个专题的工作坊均进行2天,还需要有劳台湾有关专家作更多的准备。
第三,这次论坛上安排的大会主题报告,精芜并存。有些并无参考价值的报告,占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而有些大家期待很高的报告,却只留给报告人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这令与会者感到几分失望。
广渠门中学听课有感
两天半的论坛,与会者最后的期待自然是想听到一节能代表北京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水准的心理辅导活动课,但是,从现场的感受来看,显然大家觉得失望了。
关于这节初中的心理辅导活动课《我们是朋友》,我不想再说更多的具体意见,因为我在现场的评课中已经说了很多,大大超过了主持人给我预定的10分钟时间。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三点:
1.任何一次大型的心理辅导公开课活动,无论课开得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研讨的现场,有无收获均取决于课后的“研讨”。如果一节课开得非常成功,但是课后的分析讨论不深入,那么就会变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回去之后最多是“照猫画虎”,听课的辅导教师不会有实质性的成长。反之亦然,即使一节公开课上得糟糕至极,但只要能在课后认真评议,分析其失败的真正原因与教训,那就会使听课的教师收益良多。这也同样是开课教师为同行们作出的重要贡献。所以,我一贯主张,评课应该“不论成败,只讲得失”。只有抛却功利心和功利标准,我们才能放平心态,才能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才能不讲套话、假话,只讲实实在在的真话。而辅导教师真正的成长就是从“讲真话”开始的。
2.我认为,这次广渠门中学的刘老师能够在全国性会议上开出这样“原生态”的公开课,恰恰反映了他的“求实”风格,一般的老师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当然,我不是说优质课都是“造假课”,有的老师看到一些上得很好的心理辅导课就心存疑虑,以为是“造假”或者“做秀”,这未免有些形而上学;心理辅导课是完全可以上得相当出色的,我们不能囿于自己的眼界而去怀疑他人的成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确实存在“造假”与“做秀”的所谓的心理辅导“优质课”,那是对我们事业的一种歪曲和玷污,是我们的专业宗旨和专业精神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心理辅导活动课如果“造假”或“做秀”,那就不是“心理辅导”,而是“心理误导”了。
3.心理辅导活动课如果上得不如人意,其主要原因是两个“缺少”,即“缺少经验”和“缺少指导”。“缺少经验”是因为现在有许多中小学舍不得把课时留给班级团体辅导活动,导致担任此项重要责任的辅导教师和班主任缺少“实战经验”;“缺少指导”则是因为大多数中小学的辅导教师和班主任开设心理辅导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各自为战,研讨机制和专业督导系统严重缺损,导致开课教师的专业成长迟缓或滞后。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看到一些不理想的心理辅导活动课,就去怀疑或指责发展性班级团体辅导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不能借口专业化水平不足而去压抑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与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开展积极的师资培训,只要指导、研讨和培训跟上去,相信没有改不好的心理辅导课,也没有上不好心理辅导课的教师。
这次“2007心理健康教育论坛—台湾心理辅导技巧展示与工作坊”内容安排之多,时间安排之紧,与我以往参加过的类似会议、活动相比,是少见的。虽然此次活动存在一些不足,有些许遗憾,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与会人员,若能调整心态,虚心学习,认真比较,积极思考,是可以从两天半的活动中得到收获的。我之所以要整理出这样一篇“随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作者单位:“心海扬帆”中小学心理辅导网站)
编辑/王希永 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