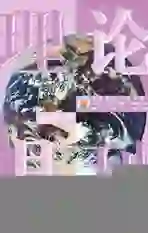对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因素的解析
2007-12-20方莉
方 莉
摘要: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从1978年至2002年虽然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的位置上,但是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参与率呈缓慢下降态势,不过进入到2000年以后,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趋势开始非常显著。劳动力参与率的这种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的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正确把握劳动力市场报酬和我国的贫富状况、“气馁工人效应”和“新增工人效应”、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状况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对于全面解析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 变化;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11-0134-04
劳动力参与率是实际劳动力在潜在劳动力中所在的百分比,它是考察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指标。从1978-2002年,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呈现出的总体特点表现为:其一,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位置上,即劳动力参与率一直高于65%。其二,劳动力参与率呈缓慢下降态势,特别在1978-2000年间,劳动力参与率仅下降了大约8个百分点,2001年后,劳动力才呈现出迅速下降的态势。劳动力参与率之所以呈上述变化,应该说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
一、 我国劳动力市场报酬和我国的贫富状况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图1 1978-2002年我国工资(W)变化与劳动力参与率(LF)的变化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按照Bowen and Finegan(1969)的观点,劳动力参与率与市场报酬是呈正比的,当市场报酬提高时,劳动力如果处于非市场阶段,必然会加大他的机会成本,[1]但是,如果市场报酬一直处于低谷期,劳动者也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从1978-2002年我国的工资虽然增幅不大,但是也是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这一趋势与劳动力参与率呈缓慢下降态势呈一定意义上的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效应不是很显著。原因在于:1992年以前伴随我国的僵化的用工制度的工资体制无法反映市场供需的变化,1993年后,虽然用工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长期积压下来的“泡沫职工”促使工资无法成为市场机制的真正的指示器,从而表现出工资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一定程度的不协调,见图1我国工资变化与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
针对劳动力参与率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借助于另外一个辅助变量来加以说明,即恩格尔系数。长期以来,我国实际的包括工资在内的市场报酬一直处于低位,劳动者为了维护基本的生存可能,必须介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获取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按照国际规定,恩格尔系数≥60%的定位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从1978-199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高于50%,说明我国居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与温饱阶段下,1978年我国的贫困人口达到2.5亿,1985年以人均年收入200元定位贫困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有1.25亿,1989年,经过国家的努力,贫困人口降至3000万,随后,随着物价的波动,1993年,将贫困线划为400元,贫困人口又增至8065万,在这个时期,庞大的低生活条件下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只有跻身于劳动力供给行列,接受着可以满足他们日常最基本生活下,低于劳动者的保留工资的劳动报酬,同时,在生活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会促使低于16岁的人口加入到劳动行列之中,从而也就可以解释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者参与率的高位状态。
农村在2000年后,城镇在1996年后,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逐步进入小康阶段,一部分劳动者由于非劳动收入的增加,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有一部分劳动者,随着整体生活状况的提升,他们也会基于对工作条件与工作待遇的考虑,从而将保留工资加入自己选择工作、接受工作和继续工作的底线,从而改变过去为了基本生存而放弃工作的底线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在乡镇企业就职的劳动者,由于他们的报酬远远低于其他类型企业人员的报酬,就制造业为例,2002年乡镇企业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6927元,只有当年城镇制造业单位员工的平均工资的62%,大型乡镇制造业企业的工人工资稍微高一点,年均工资8899元,但也只是城镇制造业单位员工平均工资的82%。所以,当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仍然低于保留工资时,[2]就会有大量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促使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下降。
二、 我国的“气馁工人效应”和“新增工人效应”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
气馁工人效应和新增工人效应是关于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两者都用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指标作为衡量这两个假说的主要指标,前者假定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呈反向变化,一般说来,在高失业阶段,劳动力参与率会下降3%。而且,劳动力参与率和失业之间关系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持久的。[3]后者假定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呈正向变化。
关于这两种效应的典型代表模型就是Strand and Dernburg(1964)年提出的“气馁工人效应”和“新增工人效应”模型。他们通过对失业率的比例、加入失业保险中泄气工人的比例、劳动力参与率的比例分析,发现气馁工人的效应通过失业率的负系数表现出来,从而证明了当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假定;以及男性17-64岁的工人中存在当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也会提高的新增工人效应。[4]同时,在Strand and Dernburg的模型基础之上,Cain(1966)也发现,当失业率上升时,气馁工人效应影响会超过新增工人效应,于是会出现在两种效应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劳动力参与率也有可能会下降。
从我国的1978-2002年劳动力参与率与城镇失业率的情况来看,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性表现不够明显,虽然从两者回归的结果来看,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197,但是从两者的关系曲线上看,两者之间关联性不够显著,见图2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与城镇失业率的关系。

图2 1978-2002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LF)与城镇失业率(U)的关系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现不明显,特别是在1984-1996年这个时间段,两者之间的变化波动很大,其相关联系度很低,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段给抽取出去,就发现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明显,见图3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分段时期的关系。

图3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LF)与城镇失业率(U)之间分段时期的关系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1978-1983年出现了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的基本正向变化(除去折线部分),高失业率伴随着高劳动力参与率,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1978年底,中央上山下乡的政策调整,导致长期潜伏的城镇就业危机的爆发,[5]失业率攀升到5.3%,另一方面,由于高失业的存在,家庭中的收入的减少,或者是由于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规定的收入标准,家庭其他成员将进入到劳动大军中,补充家庭收入,从而引发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增加的“新增工人效应”。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制度的改革,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失业率水平也就不断降低,劳动者的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所在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参与工作的动力开始下降,另外,我国特殊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在国有部门里,1986年前,企业无法雇佣自己想要的工人,长期的永久性雇佣,导致部分新增劳动者无法参与市场活动,只有转为家庭生产,从而促使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的缓慢下降。[6]
1997-2002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之间大致呈反向变化(同样如果忽略折线部分)。失业率下降伴随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对此的解释可以归为“气馁工人效应”。即一些长期失业者对寻找一份可以接受的工作感到悲观时,会停止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努力,从而促使这些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一部分准备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新人,也会由于对就业机会预期不好,而暂时放弃寻找工作的打算,从而造成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为此,蔡日方、都阳、王美艳(2005)运用横界面数据,证明了在我国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存在越是失业严重地区,劳动参与率就越低的现状。[7]
虽然,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新增工人效应”和“气馁工人效应”影响到劳动力参与率,但是如果把1984-1996年这个时间段也考虑进来,这两种效应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就会弱化,从而很难得到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准确关系。不过这种结论的存在也并非意味着这两种效应所起的作用轻微。因为在我国得到官方关于失业率统计数据仅限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所以,往往显示出较低水平的失业(Solinger,2001),为了弥补统计缺陷,一些学者对失业率重新估算,得出的结论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高的多,如,UNDP(1999)把我国的登记失业、下岗、农民工合并起来,估计1999年我国城镇的失业率为7.9%-8.5%,要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3.1%水平,所以在数据不完善的条件下,“气馁工人效应”与“新增工人效应”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的估计会因此而出现误差。[8]
三、 社会保障程度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稳定社会风险网络的基础,是维护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是劳动者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依赖于时间序列变化,通过研究对劳动力参与率的一些参数变化,来重点分析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冲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大多数据分析显示由社会保障中所获得的利益趋于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促使退休时间提前。例如Moffitt(1987)通过对对数-线性收入函数的分析,得到了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的结论,但是,他同时指出,劳动供给的时机变化会与社会保障的变化不一致。但是,也有对此结论不赞同者,如Aaron(1982)认为社会保障减少了劳动力参与率的证据不足;不过,Plotnick(1981),Myers(1990),Parnes(1988)得到的一致性的结论是老龄工人的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的有一部分应该归结为社会保障。[9]其二,是通过横界面数据研究社会保障对家庭劳动力参与率的冲击。在一定时期,个人由社会保障中获益的变化会促使个人禀赋发生改变,而促使个人禀赋变化不同的要素有可能会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所以,在研究社会保障过程中,横截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为重要。(Pellechio,1979;Gordon and Blinder,1982)在我国,由于横截面数据获取的困难,所以,关于这两者关系的探讨就更多的放在时间序列的分析上。
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体制实施比较晚,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不健全的問题,所以,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可能就有一定限度。

图4 1994-2002年我国职工加入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人数在非农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例(F2)与劳动力参与率(PF)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从1994-1998年,我国职工加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在非农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态势,1994-1995年我国开始全面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后,由于许多企业对养老保险制度认识不足,加上养老基金管理不到位,企业以及职工对加入养老保险的信心得不到增强,从而出现加入养老基金的人数比例下降的态势;同时1993年后我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但是真正加入到失业保险行列的人数并不多,原因在于他们在下岗的同时,也丧失了与企业相依附的一切权力,包括必要的社会保险权力,而且随着下岗人数的增加,相应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比例也会相应下降,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1994-1998年我国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所占比例呈不断下强的趋势。
从总的趋势上看,我国职工加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所占比例变化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出现一定的不一致性,1994-1998年,我国职工加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在非农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成下降态势,说明两者之间变化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一变化可以用替代效应来加以解释,由社会保险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积极参与市场活动,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但是1998年后,我国职工加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所占比例呈缓慢上升态势,劳动力参与率却出现反向变化,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形出现,是由于收入效应的存在,加入社会保险,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劳动收入,从而降低参与市场活动的动力。但是,由于从社会保险中获得收益数据的缺陷,目前无法证实这两种效应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力度到底有多大。
四、 教育状况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
教育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从直接效应上看,教育水平的发展与青少年就业存在极大负相关性,当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高时,青少年接受教育人数增加,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就会减少,劳动力参与率会进一步下降。按照Lisa A.Cameron;J.Malcolm Dowling; Christopher Worswick(2001)年观点,[11]教育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是倒U关系,识字很少或文盲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很高,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很高,而中间教育水平人员的劳动力参与率较低。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这种倒U关系尚未形成,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即两者符合正相关的假定。
在总体水平上,高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参与率(大于62%)要远远高于高中以下学历人员,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的参与率就越高,教育水平越低,劳动参与率越低,文盲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仅有24.98%;从性别上看,男性劳动力参与率(76.07%)要高于女性(59.25%),但是如果从教育水平上看,女性和男性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参加市场活动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明,教育状况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是显著的。
如果从受教育人数出发,可以看出,在我国随着国家、社会、家庭对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家庭中用于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在不断加大,高等学校的在校人数不断攀升,从而促使了不少适龄的劳动者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见图5我国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与劳动力参与率的关系。

图5 1978-2002年我国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WEDU)与劳动力参与率(LF)的关系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在图5中,随着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的上升,劳动力参与率呈缓慢下降态势,两者的变化趋势呈反向关系,特别随着1989年高校扩招之后,高等学校学生人数激增,相应的减少了适龄参与劳动的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促使了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而且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看,系数为-0.19,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
从间接效应上看,通过在教育水平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介入一些变量,来对劳动力参与率实施影响。在这些变量中,讨论最多的变量是收入水平,在一般意义上,劳动力参与率是工资的增函数。相应的,在教育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的间接效应中,教育与劳动力参与率的关系更多体现在正相关关系上。随着教育层次的不斷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从事非市场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应也会增大,于是加入市场活动成为理性选择,劳动力参与率自然会不断攀升。
在对微观家庭行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教育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这种家庭间接效应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家庭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我国一般为妇女,通过教育层次的提高会增加其参与市场活动收入,从而增强其家庭地位,随着妇女在家庭地位的提升,所享受的效用的增加,投入到市场活动的兴趣也就会越来越浓厚,从而促使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如果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一样,教育提高促进了收入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参与市场活动动力。这时教育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表现为工资和工作的边际效用的提升,工作的边际效用提高了,使得为了工资而工作的吸引力更大,劳动力参与率也会不断提升。
五、 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一般而言,一个国家以老年人为人口主要构成部分,则参与市场活动人口必定会因人口的老龄化而减少。反之,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必会上升。Robert Shimer(1999)从实证角度,说明了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对工作年龄结构变化的反应。通过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里,年轻人所占的份额增加1%,年轻工人的失业率减少量会多于1%,老年工人的失业率减少量就会多于2%。反过来,如果老年工人所占比例越高,劳动力参与率就会下降越大。在其他条件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这些结论与劳动力市场规模收益递增是一致的。
根据我国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1953第一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4153.8万人,如果加上尚未调查到的边远地区及部队,实际估算60岁以上人口为4215.4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7%;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25.5万,考虑到1959-1961年的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我国老龄人口在所占人口中为6%;1982年的三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7663.8万,比1964年实际增长81.01%;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9738.3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59%;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900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10.19%,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的改变不仅变革着食物需求结构,也影响到不同经济部门的就业模式,导致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
除了上述因素会影响到劳动力参与率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包括:经济形势、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市场活动生产率、闲暇与工作的偏好以及劳动者个人禀赋等。不过,虽然这些因素或多或少的会对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各自影响的力度不同,而且影响效应也会呈不一致或者呈现矛盾态势,所以,如何真正把握这些因素,也成为制约分析劳动力参与率变化的关键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是由非人口结构转变引起的,那么,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就并非意味着就业压力的减轻,实际上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将更多适龄劳动人口在短期内被挤出劳动力市场,促使“潜在失业”人数比例的上升,而且如果适龄劳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即人力资源将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导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如果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是由人口结构转变主要引起的,那么这就不仅意味着我国比较优势所产生“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意味着由于老龄化所产生的适龄劳动人口的不足,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要经历一个巨大阵痛期,向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转变,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弥补由于老龄化而带来的经济萎缩。所以,正确分析引起劳动力参与率变化的原因对于我国今后经济走向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Richard S. Toikka; Charles C. Hol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Earnings in a Demographic Model of the Labor Marke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76.
[2]Judith Banister.中国制造业工资和劳动者报酬[A],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劳动经济学[C],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Vol.3 No.2..
[3]Stuart O. Schweitzer; Ralph E. Smith,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scouraged Worker Effect[J],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27, No. 2.,Jan.,1974.
[4]Peter S.Barth,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34,No.3,Jan.1968.
[5]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JingHai Zhe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mployment Adjustment in Chinese Enterprises(1986-1990)[J],Economics of Planning 34,2001.
[7]蔡日方,都阳,王美艳著.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蔡日方.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J].中国人口科学,2004.3.
[9]Alan B. Krueger; and J?rn-Steffen Pischke,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Labor Supply: A Cohort Analysis of the Notch Generation[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0, No. 4,Oct.,1992.
责任编辑 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