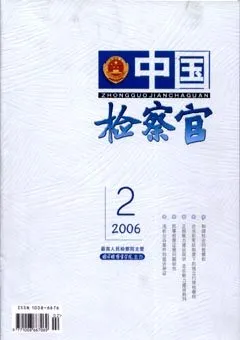国企法定代表人免除国有资产债权应定何罪
2006-12-29陈娅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6年2期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在1998年对某县某镇某片区进行旧城改造。其间,甲公司将其中的一部分非主体工程分包给一国有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2000年该片旧城改造全线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甲乙双方进行了工程款结算,甲公司尚余30万元未支付给乙公司。后甲乙两公司因另几个工程的结算发生纠纷,于2002年初诉至法院。诉讼中,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免除了对甲公司的这笔30万元应收款的债权。不久有群众对丁某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丁某的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从刑法修正案第2条可知,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只有因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才构成犯罪。如果没有发生这一法定危害后果,则不构成犯罪。丁某的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造成了国有资产30万元的损失,但因为其实施的是无权处分的行为,乙公司依然能够向甲公司讨回这笔工程款,故不宜对丁某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由其所在的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丁某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理由是:丁某在该笔工程款被拖欠几年的时间内,不正确履行其催收该款的职责,根据实际情况,丁某是应该且能够履行的,但其不严肃认真对待其收款职责,态度不认真、马虎草率,以至解决问题不及时、不得力,致使30万元工程款无法收回,导致国家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丁某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1999年12月25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丁某身为国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职权,实施了其无权实施的对国有资产的处分行为,造成30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以追究。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首先,丁某的行为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而不是玩忽职守或失职的行为。
修正后的刑法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从立法意图看,是为了解决刑法第397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刑法第93条规定,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根据刑法第168条对这两罪的具体规定来看,两罪在主体和客体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两罪在主观方面不同:失职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多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有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有时行为人还出于徇私舞弊的动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失职的客观行为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而滥用职权只能由作为构成,即不正确行使职权。
本案中,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是该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在国有乙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按职务范围享有处理单位集体公务的职责和权力。丁某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享有对乙公司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之权力,享有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中除处分权外的另三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但是,丁某在行使其职权时,逾越其职权范围,实施了其无权实施的处分这30万元国有资产的权力,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是作出免除该笔国有资产债权的作为方式,因此是一种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
其次,丁某的行为已经导致这笔国有工程款的流失。
从民事法律有关债及债权的理论角度讲,乙公司享有依甲乙双方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所产生的收取相应合同项下的工程款之权利,有依该合同之债权向甲公司为一定的请求,即请求甲公司支付该笔工程款。对甲乙两公司而言,这笔债权要消灭,有清偿、提存、抵消、免除和混同等几种方式。而免除是债权人以债的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是一种单独行为。免除的方式有三项要求:(1)免除人须为免除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2)免除的意思表示应向债务人为之,向任何第三人所为的意思表示对债务人不生效力;(3)免除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不得撤回(即债权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只要符合法定要件即生法律效力,免除人不得撤回)。而免除一旦作出,在民法上将发生:债的关系绝对归于消灭(当债务全部免除时,债权债务关系全部归于消灭)的法律效力。
在本案中,乙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丁某选择了免除的方式去消灭这项合同之债。丁某代表乙公司而为的免除债权之行为已经是一种有效的放弃乙公司合法债权的行为,其行为一经作出,就已经是民事法律行为,即是合法的民事行为。
刑法规定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属结果犯,如果没有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则不构成犯罪。根据上述分析,从民事角度这笔款项已经无法收回,丁某的免除行为已经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虽然可以通过丁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主动去挽回经济损失,但那只是在对丁某具体量刑时予以考虑的因素,并不影响对丁某行为的定罪。
最后,应正确理解刑法第168条规定的“重大损失”数额的界定。
本案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丁某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数额应如何认定?刑法将“重大损失”规定为第168条的构成要件之一,意味着没有达到一定数颠标准的“重大损失”的滥用职权行为不构成犯罪。在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之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6日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项关于滥用职权案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即本罪的“重大损失”数额标准宜界定为20万元。本案的损失额已达到30万元,完全符合刑法第168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本案中丁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作者:重庆市大足县人民检察院研究
室 [4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