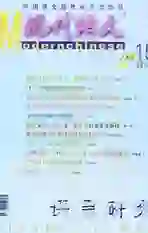《边城》中虎耳草的喻义
2006-07-27田旭东
读了《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3期肖平理先生的《〈边城〉中的虎耳草》一文,有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
肖先生认为“送虎耳草其实应是女孩儿向自己心上人表白爱情的特殊方式。当然,这只是一方一俗”并从《边城》有关情节及中国民俗中找了一些佐证。肖先生于是说:“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虎耳草的特殊含义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产生出来。因为‘虎耳两字在普通话里念‘huer,而在方言里却是念作‘fuer的,由此也就可以产生‘抚儿这样的联想;再看‘草字,下面不是一个‘早吗?既然如此,‘早抚儿子和‘快生贵子不也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虎耳草在《边城》中成为爱情的信物,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作为湘西人,笔者认为“当然,这只是一方一俗”和“抚儿”说的论断却错得离谱。
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是湖南湘西凤凰人,有苗族血统,少年时期在酉水流域各地漂泊。《边城》中的茶峒就位于酉水由川入湘的湘西一侧,是沈先生的旧游之地。沈先生素负盛名的作品《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都跟酉水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幅幅瑰丽的酉水风情风俗画卷。沈先生作品语言的方言味举世公认,当然是典型的湘西方言,湘西话属西南官话,跟四川(含重庆)话区别甚微。笔者旅游各地,以方言示人,一律被听为四川人或重庆人。西南官话“虎耳”念“fuer”,但在湘西无“抚儿”之谐音谐趣。笔者乃湘西土家族人,妻为湘西苗族,均出身于土寨苗村,自由恋爱结婚,我们从未以“虎耳草”传情示爱,朋辈中也没有,也从未听说过有此种习俗。看了肖先生的文章后,笔者首先询问了凤凰和茶峒的学生多人,他们均说当地没有这种习俗,“虎耳”也无“抚儿”的喻义。又与出身凤凰和茶峒的同事讨论,他们有男有女,土家苗汉各族均有,有的还会说苗语,都说虎耳草就是虎耳草,一无“抚儿”之喻义,二无以之作为爱情信物的习俗。不放心,又遍询各族农村老年人,又查询民俗资料,亦未得。再说,情窦初开的翠翠,在与傩送的爱情尚未明朗的时候就拿有“抚儿”之意的虎耳草送心中的情人,也太匪夷所思了,开放得过分。
所以,肖先生“既然送‘虎耳草已喻‘抚儿之意,用以表达爱情便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不过是想当然耳,“因此,‘虎耳草的谜底也就揭开了”也就成了一厢情愿。
但是,虎耳草在《边城》中确实是爱情的信物,为什么是虎耳草而不是别的花花草草?我们得从虎耳草为何物和沈先生的人生经历中去索解,或许会有所解颐。
虎耳草在湘西极为常见,是一种常绿草本药用植物,叶片基部呈心形。土寨苗乡的土医用它来治疗风寒感冒和“猴儿包”(腮腺炎)。从《从文自传》中可以看出,沈先生儿时是一个流连山野的典型顽童,对虎耳草不可能不熟悉。而写《边城》时的沈从文,新婚不久,青岛执教,与新月派文人交往密切,多成挚友,热衷学习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并运用到写作实践中去。他应该密切接触和学习过西方文化知识,对丘比特之箭不会不知,且虎耳草的花语是真切的爱情,“喜欢此花的个性沉静,保守内向,消极退让是你的特点,但你的外表跟内心世界并不一致,你眼光锐利,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内心盼望得到真挚的爱情,外表却是冷冰冰的,你这样只是掩饰自己的真性情罢了”。(见http://www.haolee.com/maoer/augury/f/h002.htm)虎耳草的花语简直就是翠翠性格和爱情观的恰如其分的刻画。沈先生创作《边城》时,顺手把儿时常见而又暗合西方文化特质的虎耳草作为翠翠爱情的信物,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边城》描绘的湘西,是沈从文先生心目中理想化的行将消失的文化湘西,是与自称“乡下人”的自己格格不入的城市的对立参照物,是湘西独有的土家苗汉文化混融后的综合体,让生活在全球化中的中国人找到了心灵的慰藉物,让生活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汇背景下的中国人有了怀旧的凭借。他们对《边城》的喜爱是由衷的,但对《边城》的阅读带有极强的主观性。现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亦蔚为大国,可依笔者看来,研究沈的学者中,对沈的作品解读到位的很少,中外沈的研究者中的翘楚当属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凌宇先生,凌先生是湘西土著,对沈从文作品的文本理解没有隔膜。《边城》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实至名归,但对她的解读,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方面土生土长且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湘西籍语文教师是不该缺席的。否则,像肖先生写的这类文章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如果以之来教导广大中学生,我想不会有什么益处。
(田旭东,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