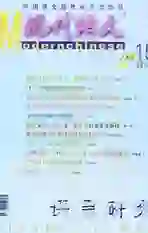东北方言中的满语与文化
2006-07-27吴红波
【摘要】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语言范畴的地名、口语词汇、亲属称谓等是人类文化的反映。满语作为珍贵的满族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满族历史语言资料,还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东北方言及普通话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的体现。
【关键词】 满语 东北方言 文化 接触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e,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这些意思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最重要的标志,也为灿烂多姿的人类文明揭开了序幕。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历史上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积极创造,那么语言应该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语言的诞生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诞生,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促进了其他文化现象的诞生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代码。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社团即使解体了,但是只要文化特征或文化心理没有消亡,这种语言或它的某些成分依然可以存在。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语言的发展比文化史的发展要缓慢一些,某些文化现象消失了,反映这种文化现象的词汇有可能随之消失,也有可能转而表示与旧词的词义有联系的新事物,因此追寻这些词的辞源有助于了解某些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和某些文化现象的演进过程。
在东北这片美丽而富饶的黑土地上,由于历史的溶铸和自然的陶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早在四千年前,这里就生存着一个古老的部族——满族的先民,其源出女真。满族人入关后,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一统天下276年,开创了中国的第三个黄金时代。这样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上却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曾经连文字都没有。满文是在努尔哈赤时期才创造出来的。就满文本身而言,大量的词汇或从汉语中借用而来,或从蒙古语中移植而用,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从女真语照搬过来。对满族人而言,满文与汉文都是新文字,而汉文的文化背景是博大精深的,满文则只限于日常口语;再者由于满族人口较少,且与汉族杂居,结果满族人迅速汉化。康熙皇帝不仅精通汉字,而且精通儒家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也都如此。这是满语被废止的主要原因。尽管满语使用时间较短,但仍对汉族聚居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东北地区。东北作为满族的集聚地,也是满语通行时间最长的地方,因此,东北汉族人至今所使用的大量地名、日常词汇和亲属称谓等,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满语的积淀,并夹杂在汉语中使用。
一、地名文化
地名是因地命名或为地命名的专用名称,是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一种语音符号,属于语言范畴。它必须借助于语言和文字来表示。因而,地名词语包括三要素,即地名的含义、记载地名词语的字形及地名词语的读音和意义。同时,地名也是一种文化标记。罗常培先生对地名研究的语言学意义做了精彩的概括。他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 特定的地名必然反映特定的文化,因此,地名是我们认知其创造者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具有重要的文化认识价值。
满族是中国东北部的土著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数量浩繁的满语地名。伴随着满语的逐渐消失,这些地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未能流传下来而湮没消逝了。虽然如此,至今仍存在数量可观的满语地名群,仍以其迥异别种文化的独特面貌在我国的地名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比如,哈尔滨,为满语“晒网场”之意;又有一说,其满语发音为 halfinn,直译为“扁状的岛屿” 。齐齐哈尔,旧称“卜奎”(bukui),是摔跤手之意,是满语“哲陈嘎拉”的音译,为边疆的意思。佳木斯(giyamusi)按满语解释,佳木斯为驿丞,噶珊为村,所以佳木斯为“驿丞村”或“站官屯”;1888年,由依兰旗署设“东兴镇”,后因重名,恢复沿用佳木斯至今。嫩江,原称“墨尔根”,为满语“精于打猎的人”之意,后在1913年设嫩江县。其满文发音为 non ula。伊春,1967年设伊春市,满语为皮毛之乡的意思,是由河得名,伊春境内主要河流为汤旺河,在伊春市市区的一段称为伊春河。同江市,1913年设临江县,后于1914年改为同江,1987年设市,同江旧名叫“拉哈苏苏”,苏苏一词,满语中为高梁,拉哈一词语义未明,现正在查找中。牡丹江,满语中称“牡丹乌拉”为弯曲的江的意思,汉人取谐音为牡丹江,满文发音为mudanula。“吉林”又叫“吉林乌拉”,是满语江沿的意思。
满族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在地名上的命名手法和构成形式,与汉民族侧重于精神风尚的命名习惯截然不同。汉族往往在地名中寄托和表达纪念、颂扬等精神情感,满族则侧重于直观地体现地方特点的一目了然的命名方式。
满族的地名命名过程,起源因素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内心的精神生活,只不过关于物质生活的内容是命名思维的主要部分而已。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因素相互作用、融合,共同孕育着地名的产生。在维持生存、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创造了寄托朴素情感、反映直观思维、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对现实世界加以分类并赋予其独特意义的多姿多彩的地名。
地名文化是一个代代相传连续不断的传承过程,是民族精神与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能体现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特征,反映文明的进化过程。满语地名的命名体现于生产劳动的过程,形象地反映了其命名者生活生产方式变迁及意识形态的演变,展示了独特的民族智慧、希望和信念,同时渗透了民族主体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情感,并带有独特的创造性,是思维意识的一种物化形态。
东北地区在地名命名上的满族特点,是其地域、生态环境、经济和文化的客观反映。
二、东北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满语词汇
满语对东北方言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词汇方面有许多满语成分。如在东北有种用羊或猪的骨关节来玩的游戏,叫“抓嘎拉哈”。“嘎拉哈”即是满语,指动物腿上的距骨(据说这种游戏和萨满教的某种仪式有关)。读chua的“抓”在东北话里也指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如猪吃食的动作,也可以叫“chua食”。东北人在指责别人胡说的时候一般说“你别跟我瞎勒勒”,满语里“勒勒”是说的意思。东北话的“挨剋”指受到指责、训斥。“剋”就是满语“打”和“指责”的意思。东北方言里有时形容人邋遢时,就说成“特勒”,也是源于满语,为衣冠不整。捉迷藏东北话叫“藏猫儿”,“猫”也是满语词,意思是树丛。东北人形容人家穷时,说“穷的叮当响”,“叮当”来自满语,也是穷的意思,响则是后加的。东北话的“磨即”“磨蹭”也是来自满语,指做事很慢。满语里的“咋呼”本是泼妇的意思,到了东北话里成了“诈唬”或“咋呼”,是瞎喊、不礼貌或不文明的意思。东北方言中有两个最常用的词,一个是“剋碜”,一个“埋汰”,“剋碜”一词在东北方言中使用率很高,是丢人、丢脸的意思;而“埋汰”一词则是从满语来的,意思是不干净,很脏,在东北使用比较普遍。
满语不仅在东北方言中有积淀,而且在普通话中也有。“挺”好的“挺”,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词,它是从满语里来的。有些生命力比较顽强的满语词汇不仅进入东北话和北京话,而且成为现代汉语里的标准词汇,如“聋拉”一词就是满语词汇。又如,普通话里的“马马虎虎”来自满语“lalahuhu”,“磨蹭”来自满语的“moji”或“moduo”。汉语里的“巴不得”也是来自满语,只不过稍微变化一下。“利索”和“麻利”来自满语中的“lali”。“啰嗦”也是来自满语,与唠叨或絮叨一样。“别扭”来自满语的“ganiu”,在满语中是特殊的意思。
三、语言接触与文化接触
世界上没有始终孤立、一成不变的文化。任何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结构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种变化通常称为文化变迁。引起文化变迁的原因除了自然环境的变迁、重大的发明发现,就是文化的传播和接触。其中文化接触是导致文化变迁的较为恒定、持久并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作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和重要载体的语言,其发展变化势必要受到文化的这一系列变化的影响。文化的变化尽管只是语言变化的外部原因,但是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许多语言变化(不是所有变化),都能从文化的变化方面找到背景性的或推动性的原因。在很多场合,文化变迁的原因同时又是语言变化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必然与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的接触必须以语言接触为手段,语言和文化二者之间天然有一种互相包含、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接触以语言接触为媒介,而语言接触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接触;另一方面,文化的接触必然在语言中有所体现,并导致语言的深层接触甚至语言融合。
清朝时,满族在东北聚族而居,人口众多,分布也广,拥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满语作为官方语言占有重要地位,是东北地区通用的语言。清代中晚期尤其是民国时期,关内大批汉族移民陆续迁移到东北地区。关内移民大都租种满族人的土地和围绕满族村屯居住,杂居共处,互相学习生产技术,相互效仿生活习惯,乃至后来互相通婚结亲,满族和汉族逐渐融合。共同的地理环境、互相补充的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上的接触,致使满族和汉语难免互相碰撞,而正是在碰撞的过程相互渗透最后达到了融合。满语作为底层语言遗留在东北方言中,成为东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北各族居民所运用。这是满语对东北方言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满族对汉语普通话乃至世界语言宝库的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曹莉萍.浅析满语对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影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黄锡惠.满语地名与满族文化.满语研究.2000年第2期
[3]赵阿平、杨惠滨.21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新发展.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
[4]胡艳霞.黑龙江满语蒙古语地名小议.满语研究.2003年第3期.
[5]赵杰.满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6]爱新觉罗·瀛生.满语读本.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7]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吴红波,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