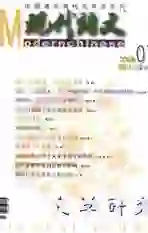白先勇作品中的放逐与回归
2006-05-20吴小琴
一、时间的放逐与回归
人的自由,本质上是与人的放逐同体共生的,人类因欲自由而遭放逐,被迫的放逐使其获得了有限的自由,而彻底自由则意味着彻底的放逐。白先勇的《寂寞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和《孽子》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笼罩在命运这双无形的双手下,遭受着时间、地域、情感三方面的放逐。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寻找过去的青春与荣耀(《青春》中的老画家);在异国他乡沉沦、挣扎,想融入到异国却被狠狠地抛出圈外(《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情感与传统相悖,想追寻真实的自我,却被命运拒绝在幸福的门外,处于情感饥渴的人们要么奋力推开命运大门却坠入绝望或死亡的深渊(《玉卿嫂》中的玉卿嫂),要么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中寻求安全感,心灵却得不到安慰,在孤寂的感情沙漠中自己温暖自己(《寂寞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感情放逐中以长篇小说《孽子》最为突出,开篇就用“放逐”开始叙述一群青春鸟的无家可归,他们被父亲们放逐,唯一理由——同性恋。
白先勇的作品中无不流露出一种悲悯情怀,将主人公的辛酸、痛苦、无助归结于命运。这些人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他们饱尝世间冷暖,经历练狱,天堂之门却无法打开。这些主人公一直在寻求一条回归之路,想做一个真正自由而幸福的人,可白先勇让他们许多人回归于生命的终点,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痛苦。人在创造中获罪,又在反省中赎罪,他们借助罪恶的力量完成有效的创造,又通过哲学、艺术或者宗教寻求灵魂的解脱,前者构成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历史,后者则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历程。白先勇用笔谱写了放逐者的精神历程。
时间的无情是白先勇着力表现的主题。1958年发表的《金大奶奶》中时间将女人的青春消磨殆尽,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男人只看重物质与青春,将金大奶奶抛弃。在男人另娶新欢时,她含恨自杀。善良执着的她何曾想过时间对一个女人的伤害,还苦守着一个不忠的男人。奴性思想伴随着金大奶奶的一生,最终她以死亡来诅咒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元稹笔下的“白头宫女”尚能“闲坐话玄宗”,因为这些宫女已习惯这孤独终老的生活,平静地发不出一丝怒吼。白先勇笔下的第一位主人公金大奶奶虽说带着旧式的奴性,却能以死反抗命运放逐的悲哀,以死来回归自由。一开始时间放逐的悲哀旋律就处于高昂状态,谱写了一曲反抗放逐之歌。随后白先勇用舒缓的节奏释放压在读者心中的痛楚,创作出《月梦》。主人公吴钟英对静思藏于心底狂烈的爱,其实是一种纯结的同性之爱,静夜的纤美月光烘托出爱的真诚。他对过往青春的怀念融入到每一个青春的身体里。命运让静思消失,吴钟英再次遇到如静思般青春的男孩,生命激情被点燃,回归到原始的幸福,他对这些青春男孩的热爱实质上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时间让他失去了青春,他却执着要找回属于自己青春的那段激情。这种温情在《青春》中却迸发出来,白先勇谱写的时间之歌的旋律再次高昂,让人感到时间的无情。老画家对青少年的青春无法捕捉源于自己青春的逝去,他却要拼命抓住被时间腐蚀了的过去,扼住青少年咽喉的那一刹那,他走向了疯癜,谁也逃不过时间的侵蚀。白先勇让他的人物仇视时间,与时间为敌。在那里,时间很扎眼地呈现出直观的腐蚀性力量:它让一张年轻的脸布满皱纹,让健壮的躯体丧失活力,最终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人的生命。它的永恒轻易地伤害人间的爱欲和尊严,肉身在它面前只是镜花水月。《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却成了一个特例,时间无法在尹雪艳的身上留下痕迹,书上描写她总也不老,带有“神性”特征,像一位命运女神左右着别人的命运。她实质上是欲望的象征,吸引人们不断地去抢夺,自己却置身事外。她似乎没法让时间放逐,她成为时间坐标轴上永恒的原点。尹雪艳超越了时间,是命运的化身。只有命运才能控制时间,让时间停止、倒流、运转。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凡与命运抗争的都走向了死亡,顺从于命运的过着麻木的生活。人被时间放逐后已回不到当初的原点,顺从也罢,反抗也罢,自身再也无法回归。尹雪艳却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当与命运合二为一,掌握命运时,时间才不会放逐你,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白先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他用自己的笔将人们的困境展示出来,给人以启迪。萨特说:“人毕生与时间斗争,时间像酸一样腐蚀人,把他与自己割裂开,使他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属性。一切都是荒唐,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白先勇笔下被时间放逐的主人公的境遇如利剑直刺读者心中,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压力。白先勇谱写的时间放逐之歌,时而高亢,时而低沉,诉说着放逐者的无奈与绝望。人类创世之初一直与时间做着斗争,夸父逐日道渴而死。金大奶奶、吴钟英、老画家这些人物如同夸父般追着时间,却被时间吞没。白先勇层层揭开时间的面纱,让尹雪艳成为了永恒。
二、地域的放逐与回归
时间改变着一切,时代的变迁,环境的置换,一切都物事人非。白先勇的《纽约客》和《台北人》讲述了被地域放逐的一群无辜的人们。地域将主人公的经历劈成两半,一半是过去,有美好回忆的大陆、台湾,一半是苦不堪言、遭受着回忆煎熬的现在,现在的台湾和美国。今昔对比在欧阳子女士《王谢堂前的燕子》已透彻地分析过。六七十年代,台湾青年因为不满台湾社会的专制、高压、封闭,大批地涌向海外时,中国大陆因为与西方社会阵营在政治制度上对立,再加上风行极左思潮,事实上将海外华人拒于门外。
1964年创作的《芝加哥之死》将旅美华人的内心世界的孤独、彷徨、无助展露无遗。一个自愿离开祖国去美深造的吴汉魂,在六年与世隔绝的学习中变得麻木,丧失自我,连母亲的逝世也激不起他感情的波浪。当他抬头注视这陌生城市时,才知道自己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去。物质的贫乏阻碍他融进社会,精神上无根让他失去自我。无意识对祖国文化的依恋,与有意地吸收美国文化形成反差,祖国文化式微在强大异国文化面前显得弱小,带来一种自卑感。一种无法适应最终让他一跃,结束了年青的生命。一个“自我放逐”的吴汉魂,徒有一个“汉魂”的名字,却没有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失去了自我。吴汉魂一直在忙碌中生活着,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对异国文化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依恋,让他无法决择。当他有勇气结束自己生命时,也就回归到生命的起点,可惜人不可能有第二次生命,他已没有回归之路了,要么现世忍受,要么干脆消失。地域放逐一开始也以死亡来诉说放逐者的悲痛,将特定年代漂流于异国的华人困境毁灭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地域放逐背后那种文化的悲哀。《芝加哥之死》将个人放置异国文化背景中,吴汉魂代表着想融入非母体文化的一类人,残存着的母体文化与整个异国文化相抗争,注定带来悲剧。白先勇接着思考如果将母体文化全部抛弃,是否就能融入到异国文化中去,于是创作了《上摩天大楼去》。通过姐妹对异国文化态度的对比,展现要融入只有放弃自我,抛弃自己的根。带有传统美德的玫伦到美国后变得似乎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妹妹玫宝却从此失去了精神依靠,在异国只感受到寒冷。玫伦徒有物质的奢华,精神依然没有融入进去。是否完全保留母体文化精神就可以融入,在《火岛之行》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主人公林刚热情、乐于助人,保留着中国人的美好品质,却与那个重利的异国文化不相容,得不到同为中国人却被洋化了的人理解,《安乐乡的一日》也是这样。白先勇进一步为这些人寻找出路,《谪仙记》中李彤带我们进入了自由者的世界。由于战争,李彤留学美国。同样是战争,她失去了父母,变得放纵、游戏人生。她在异国始终以优越的身份生活着,但她属于无根的一代。当最亲的人离她而去,生命的厚重就没了。在世俗中享乐、放纵、麻木,过着自以为自由的生活,殊不知灵魂已离开祖国远去,只剩下躯体而已。她比周围的人活得精彩,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死,命运将李彤放逐,又让她回归到自由,悲苦之情渗入其中。李彤属于旅美台湾作家创作的“无根”一代,是这一代中的独异者和佼佼者。李彤用生命唱响了地域放逐者的悲哀之歌,她比吴汉魂的生命精彩,但仍以悲剧告终。白先勇寄寓笔下的主人公名字深刻的含义,吴汉魂空有“汉魂”的名字游离于祖国文化之外;李彤的生命像热情的太阳灼烧着自己;林刚的正直、刚强代表着中国人的精神;依萍如浮萍般的命运在骨子里却依恋着祖国。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性格代表着各自的命运。白先勇将这些人物置于广阔的陌生世界,让他们感受着个体的特殊。在放逐到遥远的地域里找不到答案,白先勇将目光定于台湾,创作出《台北人》。
《台北人》中,没有几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大部分人物是随40年代末移民浪潮而漂流至陌生海岛的大陆人,也正因此,他的作品独具一份与旧民国历史相纠缠的情结。《台北人》中每位主人公都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由于社会动乱、变迁,过去遥不可及,现在苦不堪言,心理反差造成了一幕幕心酸的悲剧。这在《游园惊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一切都是由唱《游园惊梦》开始,蓝田玉当初虽红极一时,却地位低贱;后来她虽荣华富贵却失去了真爱;而如今她虽生活优裕却孤独寂寞。年老的丈夫只能给自己物质享受,对自己心爱的人无法表白。多年后已无法唱出《游园惊梦》,真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台湾与大陆有同根的文化,大陆人漂流于台湾找不到过去的辉煌与感情,是自己不能融入新地域还是不想融入。白先勇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他只将一幕幕放逐者的悲剧展现在我们面前。
白先勇注意到历史对人的制约,人在历史面前无法反抗,只能顺着历史卑微地活着,这是白先勇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每个时代的悲剧。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和传统也是白先勇个人的写照,他笔下的主人公无法像他能用笔让自己回归,能让自己的心接近传统文化,主人公的放逐其实是一种回归,用痛苦的经历证明自己在这世上活过,向世人展现放逐者的悲哀,希望更多的人幸福地活着,不用放逐,更不用在放逐中回归,以青春、死亡为代价。在时间的长河中,白先勇关注个人内心的感情,青春敌不过时间摧残;在地域的变化中寻找个人栖息之地,母体文化难以融入异国文化之中。
三、感情的放逐与回归
在时间与地域的放逐中,已充斥着感情的放逐。时间、地域的阻隔,将人的感情击得粉碎。人们对于异于社会常理的感情持抵触、毁灭的心态。《我们看菊花去》中姐姐由于精神问题被世人遗弃;《闷雷》、《黑虹》中的福生嫂和耿素堂都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福生嫂始终克制着自己的情欲,耿素堂虽然出走了,但在一夜风流后走向了死亡。《玉卿嫂》中玉卿嫂却将感情放逐回归到自由的高度,她身为寡妇却爱上了自己的“干弟弟”,并与他同居。玉卿嫂传统意识中的奉献精神和强烈的占有欲,将她与庆生死死捆在一起,庆生爱上别的女人后,玉卿嫂杀死了他,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玉卿嫂在那个社会敢爱就冲破了束缚,她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但也同命运同归于尽。这些主人公的爱得不到社会承认,被社会放逐,遗弃,他们挣扎过,反抗过,但争不过命运的嘲弄,都以悲剧收场。
从《月梦》、《青春》开始,白先勇开始探讨同性恋的内心世界。在那个时代同性恋不被人们接受。《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朱焰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进入公园,放纵自己。《孽子》中充分地展示了同性恋者不为世人理解的悲苦生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基督教的《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描述:人类始祖亚当因夏娃而受蛇的引诱,偷吃了禁果,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引诱、偷吃禁果,父亲(上帝)放逐,在《孽子》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群缺少父爱的青春鸟在同性之中寻找爱,偷吃了“禁果”中的“禁果”——同性恋。同性恋如果放在上帝眼中不知是否会背上双重十字架,上帝眼中容不下亚当与夏娃的背叛,他们违背了上帝与他们定下的契约;人类眼中容不得同性之恋,容不得异于常态的感情,这些人背上了人类给他们的十字架,人类变成了这些人的上帝,他们只有躲在黑暗的王国里寻找光明。白先勇曾说过:“《孽子》所写的是同性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什么同性恋的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迫的人,中国读者也许是由于经历了过去的动乱,虽实际情况和问题不同,但感受却一样:一种被压抑、被中心权威束缚、被流放的感觉。”被中心社会放逐,被权威放逐,如同人类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无家可归,一代又一代的人寻求回归天堂之路。
《孽子》中同性恋的人偷吃了禁果中的禁果,上帝会放逐他们,人类也会放逐他们,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怜悯,也得不到人类的尊重。上帝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人类眼中也一样。人类被上帝放逐,却学会了上帝如何运用权威惩罚人类的权术,殊不知人类自身的罪也未赎完,却将自己的罪转移到不合群的同性恋的人身上,让他们在这世上无立足之地。这种伦理的悖论让人无法理解,人的追求总是这样自相矛盾。大多数人类无法逃脱这一悖论,他们在圈外嘲笑少数人,殊不知他们自身也陷于上帝给我们制造的圈内,以五十步笑百步,上帝看在眼里,笑在心中,难怪犹太人会有这么经典的一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主人公李青、吴敏、王小玉都有一个破碎的家,他们的性取向的不同遭到社会、家庭的放逐。他们不约而同地逃到新公园,在这黑暗王国里嚣张姿纵,身心受到严重戕害。寻父贯穿全书,现实中的父亲将他们放逐,只有寻找精神父亲。父子冲突造成父亲位置的空缺,他们想回归,只有填补这一空缺。书中描写的三对父子,阿青父子,龙子父子,傅卫父子都带有悲剧色彩。父与子都没有赢得这场战争,赢得是这个社会的传统观念。
从时间放逐、地域放逐到感情放逐这一流程都与白先勇的经历有关。从小得病被世界隔离,由于战争的关系到处流浪,到美国后对祖国的依恋,同性恋为世人不理解,这些都融入到作品中,我们感受着作品的爱与恨,也感受着白先勇的感情世界。余光中曾说过,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在他每一部作品中都流动着放逐与回归,其实白先勇一直在追寻中国传统的文化之根。漂泊在海外的他更明白这种传统,更爱这种传统,他一辈子都在追寻,身被放逐于国外,心却回归于传统。
(吴小琴,湖北三峡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