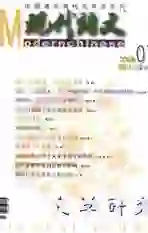从历代边塞诗看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2006-05-20王素敏
一
中原农耕文化的内涵,早已熟稔于人们的心脑,而“草原文化”,却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奎曾在《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中的论述或可作为一家之言:“当我们阐述草原文化时,指的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带有骑马民族特点和草原生活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其内容是以草原和草原主人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感知和认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现象,并通过特定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观照生活、抒发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草原文学应该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具有一定语言思维能力时就诞生了。与汉族的文学一样,草原文学也起源于诗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保存最早的《匈奴歌》,真实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思想感情,堪称古代草原文学的杰作。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大将霍去病将万骑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其夏又攻占祁连山。二山皆水草丰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里反映出匈奴以畜牧为业,失去了它们,不仅使匈奴的牧业生产大受影响,而且使匈奴丢掉了强盛的声威,以至于连族中的女子也显得容貌顿减无颜色了。“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焉支”与“阏氏”谐音,失去了焉支,也就等于失去了阏氏(单于的正妻)。妇女不能为人正妻,这当然更是羞愧难当“无颜色”了。所以,历史学家林干称这首民歌“内容具有十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及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特色”。这首民间流传的歌谣,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我们不排斥它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可能,但从全诗整体的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看,无疑是匈奴人的作品。全诗连用两句“失我……使我”,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和强烈的主人公意识,对长期游牧于北中国大地的匈奴民族来说,战争失败以致丢失大片的土地牧场,理所当然地感到悲伤而又愧恨。“六畜不蕃息”与“妇女无颜色”,既充分表现出事态的严重与损失的惨重,同时也体现出匈奴民族人民对中原汉族统治者占领其土地的强烈仇恨和不满情绪。
从《匈奴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当民族间的矛盾激化,两个民族处于对立和冲突的状态时,文学作品作为映照现实的一种手段,就会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情调,来反映这种民族间的存在状态。草原民族对汉族的情绪情感是如此,汉族对草原民族也莫不如是。汉族士人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其民族出身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决定了当民族矛盾出现时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独立性,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是,当民族间的战争爆发时,一些反映边塞征战将士缅怀故国、情系乡土的忧愤深广的作品便脱颖而出,并且被陈列在文学史的突出位置上。如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是一首雄浑悲壮的边塞诗,诗人选取两个典型细节“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传出北部边塞奇寒的神髓,反映了边塞征战的艰苦卓绝。王昌龄《从军行》(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描写了军队在沙漠中大规模出征的情景:狂风卷动着飞舞的黄沙,天日为之昏暗,风沙之中半卷的红旗引导着一支士气饱满的队伍缓缓行进,预示着将要爆发一次激烈的战斗。范仲淹的《渔家傲》,咏叹在北宋积贫积弱之势下久戍边塞将士的内心抑郁。其中“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突出表现了戍边将士内心的复杂情感。一方面,边塞寒苦,久戍怀乡;另一方面,卫国逐敌,重任在肩。思乡之苦与报国之情交织在一起,将军因之而发白,征夫为之而泪下。这一画面形象生动而富于概括力,给人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之感。清代吴嘉纪《赠歌者》诗:“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樽前。从此一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从诗题来看,这是歌者唱了“边关调”后,诗人于席间感怀世事而作。诗人悲慨万端地说,自从这首反映边塞征战的曲调在中原响起,二十年来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兵燹遍地,生灵涂炭,泪水沾衣的情景就再也没有断过。后人便常借用此诗来表达身处乱世的遭遇和心情。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反映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妇女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的诗篇。离乱时代,男儿们或保家卫国,或忧国忧民,此时妇女们(即便是贵族妇女)也不能再如和平时期一样过着安适的生活,有的甚至还要承担起和平大使、保国平安的历史重任,远嫁异域。而她们内心的悲伤愁苦却无人知晓,只能暗自神伤。《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之女名细君者,曾以公主身份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为右夫人,后又下嫁其孙岑陬军须靡,生一女。她悲愁终日,自作《细君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安得黄鹄兮归故乡!”东汉末年由胡归汉的蔡文姬,相传作有《胡笳十八拍》,她曾与南匈奴左贤王为妻十二年,熟谙那时胡地的文化习俗,所以有可能写出“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等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匈奴游牧文化的繁荣情况。但是全诗同《细君歌》一样,中心是表现自我的思乡情怀:“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 “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 这两首诗歌在文化内涵上的重要意义,是明确地反映出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在自幼于中原农耕文化中浸染长大的刘细君、蔡文姬看来,“汉地”与“异国”天各一方,风物悬殊,人情迥异,是难以联系在一起的。她们怨恨“吾家”将其远嫁到他乡异域,思念家乡情真意切,希望能像鸿鹄一样飞回故乡,却又难以割舍骨肉相连的母子之情。另一位贵族女子王昭君远嫁匈奴,为宁胡阏氏,从胡俗,生儿育女,泽被后世,至今传为佳话。虽未见其有诗歌传世,但我们或许可从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其一)中探其心迹:“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诗人以设身处地的心境,写王昭君身在匈奴,心系故国的情思,同样感人肺腑,动人情怀。显然,这种怀念中原的思乡情感,只能出自汉家女子之口,而绝对不会是游牧民族妇女的文化心理状态。
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无论是草原民族还是中原汉族,也无论是七尺男儿还是柔弱女子,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都明显忠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一切均持排斥态度。因此,此时的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他们宣泄爱国思乡感情的最好载体。
二
草原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居无恒处”,到处游动,它们较之祖辈守在某块土地上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原民族来说,眼界更开阔,胸襟更博大,更习惯于汇纳众长,壮大自己,尤其注意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民族的文化。
拓拔鲜卑向南迁徙建立北魏王朝后,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第一次开创了使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同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北魏、北周等朝代的鲜卑族皇帝和皇室,许多人精通汉语语文,留下了不少古典诗词。象北周文帝宇文泰第七子宇文招的《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概括了北疆军旅景象,慷慨雄壮,豪迈英武,同当时南朝的纤巧柔弱的诗风大相径庭,实为后来盛唐边塞诗的先声。
《敕勒歌》是产生于北魏至北齐间的民歌,由敕勒族人斛律金首唱。它不仅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更主要的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审美尺度,都具有鲜明的骑马民族的特征。诗中将苍天与穹庐相类比,不仅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艺术想象,而且也反映了那时北方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而“天苍苍,野茫茫”的深邃博大的意境,既是典型的草原自然环境的写照,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精神气质的外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敕勒歌》超越了一般景物诗歌的内涵而具有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的文化价值。金代著名的鲜卑族后裔诗人元好问曾在《论诗》中评论此歌为“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对于这首诗歌,元好问绝不仅仅只停留于欣赏者的角度,并且将其神髓化用在了后来的创作中。
辽金时期,草原民族的汉语文学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其成就尚不能代表汉语文学的水平,而在于草原民族汉语文学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从此以后,草原民族汉语作家,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持续发展,草原民族汉语作家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
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汇融合。元朝近百年间,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既是作为当时统治集团的主体文化.必然影响逐步扩大,波及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不断吸收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丰富和壮大自己。我们从元代许多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人描写草原生活的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例如元代开国名相、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推行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政策,他自己的诗文既长于描绘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狩猎游牧生活,同时又眼界开阔,善于横向比较。这是过去草原文学中所没有过的。他这样描写阴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将“西域”与“江左”,亦即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作比较,自然就要比就阴山写阴山气势恢宏,意蕴深邃。他的《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诗则完全是以汉族文人的价值观评判昭君出塞,以感伤的情绪吟咏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契丹、汉族文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交流。耶律楚材从军西征时写下了大量的边塞题材的诗文,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前夕,一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契丹族文化精英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是元代开国名相兼名将的蒙古人伯颜,善诗文,存有《咏鞭》、《奉使收江南》等绝句,俱大气磅礴,表现出骑马民族的豪放英武的心理特征:“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此诗作于灭宋南征途中,既反映了它葆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也显示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恰体现了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双向交流带给文坛的新气象。
三
草原文化对汉族文人诗词创作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它是在慢慢渗透中完成这一转变的。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汉族文人主观上对草原民族的文化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但民族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汉族文人受草原文化耳濡目染,尤其是在汉民族处于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时,汉族文人进入仕途之后,必然要与这些民族官员朝夕相处,客观环境使得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汉族文人在与草原民族文人唱和时,势必要考虑到对方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在接受其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勇武强悍的个性,便这样借助其政治优势,向汉族文人的创作中渗透。
辽金之际,南北交往密切,出现了不少汉族诗人描写草原风光的诗篇。严羽的《塞下曲》,描绘了黄河河套西北部风光:“渺渺云沙散橐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与严羽齐名的严仁也写了一首《塞下曲》,同样是描绘草原傍晚的景象:“漠漠孤城落照间,黄榆白苇满关山。千支羌笛连云起,知是胡儿牧马还。”这两首景物诗都写得舒缓闲适,生意盎然,呈现一种对草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艺术上的圆融美。明初僧人梵琦有咏塞北草原的诗作数首,对当时的漠北漠南的蒙古族游牧生活描写得颇有特色。如《当山即事》:“水草频移徙,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氎,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租。”在明代,与此风格相似的还有另外几位汉族诗人的诗,如钱逊的《胡人醉归曲》:“更深宴罢穹庐雪,乱拥旌旄马上归”,描写别有风味;于谦《塞上即景》中的“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及“坐听鸣笳送夕阳”句;李梦阳《云中曲》中的“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奔紫塞头”、“白登山寒低朔云,野马黄羊各一群”句;谢榛《漠北词》的“石头敲火炙黄羊,胡女低歌劝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李攀龙《观猎》的“胡鹰掣镟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等句,都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在这些汉族诗人笔下,北疆草原不再只是朔风劲吹、黄沙漫天的令人生畏之地,而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向往的风俗画卷,这正是汉族文人在思想上对草原民族文化接纳、认同的外在表现。
由于北方草原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也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优势互补。同时,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冲突、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
(王素敏,包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