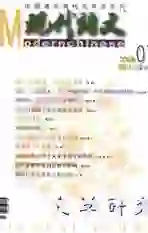秦观:飘摇词心
2006-05-20李春丽
《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只赋,赋才也;长卿,卿新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字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在这里冯煦特别拈出“词心”来谈秦少游,确实颇具眼光。“词心”作为评赏词人的一个标准,切合了词体的特征,因为词作为隐约幽微的情绪抒发,确实更多地借助于心灵深处的一种敏锐的感受。而且在评论中冯氏更肯定“词心”,认为“词心”胜于“词才”。
那么何谓“词心”?最早直接提出这一概念的应该是况周颐的《惠风词话》:“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见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只酝酿何如耳。”
归纳况氏观点,词心可谓三内涵:其一,词心乃为“万不得已”的真切深情;其二,词心乃是酝酿而生,发之于内,未可强求;其三,“词心”酝酿而出,即有词之真也。用我们的话来讲,词心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真实、独特、一贯性的创作感知,词作是词心最真实的载体。
早在宋代李清照曾言“秦少游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就“主情致”这一点应该属于“词心”范畴,至少说他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灵。后代学者围绕少游“词心”作过很多探讨,更多看到的是作家的脆弱与敏感。而今透过《淮海词》的仇怨绵绵、泪水盈盈、愁天恨海、满目凄清的伤心词境,笔者以为秦观“词心”最主要的是一种无可皈依的生命体验,是飘摇的词心。所谓飘摇,既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感受状态,也是自我生命的体验方式,往往决定了作家在面对人生境遇时的一种基本反应方式。而面对种种处境的变化,作家所体现出来的一惯性的对应状态,往往就是他内在精神的准确表达,那么我们可以从词作来寻绎这一位“古之伤心人”的内在真实状态。
“孤魂不竿归”——浮梗漂萍的身世与无所归依之感
关于秦观的家世,我们能知道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其《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一诗中写道:“我宗本江南,为将门列戟。中叶徙淮海,不仕但潜德。”(《淮海集卷四》)可知家门由显赫到中落的变化。在《与苏公先生简》中,秦观谓其家境:“敝庐数间,足以庇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饘粥死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七。”(《淮海集》卷四十)也就是勉强度日的情形。幼年丧父的不幸,加上贫困艰辛的生活状况,常使他痛感到生命好似“浮梗漂萍”,对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格外敏感,潜意识中形成在这一方面的惧怕和敏感,在他的词作中,他总在表达这样一种归宿无着的情感:“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扬州梦》)(晚云收)。远谪郴阳,“乡梦断,旅魂孤。”(《阮郎归》)(湘大风雨破初寒)尤其是元符二年,身处雷州,在举目无亲绝望中竟自做《挽词》:“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表现出身如孤魂、飘荡无依的无助和恐慌。在这种飘摇的景况下他也曾多次表达出对桃源境界的向往。“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在《点绛唇·桃源》:“醉荡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隐括桃花源,表达了对人生归宿的苦心追寻。其实细考秦观词作,这几乎就成为他人生所有痛苦的指向了,而秦观的“词心”,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是最“万不得已”的了。如果说此后的人生能做一点弥补,也可能有所改观,然而从秦观此后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所遗憾地看到,一生多舛的遭际更加强化了他人生飘摇感,逐渐形成一种“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的基本形态了,这就是“词心”。正如王国维所言:“生即痛苦”,因而在《人间词话》中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又说:“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秦观正是一个与苦难相始终的人,他的苦难来自于不幸的身世和坎坷的人生遭际,而他因这苦难而生的“万不得已”的“词心”就是由此而生的无所皈依的心灵状态,在以后无数次创作中,他总是最能从这一点上感受到生活的苦难。
“人不见,水空流“——多舛的人生遭际与漂泊无定之悲
虽然秦观在青年时期已经才华显露,但还是淹留场屋多年。第三次进士及第,然已近不惑之年,而此时残酷的党争序幕已经拉开。与师友苏轼同升共谪,无辜陷入残酷的党争旋涡,政治命运惨遭摧折,其内心的愁苦更为凄苦和感伤。“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龚自珍:《题红禅室诗尾》),境遇促使了敏感心灵的痛苦感受,而心灵感受中最容易让人感到绝望的那一部分往往是一以贯之的,秦观的绝望情绪更多的是因为其所感到的人生无定的漂泊感。词中多以怀旧念单的情绪,表现出对孤单前程的深深畏惧,对漂泊生涯的极度忧惧,那种人生的万不得已的情感成为所有悲苦的焦点。
绍圣元年(1094),新当人士章悼,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追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因“离忧”而生巨大的悲哀和绝望,在离别之中所写的最可伤感处又是“当日事”之过往,“人不见”之怅惘,“水空流”之无奈。是人、事两空,独自飘零的痛楚。其中对旧友前事的格外怀念,体现他对于未来前途的无限忧惧感,对前路的不可预知使他有了“落花飞絮”般的生命体验,在这样的心境下才有“便做春江都是雷,流不尽,许多愁”的深切悲情!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惧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进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生平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此段记载比较直接说明一个问题,即作家心理状态不同,所对应外界境遇的不同反应。同样被贬的处境,苏,黄都能各自解脱,秦观往往更多地感受到失去的痛楚和将来的难为,表现出独自面对不确定未来时的那种惶恐和忧伤,表现对孤单和漂泊的生存状态的格外敏感,这就是秦观的“词心”。其实就苏轼的人生波折,宦海沉浮比之与秦观更为过之,但苏轼却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心灵走过了苦难。
被贬处州时,他写了《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比之“便是春江都是泪”更加悲哀。但词表达的依然是从离别而起的曾经携手而今独自的惆怅。“人不见”,“携手处”,他所怀念的依然是相依相伴的日子,最能触发他生命感悟的往往是相互依存的情形,对这种情形的无尽追忆正表现出词人对此刻飘零生活的深深畏惧和巨大感伤。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对两个“伤心人”有这样的分析:“小山所写之伤心,原来只不过是对往昔歌舞爱情之欢乐生活的一种追忆而已。而秦观所写的‘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为谁流下萧湘去《踏莎行》一类的词则其所表现的变不仅是对往昔欢乐的追怀,而已是对整个人生绝望的悲慨和对整个宇宙之无理的究诘。如此的‘伤心,才真正是心魂摧抑的哀伤。”遭贬的遭遇更促发了他那种飘零之感,他始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会着人生的种种,而这种方式就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万不得已”的情感存在。
尤其是被贬郴州之后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迟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萧湘去?”
王国维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甚可堪一句则变凄厉矣”。词的开端,真正体现的是一种前程渺茫路途难定的难寻归宿的无依感,表达出作者生命思想中一直萦绕、始终无法释怀的一贯追寻,是他所追寻的一个集中的体现。与这样的追寻相呼应的竟然是“孤馆春寒”,巨大的失落和凄楚之感使得作者不得不有杜鹃啼血般的哀鸣了。下片海之寄梅传书也归宿于出发的相思,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萧湘去?”寄托的依然是漂泊无定的浮萍飞絮般的人生感叹!真正是“千回百折之词心,始充分表现在字里行间,不辨是血是泪”。“千载之下,令人腹痛”(王士桢《花草蒙拾》)。
“那堪肠已无”——并入身世的艳情与断雁无凭之慨
秦观的艳情词和他的身世词一样是“词心”的产物。在飘摇无依这一点上是一贯的,是词人真实心灵的体现。二者其实也是互相渗透的,这样的词在更深的意义上也包含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包括对人生社会,对自我情感世界这两方面。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礁门。暂停挣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处,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处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是一首离别词,上片叙别时之景,勾勒出暮色苍茫,凄清弥漫的境界,含蓄地表达满腔的别情。下片直言离别的痛楚,并以景为结,写尽离人面对的冷落与凄凉。看似艳情词:“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然在别情中,包含了身世漂泊的悲苦。“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贯注了词人官场失意、前途渺茫的抑郁之情。“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一个“谩”字,所包含的何止情事!也是对政治失败与身世凄凉的悲苦叹息。怪不得周济评此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宋四家词选》),可谓是独具慧眼。一生都付飘摇,何况身之附丽!
从飘摇词心出发的人生漂泊感,在艳情词里常常突出地表现为总想借助什么又总无以借助的惶惑。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萧湘时所作的《阮郎归》,论者以为可能是抒发与长沙艺妓分别之情,词云:“萧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躇,有人偷向隅。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余。人人道尽断肠初,那堪肠已无!”断肠而又无肠可断,其意翻进而折转,想以肠断寄情,而今竟无肠可断!那么人生还将有什么可靠?什么可凭借?什么可把握?诚如明人杨慎批《草堂诗余》所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
这样的表达在秦观亦是常见,他总是以一种独特的心理去体验人生,把那种毫无凭借的孤独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到郴州贬所约一年,他有《阮郎归》之作:“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单影只,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结句是奇思妙语,然却由“词心”所致,大雁南飞大概只至衡阳,而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就这一句,真正是阻断了所有的凭借,只剩了无边的孤独和无尽的思念。作家所选取的这种表达方式,看似很偶然,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是酝酿于中的一份格外的敏感。这种敏感,往往不是简单的由外物触发,甚至可以从心灵去设想的,也才更能体现深厚情感。所以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确实是“心”之“伤”啊!
(李春丽,包头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