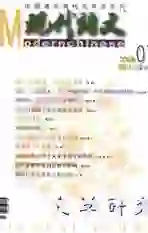浅谈杜甫笔下的儿童形象
2006-05-20张延波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诗歌中对儿童的刻画,同样是放在对他所在的那个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语境中进行。他总是通过描写儿童的悲惨生活来揭露批判动荡不安的黑暗现实。在他的笔下,幼小的儿童承受着太多太重的苦难,他们在战乱中挣扎着,或东奔西跑,或饥寒交迫,或尸横荒野:
“兵草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在《羌村三首》中诗人这样写道,这里虽然没有对儿童形象作更为具体的描写,但一个“尽”字却写出了儿童对于战争的无从逃脱之苦,正当成长的时候,孱弱的孩子却被赶进不该他们进去的军营,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生死无常的战争生涯,对未成年的孩子而言,这是何等的残酷!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是贫穷和饥饿,诗人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没有放弃对在无穷无尽的贫穷与饥饿中的儿童的关注:“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哭,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北征》),这是久别的父亲回家时所看到的一幕。白净细嫩的娇儿娇女,本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花枝招展才是,但贫困的现实只能使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不弊体。“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身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这里写的是诗人携子女仓皇逃难途中孩子们食不果腹的惨状。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白骨堆里就充盈着儿童的尸骨,而这少儿的尸骨中甚至还有着诗人自己的儿子!一个曾经还算“生常免租税,名不逮征伐”的小官僚家庭的子女尚且衣食不保,性命难存,普通人家的孩子更是可想而知了!
诗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于这种表面的物质的困苦之下更进一步地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对儿童心灵的严重摧残:“柴门鸣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羌村三首》),这里的一“怪”一“惊”,写尽了骨肉分离对于儿童心灵的伤害。“我在”应是高兴的事情,但因为分离太久,儿女们早已习惯了“我”的不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无法承受“我在”的事实,于是便有了在常人看来反常的“怪”与“惊”的心理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心理上的变态与异化了。更为严重的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污染孩子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是我们在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所感到的无奈与尴尬,当然,这种无奈与尴尬首先是原本天真可爱的儿童对老者的欺侮,对偷盗行为的不以为然,这种顽劣的品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堕落的开始,而引发这种堕落的是社会的贫穷,因为既是“盗贼”,就说明他们“抱茅入竹”不是简单的顽皮,而是迫于无奈的生计。
杜甫诗歌很少专门去写儿童,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诗人在他的众多的诗作中总是不会忘记对于儿童的关注。从涉及儿童的诗歌的数量来说,在历史上众多的诗人中,杜甫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为什么诗人对于儿童表现出这样一种长久的兴趣呢?高度的责任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杜甫的许多描写儿童的诗歌是以自己流亡生活为基本素材的,试想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不是把孩子当成是可怕的累赘,而是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仁慈宽厚的爱,充满着对儿童美好天性的由衷欣赏,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证明。
“仆夫穿竹语,稚子入云呼。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穴鼯”,当诗人在《遣意三首》中描写孩子的天真健康、无忧无虑的活泼之态时,诗人的喜悦不是同样也溢于言表吗?更为重要的是,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尤其对儿童道德上的进步、生活劳动能力的培养给予了及时的训导,表现出了一个长者的应有的责任。
他注意敦促孩子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避热时来归,问而所为迹”(《催宗文树鸡栅》),“卷耳可疗风,童儿可时摘”(《驱竖子摘苍耳》),“堂下可以畦,呼童对径始”(《种高苣》);他要求孩子们努力学习日常功课:“呼俾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小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仗藜还拜客,爱竹遣儿书”(《秋清》);他更教育孩子们如何为人处世:“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郑公五首》)。
在杜甫诗里,强烈的责任转化为深切的爱,深切的爱最终落实在对儿童长久的关注与细致的观察,这是诗人对儿童形象刻画的内在的心理逻辑。这样一种深厚的逻辑起点,使得他不仅写他们的折磨与苦难,也不仅写他们的天真与纯洁,更写他们在苦难的生活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的品性。
在《北征》中,诗人刻画了这样一个在生活的煎熬中仍然不失对美的近乎天性的追求的女孩,令人感慨万分:“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阁”,虽然没有象样的化妆品,也不懂什么化妆之道,又是在无家可归的流亡途中,但正因为如此,姑娘的行为才显得那样的可爱、可敬。即便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诗作中,细心的读者也会感到,宽厚的诗人在痛惜儿童人格异化的同时,对仍然留存在他们身上的稚子之气所发出的会心的微笑,在儿童的“公然”为盗的行为中,诗人似乎也看到了他们未被老练世故的社会完全污染的本真之处。于苦难中凸现孩子的天性,一方面说明了这种天性的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诗人的良苦用心:诗人决不是为写儿童而写儿童,他是将儿童的天性视作一种希望、一种理想来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对抗。这正是诗人在诗歌中对儿童形象刻画的高超之处。
回过头再来看看诗人对那个随父母逃难,在长途中艰难跋涉的活泼男孩的描写:“仆夫穿竹语,稚子入云呼。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穴鼯”,这个阳光男孩形象是在与“云”“魑魅”“穴鼯”等阴暗龌龊的形象的比照中刻画出来的,二者构成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理想与现实的两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实是不乏浪漫主义精神的。
金启华在《杜甫<北征>赏析》一文中说:“杜甫描写儿女情态,常常结合着时世的描绘,构成反映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生活小插曲,并非是儿女闲情与天伦之乐的单纯抒发”,这样的评价大致是不错的,也适合杜甫所有关于儿童描写的诗作。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现实意义不仅包括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也包括在黑暗的现实中对美与理想的坚守。
(张延波,河南省汝州市职业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