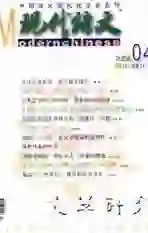古典文学中“后花园”意象的审美意蕴
2006-03-03梁永存
在中国古典文学描写青年男女爱情(通常被称为才子佳人程式)的作品中,通常会将才子佳人发生爱情或者幽会的地点选在一个草木繁盛、生机勃勃的地方。上古的《诗经》中是在真正的大自然“桑中濮上”,到了宋元以后的作品中就大多在后花园,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红楼梦》将其发展到了极至,出现了“大观园”。我们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称之为“后花园”意象,这种“后花园”意象,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不仅仅是为了给才子佳人们提供一个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具有深刻的审美意蕴。
自然美意蕴——充满生机的后花园
后花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草木繁盛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的意义。如《牡丹亭》中杜家的后花园“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杜丽娘一见就生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感叹。再如《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就用整整一回专门描写了大观园景致的妙处。那么,为什么众多作品都选择这样一个地点来促成青年男女的爱情呢?其最表层的原因是因为这对于隐蔽状态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来说是个绝佳的地点:后花园少有人去,不易被人发现;即使一旦被人发现也极易隐蔽,所以后花园受到作者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除此之外,后花园还有其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早在西周、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有许多借助自然美景表达情感的诗篇,最为典型的就是《郑风》。在《诗经》的研究史上,《郑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离奇古怪的解释和说明,以致面目全非。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的时候,就会发现《郑风》不仅描写了男女的爱情,而且展示了许多与爱情有关的郑国的民风、民俗。郑国在西周以前隶属殷商,殷商是个重祭祀好歌舞的民族,商之后这种风俗在郑国得到继承并盛行不衰。《韩诗章句》中记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己上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史记·郑世家》“正义”引《韩诗外转》:“郑俗,二月桃花水出时,会于溱洧水上,以自祓除。”由上述古籍记载可知,自伸春二月的桃花水到三月三日的上已节,都是郑国青年男女聚合相欢、对歌言情的良辰佳日。春天草木萌发,鸟语花香,在春天的男女之会上人们常常即景即兴唱起情歌,久而久之,情歌中写春就成了一种习惯。
这种写春的习惯再加上春秋以前,无论平民或贵族,都沿袭以春天为婚期的风俗,就使得蕴含无限生命力的春天,成了后世青年男女发生爱情的最好的背景。但随着封建社会逐步发展,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断加剧,当时的时代和社会都没有条件给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提供一个真正的自然宽松的环境。于是,作家们就选择了后花园这样一个模拟大自然的环境来代替。因此,后花园就成了古典文学中表达男女情爱的重要场景。
人性美意蕴——价值人格的显现
在由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对爱情的排斥是十分严厉的。儒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德崇礼”。“礼”本身是社会的名分系统和伦理秩序,它排斥两性爱情的需要。《易传》认为,礼义就是排出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等级系列。孟子还进行过礼色之辩,“色与礼孰重?曰:礼重”。儒教只让男女结成既非爱情也非友情的“勉强共同生活的互助组”。而这些礼教纲常对于青年女性来说则束缚得更紧。
《西厢记》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出身名门,她的家中“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她一次潜出闺房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更有甚者,莺莺在幼年时期,便被父亲许给老夫人之侄、郑尚书之子郑恒为妻,只因此时父丧未满才未得成合。莺莺生存境遇的特殊性在于,既有父母的亲子之爱,又有父母礼教的管束。当莺莺的父母为了使女儿更有社会地位,未来更高贵而按照门当户对的等级秩序定下亲时,他们也不可能想到,这已经改变了舔犊之情的性质。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顺从外在的等级纲常,而完全忽视了作为主体的女儿的内心追求。《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也是这样的遭遇。父亲杜宝拘管得十分严密,她连刺绣之馀倦眠片刻都要受到严父的呵责,并连带埋怨其“娘亲失教”。请教师讲书,原也是为了从儒教经典方面进一步拘束女儿的身心。可怜杜丽娘长到如花岁月,竞连家中偌大的一座后花园都未曾去过,而华堂玉室,也恰如监牢一般。作为顽固不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杜宝从来不理解女儿真正的需求,用他的话说“古者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什么七情六欲?不仅如此,他对封建礼教纲常的维护也到了扭曲人格的地步。为了维护场上的清誉,当新生女儿复活时,这位平章大人不仅不亲自勘验,反而再三奏本,请皇上着人擒打妖女。哪怕杜丽娘再三痛陈原委,他也不为所动。道理很简单,他宁要一个贞节的士女,也不要一位野合过的鲜活的杜丽娘。为了违护封建礼教纲常,杜宝变得缺乏起码的家庭温情,显得绝情绝义。
爱情本来是男女青年最基本的要求,中国文学中有不少诗篇直率地表达了这种恋情的需要,南北乐府民歌中的《折杨柳枝歌》和《捉搦歌》表现了女儿愤慨地抱怨母亲不懂女儿的恋情需求,一再拖延婚事,“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论计”,但是这种最基本的爱情需求却被紧紧压抑着,使得青年女子们生发出伤悲的情绪,并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腿,能消几度黄昏?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栏干,目断行云。”这是崔莺莺对生活的感叹,当她面对草木葱老一派生机的后花园时,自然的生机就唤起了她内心对现实的不满,对自主爱情的渴望,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杜丽娘一入花园如痴如醉,她的惆怅无奈,她的委屈与痛苦便如江涛般涌在心头,《牡丹亭》中最使人感慨的惊梦这场戏中杜丽娘面对满园春色发出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凭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践!”这不仅仅是对春光这美夫人识得的叹息,更重要的是对自身之美无人怜惜的感喟。这些青年女性在悲哀和感叹中,有意识地将自己分离出来,确定了自主意识。雅斯贝尔期说:“如果他不迷失于这个世界,不迷失于无意义的和陈腐的常规,他就必须将自己拯救出这个庞大的机器。”崔莺莺、杜丽娘等青年女性的感喟,正表明了她们拯救自己的意向,而她们的价值人格也就在这艰难的自我拯救中一步步地显示出来。
崔莺莺的价值人格是由张生对诗召唤出来的,对诗是莺莺“愿得有心郎”这个价值人格的初步展露。张生的流畅而清新的诗引起了她的审美观照,而她不由自主地依韵唱和展露自己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渡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之后,随着她与张生交往的深厚,尤其是张生请来好友杜确破了孙飞虎,救了崔莺莺之后,她对张生“笔尖横扫五千人”极为钦佩,内心的“有心郎”与张生契合。这种
契合,既使崔莺莺的爱怜对象最后确定,也使她的价值人格鲜活起来,并且毫无遮蔽地完全展露。正是因为这种展露,才使得莺莺在争取自主婚姻和自身幸福的道路上敢于对老夫人进行斗争和反抗。尽管由于封建纲常的影响,她的行动有时违反常理:她一方面“人前花言巧语”,一方面“背地里愁眉泪眼”;一方面请红娘鱼燕传书,一方面训斥红娘带回简贴戏弄人。莺莺既想追求自己的幸福又怕失去先前的社会文化礼制的基地,但是当她一旦发现了二者的绝对冲突对立时,便毅然的听命于本已的价值人格,做出与张生在后花园幽会的举动。这样她就将本真的自我完全显露出来,进而从根本上把自己从生存的苦闷中拯救了出来。杜丽娘也是在一步步与现实的抗争中争取自己的爱情。她从唯唯诺诺的千金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而后又敢于在阎王面前据礼力争,身为鬼魂也对情人一往情深,到了最后为了捍卫爱情,杜丽娘又在金殿之上深情叙述、慷慨陈词,使得皇上也为之感动,“敕赐团圆”。杜丽娘的个性和人格就在勇敢大胆的追求爱情、反抗现实中现露出来。
礼教纲常并非为真正的佳人所设。《西厢记》、《牡丹亭》等许多文学作品通过才子佳人相传后花园这一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情节,揭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在婚恋方面的自主意识,否定了已成为历史陈规的伦理纲常礼制,否定了人的生存意义就是接受纲常维护礼制,并且使人性和价值人格得到深刻的展露和张扬。
社会美意蕴——自由生命的栖息地
自从“桑中濮上”的自由之风被无情的封建礼教扫荡殆尽之后,人们自由的生命与个性也被越来越紧地禁锢下来,这一点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极至。之后,随着蒙古族的南下及其政权的建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出现松弛,个性解放的要求开始初露端倪。再加上元明两代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这种形势对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厢记》、《牡丹亭》等一批反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作品相继出现。而到了封建社会最末期的清代,又沿袭和发展了元明时期萌芽的民主思想,这在文学上最主要的反应就是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伟大著作。王实甫、汤显祖等作家们首先选择了“后花园”这样一个封建思想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在封建统治的间隙中表现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他们批判了封建礼教禁锢人性、违背常情的地方,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崔莺莺、杜丽娘等一批大胆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从而使“后花园”成为了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最早基地。也是中国妇女追求婚恋自主之路中一块不可缺少的生命栖息地。
在《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出现,初始完全是因为“元妃省亲”的缘故。元春是贾政的长女,回贾府来省亲,若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回来探望父母,贾府原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的。但是由于她的角色位置元妃,标示了背后的“君王皇室”,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等级序列中,这已经是最高的阶位了。贾府历来是深被皇恩、希官封爵的,因此,对宁荣二府而言“元妃省亲”便是一桩共同的大事了。是以,大观园之筹建,便完全是贾府站在“君/臣”的臣子立场,以相应于皇室的排场规模来考量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贾元春所处的这个名位,让她可以在形式上如被接圣驾一样地对待着,而随着元妃回贾府而看似为元妃所建的“省亲别院”一一大观园,事实上的重点,乃完全是为了成就君/臣之义,而烘染出富丽堂皇的形式上的虚名罢了。大观园以“如实的建造”来颂扬了皇权的神圣之名,但矛盾之处也在这里:当省亲结束后,这当下的“崇高的”“皇权之名”功能亦同时完成而消失,然而,此“实际的”“如实的建造”却依然矗立在那里,它原初看似的神圣之名和供游赏遣玩的园子实用价值之间,有了一段差距。对此,贾元春有深切地了解:“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在这形式的“名”与现实的“实”之间造成的空隙,使元妃有了以“皇权之名”来成立“女儿国”的机会。由于元妃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皇权的依附者,相对于封建等级制而言,她可以说超越了家庭权力的核心,而到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因此趁这神圣之名所形成的空隙,元妃动用了皇权,将贾府中的姊妹及认同女性价值的贾宝玉都移置进了园内,让他们在空间上得以暂时离开了与父权制过于密切的关系。诚如元妃所以为的:“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因此,大观园便在这样的前提下,成为了女儿们的王国,而取代了初始建园的目的。这其中的转换,应该说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的动用。脂批有言:“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脂批言也就是曹雪芹以元妃省亲之名,利用了名实之间的空隙为女儿们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姊妹们和宝玉都般进了大观园之后,宝玉是“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风,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到也十分快乐”;而女儿则更是“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在这样一个宛如没有封建礼法和等级制干扰的世界中,园内的女儿们,置身在如诗如画的景致中,便以成立诗社.(海棠社与桃花社),以做诗(偶尔填词)的方式,托物寄“情”地呈现他们自己,展现他们的“感情”“性情”与“才情”,她们透过“诗”的表述形式,建立了有别于园外的世界,由与大观园平行叙述的情节中可知:园外的男子行酒令,放纵性欲,或者缺乏活泼的诗心,而园外的女子则忙于家族事务。在此大观园的世界中,女儿们的鲜活的主体特质逐渐地被建立起来,而她们的诗作也都表征了她们的性格与形象。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展现了在封建礼教纲常统治下,女儿们不被角色规定的生命光彩,就这点而言,从香菱的由园外移置园内后,方能开始学做诗,更可清楚见出大观园已成为女儿们耀动生命光华的主要空间了。
结语
综上所述,后花园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深刻的意蕴,代表了中国古代青年男女,特别是女性对自主婚姻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但是这种渴望和追求毕竟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而且文学家们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仍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许多文学家几乎都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的藩篱,而只是对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乞灵于科考得第、皇上明断,以达到大团圆的结局,也是这一类才子佳人故事的常套之一。只有到了曹雪芹那里,才突破了这种程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后花园相会”的爱情必然失败的悲惨结局。在异常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违背纲常礼教的行为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当封建礼教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被彻底地毁灭和推翻时,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选择的幸福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梁永存,唐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