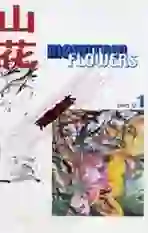打电话
2005-04-29刘自立
刘自立
你好。——她说。
对方和她应付。然后挂断了。
时隔十分钟。她又说了同样的话。对方说,你说过了……对不起。就先她挂断了。
又隔了十分钟。她又打过去。
这次是忙音。忙音中,她把对方想象成为复数的几个人。因为每一次通电话,她都处在一个无法确定前提的心态;那个要接电话和应接电话的人,是影子和实体的轮换,再轮换,就像学习哲学的学生,不知道应该如何分辨那些本来就不应该分辨的前提。于是,我们只是在虚拟的对话里才偶尔使用诗歌辩证法。我们在这个人和那个人中间进行转换,转换时代和背景什么的。
首先是时代在变,也未变——对于某些人,时代在变;对于她,没有变。或者说,对于以前的她,时代在变,而后来,是她在变。究竟是什么在变呢?
人。那些被她记录电话号码者。那些老朋友。那些本来在她记忆里永远不会老的人。以及以这些符号传达的记忆,联想,幻觉。那些老面孔,面孔后面的墙壁,墙壁上的门,门外的街道,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春夏秋冬,雨和风,政治上的雷区,冰雹,薄冰,在眼前闪现,忽上忽下,忽远忽近。他们在电话里呈现的是几个人?是还原和未还原者。是她,他,或者你。也不是。他们,本来就是她心中的一个部分,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想听到电话,她的电话。以前呢,以前,事情还没有出现本质。是没有本质的来往,人还未老,远离死亡,而现在不是。
我没有必要说明某个人的声音对于她的意味。一个熟悉的老者。第二个。第三个。每一个身后有一个背影,一个背景,一个悲剧——也许;像她一样。把时间锁定在某年某月某日,悲剧曾经上演,还会上演。于是,不是他——她的老伴,打电话告诉她——是别人。
他曾经告诉她:远离这个城市!——但是,她还是等待着,等待他的电话。
她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周围都是他的影子,像墙上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出出进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她还梳着粗粗的辫子的时候,就知道,某一日,他,会打电话。这是一个象征。一首所有人都在写的雷同的诗。但是因为有青春,电话号码就是诗句。这一切忽然陈旧,腐烂和溃败了。他,蓦然消失,虽然,也许在她看来,他没有消失,不会死。
向坟墓打电话吗?
忙音在小客厅持续着。这声音忽然变得极其质感,触之可握。他是断线的蜘蛛泪,有黏附感。是星空浩大空间里极其微小的声波粒,回忆流,尘埃和渣子。声音闪着异样的光。也许光和光组成数字。组成数字流。出现号码。
在月光变幻的瞬间,图画的操作者,躲在声音的操作者后面,暂时没有出声。他在等待她的等待—那样的话,就可以结束忙音。忙音没有文字和图画的个性特征。节奏持续,并且极其顽强。好像要推论什么,又好像放弃了。他在结论前打盹,蓄意做出某种等待状态。没有人知道她和忙音达成的妥协。
她不耐烦的表情后面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但是,轮廓清楚。拨开皱纹,那张清秀的面孔就挂在她的脸庞。
她们可以分开,合拢。一张脸是很美,沉默;另一张,焦虑。面对电话和几个可怜的号码。
然而她还是在心里说,你好。——
对方躲在月亮里?
从月亮到她的屋子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并不取决于她在哪里打电话。在家,在路上,在医院或者病房的过道或者大厅里;是第几层大厅?是呼吸病房,还是肠胃病房,或者高级病房——每一层大厅只放一部电话。
对方说,你好。——可能,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他不说“你好”了。不说“你”,也不说“好”了。几乎是无话可说,万般无奈。因为许多的他,发现她没有对他们说话的意思,只是完成一个打电话的程序。她的年龄早就到了失去牙齿的岁数,但是她,还是以她的声音占据一个记忆的空间,并且把记忆塞给对方。这件事当然严重。“他”如果活着,大约也是八十岁上下了。他就这样被她的记忆呼唤着。
在这座刚刚扩建的医院里,他年轻时的身影经常在以前未扩建的各个角落里游荡。他的确时时出现。虽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电影和小说中活灵活现的鬼——她们动作婀娜,轻飘;谈吐温柔,文雅,如风似雨。影子,在丝织的绣袍中显得梦华如烟。他们/她们去而复来,带着今天年轻人无法模仿的倩影,语调。出没,并再次出没。在这里。
是的,这个“这里”——只是一种托词和借口,在“那里”,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和场所,也行。对方回答——说了,还是没说?说和没说,不同。你们是对过话的,几年前,十几年前?五年,十年,二十年,这很不同。话语和话语的份量不同。有的话语解密了,有的没有解密,有的根本就没有秘密。话语轻重缓急,他一点到,就被理解。话中的话,一说,就传达了。解释,是多余的。打电话时候就是这样。只是说:你好吗?这就够了。现在,打电话要说什么,什么也不要说。只是完成一个动作,甚至一个仪式。因为,没人懂她要说什么。说了,也没人懂。懂,也是误会,是误解,误读。一个神秘的信号躲在电线或者其他角落里。一个神秘的信号借用她的面孔,眼睛,眼神和皱纹。他们说皱纹是鱼尾,带着海的秘密,波浪和哀叹。神秘者的沉默借用她的罗嗦和意欲,做诗。没人懂。她说了好多话。那些话没有逃出话之门。那门关着。始终上锁。是很重的,很大的锁。
于是,她远离沉默。失去了沉默的嗜好。反抗沉默。这是危险的;像保持记忆一样危险。沉默里,语言形成内敛的张力,像一首诗。
“你好”……
他说了好久,她也听了好久。这是一个瞬间。几乎没有战胜忙音的能力。忙音近乎永恒。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夜晚是一个分水岭。一个瞬间的分水岭。这是她最近一次的回忆。她重复这个回忆一百次。现在,在医生面前,还在重复。但是医生教她指自己的五官,前额,胸膛,四肢。就像做操,有一套动作。动作有数字代替。变成信息和号码。她的指向是一个人吗?
她指向自身吗?
做完检查,我遵医嘱,把她横放在一张巨大的活动床上,离开病房,向实验室转移。
床下有六个轮子。床头有推手。我推动床。轮子旋转。是的,床开始移动。在上坡和下坡中移动;一张,焦虑。面对电话和几个可怜的号码。
然而她还是在心里说,你好。——
对方躲在月亮里?
从月亮到她的屋子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并不取决于她在哪里打电话。在家,在路上,在医院或者病房的过道或者大厅里;是第几层大厅?是呼吸病房,还是肠胃病房,或者高级病房——每一层大厅只放一部电话。
对方说,你好。——可能,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他不说“你好”了。不说“你”,也不说“好”了。几乎是无话可说,万般无奈。因为许多的他,发现她没有对他们说话的意思,只是完成一个打电话的程序。她的年龄早就到了失去牙齿的岁数,但是她,还是以她的声音占据一个记忆的空间,并且把记忆塞给对方。这件事当然严重。“他”如果活着,大约也是八十岁上下了。他就这样被她的记忆呼唤着。
在这座刚刚扩建的医院里,他年轻时的身影经常在以前未扩建的各个角落里游荡。他的确时时出现。虽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电影和小说中活灵活现的鬼——她们动作婀娜,轻飘;谈吐温柔,文雅,如风似雨。影子,在丝织的绣袍中显得梦华如烟。他们/她们去而复来,带着今天年轻人无法模仿的倩影,语调。出没,并再次出没。在这里。
是的,这个“这里”——只是一种托词和借口,在“那里”,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和场所,也行。对方回答——说了,还是没说?说和没说,不同。你们是对过话的,几年前,十几年前?五年,十年,二十年,这很不同。话语和话语的份量不同。有的话语解密了,有的没有解密,有的根本就没有秘密。话语轻重缓急,他一点到,就被理解。话中的话,一说,就传达了。解释,是多余的。打电话时候就是这样。只是说:你好吗?这就够了。现在,打电话要说什么,什么也不要说。只是完成一个动作,甚至一个仪式。因为,没人懂她要说什么。说了,也没人懂。懂,也是误会,是误解,误读。一个神秘的信号躲在电线或者其他角落里。一个神秘的信号借用她的面孔,眼睛,眼神和皱纹。他们说皱纹是鱼尾,带着海的秘密,波浪和哀叹。神秘者的沉默借用她的罗嗦和意欲,做诗。没人懂。她说了好多话。那些话没有逃出话之门。那门关着。始终上锁。是很重的,很大的锁。
于是,她远离沉默。失去了沉默的嗜好。反抗沉默。这是危险的;像保持记忆一样危险。沉默里,语言形成内敛的张力,像一首诗。
“你好”……
他说了好久,她也听了好久。这是一个瞬间。几乎没有战胜忙音的能力。忙音近乎永恒。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夜晚是一个分水岭。一个瞬间的分水岭。这是她最近一次的回忆。她重复这个回忆一百次。现在,在医生面前,还在重复。但是医生教她指自己的五官,前额,胸膛,四肢。就像做操,有一套动作。动作有数字代替。变成信息和号码。她的指向是一个人吗?
她指向自身吗?
做完检查,我遵医嘱,把她横放在一张巨大的活动床上,离开病房,向实验室转移。
床下有六个轮子。床头有推手。我推动床。轮子旋转。是的,床开始移动。在上坡和下坡中移动;在几座楼房中间移动;在昼夜之间和岁月之间移动。她安静,或者并不安静地躺在那里。她在半路上喊出一个字母:啊,K!!!
我看见阳光刺在她的眼睛上。她闭上眼睛。任由阳光打量她的面颊。一个横陈的人体在移动。看到这里,我有点尴尬和悲伤。其实,人体是在众目睽睽中移动的;但是我觉得天地间的荒凉已达极点。后来,这个印象,我再也挥之不去。
我们进入地下室狭长的,阴湿的,霉味刺鼻的通道。这个通道好像是专门为我和她准备的。虽然有个护士跟在身边。但是我觉得通道里只有我们o
“啊!!”她叫喊。
因为,通道的入口处像坟墓的入口。
要给坟墓打电话吗?
——你好!
那声音于是穿越时空和生命,直达灵界。
没有人接。
没有——人——接!
是的。
人。这是一个空白。
没有人,就对了。但是没有人接,何必要打电话。
如果不是人接?又如何?
有人接吗?(她问电话机。)
没有。
电话机回答。
于是,忙音。
我听见忙音。在移动中。
我不是听见移动电话,而是听见从每一部电话机里传出的忙音。这声音围绕在我的身边。这声音围绕她。
现在,我继续在忙音里推动床。
时间漫长。移动床的时间漫长。虽然只有几分钟。
“没有人接。”
我纳纳成木。木,移动。和床上的一具准僵尸。只有电话忙音提醒我,她还活着。
轮子嘎吱嘎吱。忙音嘀嘀嘀嘀。我脑袋里静静的轰鸣声彻天彻地——我从来没有听见如此惊天动地的雷声,在我的体内炸响。
女护士打开了通向地下室二层的铁门。
向下行进。这是事实。再向下吗?
床,移动着。她躺在床上。躺在移动的床上。
她。是谁?一个打电话,却没有“人”接的打电话者。如此而已乎?
医生突然决定要给她做试验。和打电话没有必然联系。不,和打电话有必然联系。
“谢谢你,医生。”她说,“我回去打电话谢谢你。”
医生吃了一惊。马上镇静下来。
那么,有“人”要接电话了。她想。
通道里有一线光,出自惨白的日光灯,却照样产生阴影。水泥铺在墙上,还是水泥,但是,已经是另一种水泥,带着岁月的斑驳。看见死尸出入和病菌撒播的,据说还有sas病毒出入的这个空间。一个蛇型的水泥身体。被掏空的隧道。这个冠状病毒在微笑,在水泥里外自由出入。出入那堵坚固的墙!
她的影子出现在墙上。人的影子。影子跟随我们。我们跟随自己。我跟随她。她跟随水泥。等等。
没有人给墙打电话。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人给墙打电话,是电话的第一个原则——虽然俊男靓女总是面壁而立,说,啊,你好!好像和墙打电话——或者和墙分享之。
分享。这是一个庞大的命题。
……和灵魂和魔鬼和人和植物和动物和影子和实体和火水和灰尘和污垢……。和电话对方的……分享语汇,分享分享的语汇……
这是我要替她转告你的—她在医院接受一种或者几种精神和身体检查。
“她还好吗?”对方是一个被身份保护的亲戚。
他在电话里说。在地下室接到手机。
而我,没有身份。
没有手机。
我,雇工,她,护士,身材好或者不好的女人。第几代:远房的亲戚,孙女的孙女,儿子的儿子,孙子:拖着一件件月亮衫。
她被放进了玻璃和金屈合成的一个容器。她闭着眼睛。八十岁,或者十八岁,黑色头发,打开髻簪,披在颈下。忙音,像头发的点缀,布满其间。每一根发丝,都是通向电话对方的,一根强有力的电线。发丝在容器里和一些微笑的金属片,发生摩擦,进发火花,是叶绿色的火。在一个无形的微笑中,我听见她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好……她是用发丝传达电讯的。
是的,现在,忙音止。
我分明听见她极其微弱地叫着她的丈夫的名字,那个名字是大写的K,K。K!K!K!!!
于是,事情变得简单易懂——她要在一,二,三,N个电话谈天者身上发现什么。这个发现就是记忆。虽然,她的远方记忆比眼前的记忆好——这是老人的特征吗?一个八十岁老人满头的黑发所产生的向四面延伸的记忆让她对数字获得敏感被数字驱使或者相反这很合她的意志美学虽然美学在她的身上死去了又不能像死不死活不活的异域的思想者一样弯腰沉思并不给什么人打电话。她常说,你好啊燃后坐下来弹琴一样拨号。
她的手指放在电话机上的形状,是一种记忆指法。这个指法,画成图画。虽然这份图画没有艾舍尔的新潮画或者赵佶的老派字那样有名望,可是,我很迷恋她的指法。她对指法无意识。她忘记了对方是谁。但是,数字,电话号码和降叫、调奏鸣曲,让她兴奋。她说,你好……其实,是说给一个魂灵听的。对方的反应对她而言等于灵/零或者简直就铺天盖地等于一切。于是,在我们此刻的叙述中,她和他,凌空而起,在我眼前升起,升华。墙和壁,灵和魂,二者合一外,多了一种元素,沟通天地的一个短句:你好。
这就多了一种元素:叫——数字。
她彻底记忆数字。这是让那天晚上变得越来越低垂的黑夜极为吃惊的事情。月亮上,她用几个音符,写上几个号码,改变了月亮的逻辑。这当然令人想起星星这音符。这比附庸俗。虽然,我没有说,星星是音符。
你好!——她或许是说给星星听的。
但是,我分明看见她这样说:你好!——星星掉在她脚下。
星星说:你已经打过好几次!
她挂断了电话。
可是,当她看见第二颗星星升上来,就又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你已经打过好几次!——星星们开始愤怒。
她,看见第三颗星星升上来。接着,繁星密布,音符成谱。忙音。对方是忙音。忙星和忙音;忙得很。谁有功夫听你胡言乱语。
她无奈回到琴上。她的指尖轻触琴键。琴说,你好!她说,你好!你好——无论是文怀沙还是赵朴初吟唱的诗词里,都没有“你好”这般美丽的辞藻。他们只是在人间唱鬼。她于是弹出一个星星符号。诡秘。坚定。绵长。艾丽丝说,你好!她。老态龙钟的脸。鲜花。破绽。泪痕。片刻。我看见她居然弹奏了一曲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旋律——忙音1,31,31,31,31,31,31,31,31,31,31,3,……然后是4,4,4,4,4,44444,444444……我愕然。
我看见她苍老的面孔上闪现着满足的微笑。因为,这时候,她说K——谜个字,是一个调。一个派。一个格。这时,她在医院狭长的地下室走廊里悲哀四溅时说出的K,居然身影毕现。不一样的K。
毕竟,她的头脑处在极度混乱中,疼痛中。血栓,成为她记忆的第一个休止符;那是红色时代的缩影。以后,这个休止符越来越多,越来越密。K———她说,你好!K———成为她的血宝贝。严重啊,事态。
这个字离开她已经半个世纪。在她的琴谱和字典里,这个字,本来已经死了。而她要反抗这个现实。她在休止符的周围写上了无数的电话号码。就像查阅字典和总谱一样,在所有这些人名和调性中查找K。在她的电话生涯里,你好——之后,就会出现K这个字。这种K,当然大于——你好——这含义。
情形是这样的。
她第N次告诉对方,他/她,是K。于是,出现一系列麻烦。
首先,对方不是K。第二,她本人不是;再者,K死了半个世纪了,有人提及他,但是这种提及,也要死了。第三,延续下来的故事是,她发展死者的故事。她像太阳罩住世界一样,要把她的全部黑发延及所有的电话终端。一如博德里雅尔说的,她制造一维世界以对应多维世界。
第四,我愿意为她辩护。我排除干扰。超越道德律。我发现,她的琴声和电话一样。如我朋友说的,是三种艺术观齐置:装置,观念,行为。电话——装置;打电话——行为;观念——K。当然这是个秘密。我没有偌大的篇幅叙述于此。但是我要说,这是个观念。是活在她心灵的观念;她在别人身上寻找他,就像拉康说的,在自己身上寻找别人。第五,她开始说话,把词,变成句子;把短句子,变成长句;把长句子,变成雄辩。这样一来,在电话的另一方,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敌对群体,甚至包括我本人了。但是,我还是把事情一分为二: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为,我为她开启的梦端,一角蛰伏,一角惊蛰。
从道理上说,死人,不可复活,打电话,没有用;但是,在她心目中,死人,是不死人,可以打电话,这叫感情弥笃,爱乌及电;你说,你不是她说话的对象,她说,是,至少是一部分,没错,你中有他,他中有你——尤其是同一所大学出身的,如北大,燕大,金陵,校风一律,律下人同;又如,都是教书的,办报馆的,甚至唱戏,拉琴,说书的;书下人同。人以群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她,没有错。错的是你。
说归说,事情还是在起变化。人们要阻止她的干扰,应该如何去做?
至少,我不知道。
我看到的内涵太多,像复杂的曲式。忙音,音符,人,鬼,神……都是她打电话的理由;忙音,是一种阻止,但是,可以被克服,只要等待——等待——你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电话线里排队,就是等待;音符,更是一种多义的解释,是她自己的解释,自由的解释;这和忙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音乐也要等待,有预设的高潮和自然的高潮,有空白,死人和自杀,有建筑般的形式感,你可以顺路走到大街——和走到远方城市的“舒伯特”大街上毫无二致——你也可以走回头路,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太阳出来,像她;于是,就下雨了;跌倒,看见尸体,看见K——这个字对我来说也是多义的。一个起码的含义,不,两个起码的含义:一、是生死循环发展出来的白色和黑色,白夜和黑夜,白昼和黑昼;二、是他,我的上帝,不可以冒犯的一种身份!!!
说到这里,你们或许可以懂得一点我的道理了!
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她被分析的话语的段落。
这比她说的“你好,K……”——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超越K的身份和生死;她对生命和死命一视同仁。
“……你好……我看你还是躲起来。我和孩子等你,等你回来……”
于是,对方说,你又搞错了,人不对,年代不对
解释。但是,解释没有用。
“你还是不要回来!”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他不同意吗?”还是有监视者站在他的身边。强迫他说这和那。另一只手挂上了电话机。他没有适当的权限。是被看守的囚犯。
她在那件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这样想。以后,她就在第二,第三,第N时间也反反复复这样想。她告诉别人。即便别人已经对此没有兴趣。她这样打电话,持续了多少年!
“他失踪了……他会回来的。”
这是两个对位的主题。
于是,她虚拟了这个庞大的企望场。这个企望场在日常生活中拉起了记忆的铁丝网。铁藜棘刺出血。这种行为影响了许多人。朋友,同事,亲戚,孩子,直系和旁系的后代,后代的后代。
当打电话成为她的晨课以后,她甚至忘记给花浇水。她在严重和不严重的时刻,渐渐将花看成一朵朵火焰。她不停地,每隔个把小时,就来给各种花浇水。因为她仅仅知道打电话会导致忘记给花浇水。火焰被浇灭了。她移动那一朵朵,一盆盆死去的花,那些花的尸体。她想到晨课以后的午课和夜课。
在每一朵死去的花的面前,她默立,致哀。花走了,她要给花打一个吊唁电,或者说,告诉每一个人,花,死了。这是特殊的仪式。在一个个人的追悼会上,她想起花。绿色的,红色的,针叶和阔叶的。其实,她记得为他献花的场面。遗照,灵柩,哀乐。她知道一切。但是,也不知道。她不相信那是真的。
太阳落山的时候,她辞去一份工作。年复一年,她发现,周围的人像落潮一样离她而去了。她不再需要分辨他们和他。这样的分辨,是一个短暂的错误。她摆脱错误。
他,好像就在隔壁,一个可以打电话的场所。
于是,她开始打电话。电话线现在错乱了时序。昼夜倒置。看不见早晨和黄昏的区别。太阳和月亮叠垒在一起。一天的两个三、四点钟,现在合为一体。她等待第二天,是因为她忘记第一天。有时候,她一人坐在轮椅上,出没于黄昏交织黎明的街道。那些冬日的树为她花开花落。而血里,有老人的汗水滴落,化开,形成一个无形的溶洞。炎热而冰冷。甚至一个梦境,也会像伞,撑起在有雾的广场上。她消失在中心和边缘。中心和边缘,在她心里消失。她,消失在自己身上,心里。那个小保姆像幽灵跟在身后。
(这是一个被抛弃的空间。从那一年开始,到这一年结束,其间三十年空白。两头是真,中间是假。两头也许也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没有人知道。
可能,在另一个交接点,生和死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其间有几千年。
也许,生死,也是假的。一切,是假的,也就是真的。这个观念,是笔者插进来的。为了和读者辩论的。
——于是,就无法说,这,是一个空间,而那,就不是。)
她一开始认为一切人,是他人,不是他。以后,她悄悄搬掉了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也许是他;再以后,她就说,你——你,就是他。你——好,我的儿子。
也许就是如此。
也许事实是,她,一个老太龙钟的形象。我们没有必要发现性别;虽然,我们看到她年轻时的靓照。那手捏话筒的身姿,是一个具体的性别,具体的性格。但是,她现在混同于那些自以为有身份,有名号,有个性,其实一无所有者。
他们说,她不认人了。可是,她难道全错了吗!至少我,不这样看法。
她的“你好”,与众不同。这,也是一种哲学。其间的你,是你,也不是你——这难道不对吗!
你,什么时候才全部是你呢?
你忘记万物皆备于你身乎?
我犹如此,你何以堪!
我改动庚信的话,没有经他同意。因为他太老了。
是的,我没有依照你的说法来苟合他/她的说法,反之亦然。这是大家的缺点。你的,或者我的,有时候是他的缺点。这很正常!
并不是要强迫她改变什么,可是,她的习惯还是在悄悄改变。忘却,终于和记忆纠缠起来。她在月光下拨动她记忆中的电话号码。她看见微弱的灯光下月光无私的影子。她透过月光辨识电话号码。她以为她可以看见月光,即便摘下眼镜;就像她以为可以搬动月亮到另一个时代,比如,逆反时序。她喜欢在月亮下面拨号。
一次次,一次次……直到清晨。
我下夜班回来,突然看见她伫立在灯光俱灭的客厅里,只剩下一个影子。手腕上落下一连串闪闪发光的数字。张三李四王五的电话号码像看不见的灰尘落在地板上。她被数字照亮的脸很老,憔悴,但很执着,精神,燃烧。
“你回来了?!”
她说。
我躲开她去洗漱。
她站在黑暗中,沉默。是哪类沉默?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沉默被写进梅特林克的书里,被赞誉和传扬,说,沉默是金。
——对着电话沉默吗?
她想。或者我想。
这可是件大事。
沉默,在数字燃烧前沉默。数字放大,缩小,等于或不等于零。
她的沉默在火焰里波动。这是永恒和不朽之先兆啊。
从一个简单的期盼发展到期盼的沉默和沉默本身是对于沉默的又反抗又迁就的人们的一种选择而不选择的人是难以沉默直到永久的他们终于冲破沉默的呼喊令人颤抖而颤抖是在沉默的身体上颤抖因为沉默难耐一个呼喊连天的时刻就要来临就要就要像海潮迫岸这是一个先兆好像你忽然发现沉默的电话机向你召唤但是没有振动他的伟大的数字链数字链数字链上的锈铁在沉默中变得滚烫像火在燃烧连同人体的燃烧,毁灭,复活,不朽,和沉默有关。她,会沉默吗?电话号码会沉默吗?——透过沉默,我看见他。同样在那座医院狭窄的地下通道里。她穿过人群,闯过人群的注视,把他送进一个试验室。他躺在可以移动的床上。这个活动床铺下面有六个轮子。床在光天化日或者漆黑的夜晚移动。她对他说,“我回去就打电话给你……”
他没有回去。永远没有。
但是她还是打了电话。……那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止她这样做。——她告诉我。
——我有一个预感。这是一种经验。有人要打电话的时候,会有一个预感。我就会先给他打过去。反正,他会打电话来。我打过去,也好。以后——她说,这个感觉变得很微弱。微弱,懂吗?微弱,但是不是消失——从他身上传来的场,很弱,可是,毕竟有场,有感觉。所以,我打过去……。但是,其实没有“人”接。“见鬼!”
这样,别人就替代了他。
——啊,K!
她长叹了一口气。
又叹了一口气。
她有停下来的时候。
她停下来,就给她孩子们打电话。孩子,是她/他的影子。
影子们围在她周围。那是她活下来唯一的支撑。但是,当昼夜交替的时候,孩子们的灵魂全部聚居在他的身上。她对他轻叹一声。电话忙音。她走到屋外的阳台上。晨光照耀她,触动她.抚慰她。她有了温暖的感觉。“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年是何年。
她看见无脑的电线杆子,看见无脑树,看见无脑的街灯和无脑星。她没有表情地移动手指,指鼻子,指眼睛,指天,指地,指人,指神。她记得有个医生命令她这样指,停止,再指,再停止。她放弃指自己。用手指沿着月晕画了一个大圆圈。嘴巴里念出一系列号码。在她念出第十三个号码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
她赶回房子里,拿起听筒——
“你好!”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