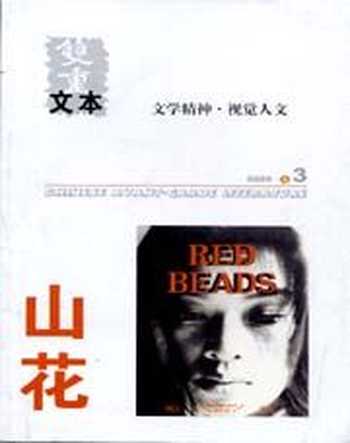都市的变迁与作家的书写
2005-04-29高秀芹
高秀芹
每一个城市都为它的书写者提供着语言、经验和叙述。在中国新文学的空间格局中,上海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和意义。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两个重要地方之一,上海以其新潮的思想和现代出版支持和传播着新文学。1856年上海开埠,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上海迅速地从一个小渔村一跃而起,成为一个国际型的大都市。现代城市的组织形式和交往方式培养着上海市民新的审美情趣,现代出版、交通、电讯又把这种新的市民观念和趣味普及化。上海,以其与传统乡土中国不同的审美情感和阅读趣味刺激着作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振小说与近代上海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穆时英们以其新鲜的感觉和现代的技巧与中国文学传统发生了革命性的断裂,而这种新的文学经验是现代上海给予的,它也只能产生于上海。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贴近上海的骨肉,走进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里,为上海书写着传奇。上海这些作家的叙述中呈现出自己,上海是包含着丰富意义的所指,很难说施蛰存们更贴近上海还是张爱玲更是上海的。他们只是写了上海的某些方面,新感觉振的上海与张爱玲的上海正好构成了荫个反差性的东西:动与静。新感觉派摄取的是飘荡在上海空中的城市符号,由外在的城市意象与刺激构造的城市:灯红酒绿、光艳绚烂的舞场,动的、摇荡的、酒的、肉的、笑的、震颤的上海,汽车的速度与摇动的舞女拼凑在一起的上海。张爱玲恰恰摒弃了新感觉派的感觉,而走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底子里,试图写出稳定的、静止的、日常的上海,写出在灯红酒绿下尘封的大园子里和弄堂里的上海。几十年后,当台湾和香港的作家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来寻找上海时,上海已成为一个旧梦。
霓虹灯下的哨兵驱散着旧上海的“香风毒草”革命和同志改变着上海。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上海真正地成了一座孤岛,上海人的西装外面罩上了灰色的列宁装,虽然在裙裾的翻动中偶尔能瞥见刹那的光艳,可是旧上海毕竟远去了。新时期以来,上海好像一个被埋葬的美人被重新挖掘出来,城市在文学的空间格局中重新成为审视的对象,城市重新塑造着文学的想像力与感觉形式。1984年,当许多作家仍从乡土中国寻找叙述对象和感觉时,城市诗人已从上海的动感和形式中获得诗情。1985年北京的刘索拉时《你别无选择》标志着现代派重新进人文学视野,稍后上海作家徐星、陈村、孙甘露、格非等也获得了现代感觉和技巧,上海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开始获得其地位和意义。王安忆在这些众多上海的作家中不是以其技巧与新异取胜,作为知青作家,王安忆与上海的关系有着走出与重新认识的过程。正如同书写老上海的作家们,张爱玲避开了新感觉派引人注目的现代技巧,而走进上海市民的普通日常生活中。王安忆也正如同张爱玲,她略过了城市表面的符号,而试图寻找活跃在城市里的精神,她像一个寻梦的人,试图在中断的上海里搭起一架内在的桥梁。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之间,两个女作家以独特的叙述方式连接起关于上海的想像和记忆。
作为上海的书写者,上海是张爱玲的书写空间。上海给了张爱玲写作的文学想像和经验,上海和香港是张爱玲两个主要的生活空间,而香港也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在张爱玲的童年记忆里还有天津和北京,那低垂着窗帘的大房子和午后的秋千是张爱玲追忆中温暖的远梦,构成张叙述底蕴的是上海。张爱玲像上海一样一下子跳到历史的舞台;一下子便光艳夺目。1943、1944年仅仅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便在中国文坛上刹那间灿烂无比,又刹那间消失。张爱玲好像预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到来,拼着力把一辈子的美丽急骤地释放出来,她急着在那个时期的上海出名,因为在她看来“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①张爱玲宿命似地选择了那个时期的上海作为呈现自己的时空,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②张爱玲紧紧地抓住沦陷时期的上海,成功地完成了对上诲的书写。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诲去香港,她的创作灵感便日渐萎缩。
1943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43年、1944年张爱玲几个主要中篇都已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分别发表于1943年9—10月,1943年11—12月,1944年5—7月的《杂志》,1944年9月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出版发行,内收小说十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心经》、《年青的时候》、《金锁记》、《封锁》、《花凋》等。从这些作品来看,张爱玲一开始便是成熟的,她的一篇篇作品是她经验的整体化呈现,所以,她的作品从时间顺序上排列并不强烈,作家的发展过程也不能在此完全呈现。尽管张的这些作品的内容不尽相同,可是她所表达的主旨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生的稳定性一面。张自己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③对人生安稳永恒性的追求,使张的作品呈现出静止时间状态。张爱玲自己说用参差的对照手法来写这个时代,“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④张爱玲的参差对手法并没有构成一个破坏性或冲突性的力量,而只是一种差异性的互射方式,现在和过去、新与旧、善与恶等在互射状态中达到平衡状态。
在被张爱玲圈定的叙述空间里,时间不再是柏格森所说的“绵延”状态,而呈现出静止状态。张爱玲的叙述空间就如一面四周充满镜子的大房子,每一个参差对照的因素都从镜子中看到自身,而不是重新发现一个他者。每一个他者也仅仅从镜子中看到自身,而没有构成故事发展的推动力。各种因素在互射中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时间在均衡中处于静止状态。《金锁记》里第一句话便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追忆性的讲故事的叙述语态一下子便将故事导人一种亘古不变的时间状态之中,曹七巧的故事便在这三十年前的姜公馆里发生。和时间一同进入叙事的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苍茫时间的流动中好像只有月亮没有变化,谁能反抗时间?曹七巧看着丈夫死、婆婆死、儿媳妇死,她自己也不过是“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七巧的女儿、儿子也没有走出封闭的公馆,女儿长安试图走过,她在童世舫的身上看到了自我,可她最终只得到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金锁记》里的上海是个被割裂开的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许多东西被急剧地挤压在一起,现代都市和封建传统贵族体制挤压在一起,客观叙述形态不曾打破空间的封闭状态,更加限定了空间有限的展现区域,客观叙述形态和封闭的空间最终造成了时间的静止状态。《倾城之恋》里白公馆里的时钟总比上海晚了一个小时,《金锁记》里曹七巧家里也永远是午后昏昏沉睡。《倾城之恋》一开头也强调着白公馆的时间状态,上海为了“节省天光”,所有人家的表都拨快一小时,可是白公馆的老钟却停止在—小时之外:“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公馆好像生活在繁闹的上海之外,生活在流动的时间之外,连搁在玻璃罩子里的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这就是白流苏生活的空间,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狭窄急促,一家子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下,却相互排斥挤兑着对方。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都有着一种被限定的拘束。她的小说一般来说,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空间,如果有变化也只是那么一次,然后又回归于那主要的活动空间。这主要的活动空间也主要是在房子里面,仿佛是室内剧式的。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再到客厅。在《金锁记》中,人物主要是在姜公馆的范围内,这姜公馆也不过是一座房子,远不是《红楼梦》中还要分出怡红院、潇湘馆之类,而只是分成不同的房间。而这不同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儿却并不分明,只是觉着它是由四面都是墙的东西围住,四面的墙又被更小的四面是墙的房子隔断着,至于怎么个隔法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就那么隔着。人物就在这中间穿梭着,活动着。那大的四面墙把一个家族的人聚拢在一起,使其处于一个屋檐下,又被那四面是墙的小房间隔开着,隔离着,使其相互窥视和相互接交着。当曹七巧从姜公馆迁居之后,住到了一个更狭小的屋子里时,那里又形成了另一个狭小的,被四面墙围起来的空间。外部的世界,只是通过这住在狭小空间中的人的出人才被带人,但是那外部的空间,在张爱玲的笔下是很少触及的。即使人物的活动到了诸如电影院、饭馆等外部的公共空间,我们会发现,张爱玲的笔也是很少对其加以展现的,仿佛那公共的空间也像这些人物被困住的那居住的四面墙围着的空间一样,是封闭的,狭小的。同样,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主要活动空间也只是居住场所。当主人公振保搬来之后,客居于王娇蕊的家里,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房子里。当振保离开王娇蕊,到了别一处所租的房子里,那里又变成了一个由四面围墙所围起来的封闭空间,在那里振保和他的新妻、振保的母亲以及后来的裁缝在演出着他们的戏。在作品中,振保是有工作的,而且是一种体面的工作;振保对妻子失去兴趣后,他也是常常出现于灯红酒绿的天地,在张爱玲的笔下也是根本不触及的,所有这些主人公居住空间之外的大的空间,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处于虚写或者虚拟的状态。而这又大大增强了主人公活动的空间的封闭性和狭窄性。
张爱玲笔下叙述空间的这种狭窄性和封闭性,由于另一方面的因素而被大大地加强了,这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人际之间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也同样是狭窄的和封闭的,而丝毫没有开放性。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对象世界,是他人世界中的一堵墙,一个限定,使这他人的世界在此人面前被挡住,被隔离,被封闭,被孤立。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在离开姜公馆之前,姜公馆的每个人都仿佛是其他人的墙,这墙构成的限定,构成着隔绝。但因为这墙、这隔离者是一个人,所以又是一个对象的世界。所以这一堵堵由他人构筑起来的墙又仿佛是一面镜子,既映射着自己,也映射着他人的他人。这映射是相互的,曹七巧既映射着玳瑁、姜三爷等,玳瑁、姜三爷也映射着她。在她从姜公馆搬出来独住之后,她与她的女儿、儿子、儿媳妇也同样处于这种关系之中,谁都离不开谁,谁都又恨着对方。这样,每个人对于他人既是一个对象,又是一堵墙,同时这墙上也似乎有一面镜子,这就构成了一种既相互对峙,又相互映射的关系。人物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就这样相互构成着,又相互限定着,相互隔离着,从而构成了一个相互封闭着的狭窄的的空间世界,直到每一方都因为限制、融绝而变得日益萎缩,日益枯干,相互间把对方榨干致死。
更为深刻的方面在于,张爱玲作品中人际关系的这种相互映射和相互封闭,都带有一种相互窥视的性质。《金锁记》一开场,是两个女仆在黑夜里议论着主人家的七长八短,这种议论就是—种窥视的表现。这时她们的议论却被睡在同一房间的赵嬷嬷听到,并遭到赵嬷嬷的呵叱,赵嬷嬷此时又是以偷听表示着窥视的另一番情景。当曹七巧的女儿长安去见男朋友时,曹七巧也同样充当的是窥视者的角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对于王娇蕊,一开始就是以窥视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刚搬来时,娇蕊正在洗头,当那头上的肥皂沫子溅在他的手背上,他的心理的感觉就仿佛是“张嘴轻轻吸着它们的”,这便是一种心理的窥视。当振保到浴室去,看到娇蕊留下来的头发,他把那头发竟收到自己的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这又是一种心理那只欲望之眼的窥视。接着第二天,振保回来便偷听到了娇蕊的电话。接着几日之后,振保又闻电话声起来,而窥到了浴后的娇蕊和她那赤裸的足踝。一日振保偶然回来取大衣,窥见了王娇蕊对他的窥视,两个相互窥视的心就这样走到一起。振保离开王娇蕊,并结婚之后,他对他的太太也处于一种窥视的状态,他妻子与裁缝的暖昧关系,就是他偶然窥见的,而他太太对他的窥视,也是站在楼上穿子的后面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封闭的叙述空间和封闭的、相互映射的人际关系,都带有这种相互窥视的性质。这种窥视的性质,增加了小说叙述空间的私秘性,以及镜像式的相应映射和隔绝。
应当说,所有的传奇故事和都市言情小说,都有某种将叙述空间从整个社会中孤立起来的倾向,以便为某种理想化的、非现实的浪漫情爱关系提供尽可能多的可能性。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理想化和从现实中脱离后带来的孤立,使传奇和都市言情小说过于模式化和过于脱离现实。张爱玲小说中叙述空间的封闭性与传奇和言情小说的这一特点不无关系。但是,它却没有传奇和言情小说的那种理想化和浪漫的情调,而更多地具有都市的挤压和个人孤立的特点。人物的相互衬托也是古典传奇和盲情小说的技巧之一,但却并不构成张爱玲小说中的相互映射和相互隔离,更少那种用互窥视的敌对。张爱玲小说叙述空间的这种压倒一切的封闭性,人物关系中的相互映射和相互窥视的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了别的小说所没有的尖锐和紧张。正是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在这相互映射、相互隔离又相互窥视的人际关系中,张爱玲展示、剖析着都市——上海的人性,它的丑、它的恶、它的裸露和阴暗。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的小说甚至是反传奇的,反言情和反浪漫的。如果说30年代穆时英和新感觉派的小说是写着都市——上海那动的一面,那千变万化、时髦而新奇的公共空间:街道、霓虹灯、舞场等的话,那么张爱玲所要展示的却是退出这些公共场所之后,回归的那私秘的空间。在都市的公共空间,每个人的私秘性是隐蔽的,暂时放弃的,每个人在这里都得遵循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而一旦离开这公共空间的私秘性,那孤寂的世界就会迎面而来。在这里每个人都不再看到自己的面目和遮蔽,而是看到自己的裸露和对他人的窥视。这些是张爱玲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底子,那种永恒的东西,正是这种私秘性的空间和人性使那公共空间的所有一切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为其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文本形式,而不是新感觉派的那种表面化的浮着的意象。张爱玲小说中的叙述空间的封闭性、人际关系的映射、隔离和窥视,都是40年代上海都市所能提供的更为本质的形式。它是真正属于市井上海的经验形式,这种经验形式在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找不到的,这正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这个都市的独特性质。
知青出身的王安忆走的是一条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道路。与张爱玲的稳定与成熟相反,王安忆和她的作品一起在变化中成长着。她的小说成为探讨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她凭借着文字与这个实际的世界发生着关联,她不停地呈现着新问题。所以,她的小说并不是同一问题的反复重写,她是在摸索着向前走。从王安忆目前呈现的作品来看,王安忆的书写状态要比张爱玲复杂得多。她文本中呈现的书写空间很广,有上海,也有小城镇以及乡村,如她想探究“民族精神”状况的《小鲍庄》的叙述空间是一个僻远的小村落,她以自身冲动来进行写作试验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乡谷之恋》的叙述空间则是小城镇或大自然。尽管如此,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的叙述空间仍是上海,我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些作品,如《流逝》、《米尼》、《悲恸之地》、《好婆和李同志》、《逐鹿中街》、《香港的情和爱》、《纪实与虚构》等等。在这一部分里,我试图分析王安忆在上海文本叙述的历史的时间状态,从而发现在两个女作家的文本中上海的迁徙。
1981年王安忆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从现在王安忆整个创作情况来看,这篇小说不是王的主要作品,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却有着特别的意味。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重新回到上海的知青对上海的寂寞感和陌生感,这似乎也是王安忆自身对上海的体验(王的十年离城与回城)。隔了十年距离的上海,构成一种异质性的东西,这种异质性促使王安忆在想像的上海与真实的上海之间寻找一种关系。《本次列车终点》是终点也是起点,寻找上海的命题则是以后的事。坐在一只痰盂里进入上海的王安忆好像与她生活的城市一直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她的另一个短篇《悲恸之地》象征性地书写了这种异质感,她写了一个山东农村卖姜的青年在上海的遭遇。卖姜的青年企图用姜敲开上海的大门,却落了空,迷失在城市里,他在城市中穿行,却被看做一个异端而被追逐。青年在城市人的围观、对峙、排斥中无路可走,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曾说:“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街上,却倍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⑤1969年,年仅15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淮北农村插队,从此,王安忆离开上海整整十年,当她重新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对于王安忆犹如一个陌生的所在。王安忆对于上海,也犹如一个异乡人。对上海的疏寓感与陌生感使王安忆把上海作为一个观察和寻找的客体,从而寻找自己与这个城市和世界的关联。
追忆的方式使王安忆舒展开曾被张爱玲挤压在一起的都市空间,把切割而圈定的封闭性空间置于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之中,时间在这种对比中流淌起来。王安忆1982年的《流逝》,写了一个旧上海资本家的少奶奶在新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意义。革命改变了一个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欧阳端丽一家从奢华富贵沦落为普通市民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的变迁。这只是一个正面叙述的故事,所有的故事也可以反过来再说一遍,当然,故事的意义在不同的叙述中不尽相同。在革命改变上海的时候,上海又改变了革命多少呢?尽管《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一个城市不再叫做‘上海了,那么‘上海到哪里去了呢?”革命似乎完全改变了上海,革命者用权力占领了城市,但情感却是异乡人。曾目睹过大上海繁华的好婆与从山东来到上海的革命者李同志始终处于相互观看的对比性关系之中,好婆眼里李同志一天天上海化,可是,仅从李同志歪斜的袜子缝里透露出李同志与上海的不相容,上海似乎没有了,上海其实并未曾改变什么。在王安忆的文本中,上海成为一个散发着樟脑味的遥远的梦,它被尘封在旧相册的箱子里,在午后的阳光里偶尔露出光艳的一刹那,却给予现实以美丽的回忆。王安忆试图打开尘封的每个弄堂的窗口,挖掘大上海的秘密。
《纪实与虚构》(1993)王安忆从个人体验人手来书写自身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她作为“同志”的后代在“同志”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的胜利气氛中进入上海,可是,她发现在这所大城里她只是个“外来户”。她的父母说着与上海话不同的普通话,限制她与弄堂的孩子交往,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戚,只有“同志”。她发现自己在这所城市里身份是不明确的,她无法在“同志”关系中获得一种依托,同时,她也无法真正地走进这所城市的灵魂中去。尽管“孩子她”是那么热切地想与这个城市认同,她崇拜地观望着邻居家的男孩去亲戚家吃喜酒,可是,她却被这些城市民俗拒绝着。老城隍庙带来的历史感对她这种无根无历史感也是一种刺激,人家弄堂里的夹竹桃的香味提示着上海的历史,这些都与她无关。她在上海这城市真正成了一个在精神上疏离的居住者,没有历史的居住者也无法确立在现实中的地位。于是,王安忆便在虚构中追忆母亲家族的历史,试图让自己的身份有一种历史的依凭。在王安忆看来,城市人是没有历史的,所有的城市人都来自不同的村落,城市人的根是悬浮于城市之外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王安忆用虚构家族神话和传统的方式重塑了现代城市人的历史。⑥
如果说《纪实与虚构》是王安忆从极端个人经验来书写上海,那么1995年发表的长篇《长恨歌》则把个人经验落到实处,《长恨歌》集合起王安忆以前所有对上海的经验与想像,《长恨歌》里尽管仍留有王安忆极端个人的经验,她尽可能把这些经验客体化。王安忆找到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王安忆写了这个女人的一生,王琦瑶的历史也就是上海的历史。在王安忆看来,女人与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城市和女人都没有历史,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人体力的弱势在这种人为的空间内转化成一种优势,女人和城市一样一下子可以跳到历史舞台上光艳夺目。这个女人是王琦瑶,也是上海。四十年的历史沉浮中的繁华与荒凉,光艳与暗淡,如同张爱玲常说的那个美丽而荒凉的手势。王安忆像一个考古学家一丝不苟地打量着繁华梦般的上海,她走出了《纪实与虚构》中个人身份的尴尬状态,或者说旧上海与新上海的紧张状态使王安亿采取了一种更谨慎的态度。她放弃了主流话语的上海形象,自觉地走进上海的民间形态中。她试图寻找上海的灵魂和精神,这精神和灵魂是上海的芯子。当年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传奇般地成为“上海小姐”,住进爱丽斯公寓,历史的变迁尘封了上海繁华梦,王琦瑶重新进入上海弄堂。王琦瑶像一条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表面上尘封起来,其实在地底下却暗暗地流动着。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以打针度日,在严师母眼里“这女人定有些来历”。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康明逊也从王琦瑶的素淡里,看见了极艳。虽然这城市是另一座,路名都是新路名,除了有轨电车的当当声,还捉示着旧上海昔日的情怀。王琦瑶的素淡和不动声色的平常心却是旧上海繁华美梦的真正底色,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下的河又流出来,她是旧的,又是新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着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心却没有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精致,面是一碗一碗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地切成丝,再撒一层细细的椒盐。上海心是家常的,有肌肤之亲和贴血贴肉的近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窗帘后面,上海因此而成为上海。
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的一生完成了对上海的书写,她用文字连缀起这个城市的历史。她如一个考古学家仔细地敲打着城市中的每一块斑驳的旧碎片,查看有关这个城市风情的那些发展的旧相册。可是,由于她是这个城市的寻找者,她对上海的叙述不如张爱玲来得近切和老道。王安忆太自觉了,很多时候她被这种自觉驱使着,自己直接跳进文本的叙述中,发表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上海没有完全融进王安忆的叙述和形式中去,她或许只是王安忆叙述的一个客体。从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比王安忆更市井化,她和她居住的上海是浑然一体的。都市经验的深刻性和独特性使她笔下的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性,也就是说,张爱玲是市井中的佼佼者,因为她能够成为市井的讲述者。但是,无论她是多么的佼佼,她也是只能站在市井的立场上来叙述,也就是说她的叙述视角是市井的。但是王安忆是一个上海市井的寻找者,一个重新发掘者,这就是使她的叙述视角比起张爱玲来要高超得多。这种高超,使王安忆的叙述视角比张爱玲的叙述视角更宽广,也因此更具有历史的意味,但也因此而丧失了张爱玲的浑然不觉的贴近。
应该说,王安忆对上海的寻找,有着很深刻的动机,这种动机里,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张爱玲对她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得王安忆也想像张爱玲一样贴到这个都市的芯子里去,掘到张爱玲所说的“底子”里去。但是王安忆所能找到的芯子不是那芯子,她找到的东西包含了张爱玲的,但又较张爱玲所呈球出来的更为广阔。
注释:
①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 13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所引张爱玲作品均出自《张爱玲文集》。
②柯灵《遥寄张爱玲》。
③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④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⑤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原载《收获》1993年第2期。
⑥在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里,她详细叙述自己作为“同志”的后代与上海的异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