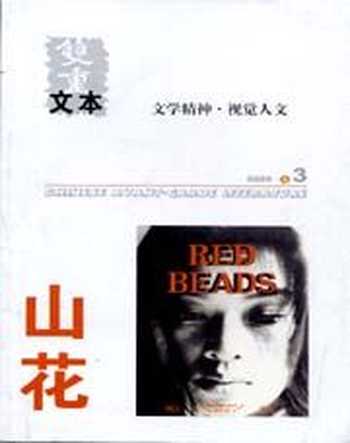《庭院》:一场精神轮廓的理性勾勒
2005-04-29俞世芬
俞世芬
《庭院》在貌似荒诞的情境之中讲述了“我”在同事景兰的引领下造访梦中庭院的事件,整体上具有寓言性质的形而上抽象化的特征。短小的文本中,作家以有限世界与无限时空为经纬架构了一个极具隐喻强力的复合时空,并对身处复合时空中的人们的精神实在作了内在的探索与考察,最终对于严格意义上的人进行了一场精神轮廓的理性勾勒。
在这个复合时空集中,传统小说中人物赖以存在的三维空间被作家转化成此在世界、彼岸世界与联系两个世界的神秘通道。此在世界就是年复一年“我”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我”始终等待着景兰能帮助“我”实现去访问庭院的愿望,“我”为自己无法确定有关庭院的记忆而“沮丧不已”。然而当“我”终于由庭院回到现实世界中时,“我”眼中的景兰家里的一切已经决然不同于先前的那个现实世界了。彼岸世界就是那个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我”却始终无法确定是否去过,但又总想去一次的“深深的庭院”。“我”最终似乎到达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庭院中的楼房里,尽管失去了自己的身体,却总算看到了庭院里的风景。“我”在这两个截然相对的领域中穿行时,还有一个关键的神秘通道。这个以钢铁搭建的长长的吊桥,竟然起自于景兰的居所。在独自向庭院迈进的过程中,难以经受考验、萌生退意的“我”在两个奇怪女人的带领下,踏上了梦境中的世界。叙述的重心显然落在后面的两个空间。无论是通道还是庭院,都显示出一种奇怪、混乱和不可解释的特征。“我”在其中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暗示着“我”在这个无限广博幽深的境域中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沮丧与恐惧。
这三种空间意象的设置,明显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对于“我”而言,重复而单调的模式化的日常生活,很难让“我”产生激情与冲动。也因此神神秘秘的景兰才能对“我”产生如此巨大的导向作用。对庭院的向往与访问,实际就是为开拓生活可能性所作的一种努力罢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企图抗拒因重复导致的生命停止的存在状态,努力完备和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身上未被发现的可能性。而这种生活的可能性显然会随着主人公的追求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当然对这种可能性的追求,主人公并非完全出于自觉。当“我”真的来到这个梦见无数次的地方时,“我”的目光是挑剔的。这间蒙灰的房间只能让“我”心生厌倦。况且庭院中的风景、景兰与景兰的两个姐姐……一切都让“我感到这是一个让人发疯的地方”,并后悔“还不如不来”。“我”的态度的这种转变,根本在于“我”魂牵梦绕的不过是一个理念的天国,“我”对它的连绵不绝的痴心与热情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子般的意气用事。所以在窥破梦境的真实面目时,“我”难以摆脱失望的情绪与退缩的念头。然而洞察“我”内心的景兰向“我”指出:“到过一次这种地方,就回不去了。”景兰显然早就经受了这场历练。如今的“我”就是昔日的景兰,而如今的景兰也正是明天的“我”。无论是谁,一旦受到这种启蒙,貌似相同的现实生活就会对其展示出截然不同的情致节奏与生命意境,并启发、诱导和鞭策他进入一个更高境界。也只有进入了这个更高境界后,他才恍然领悟到自己的生命境界已大为提高。但是,前头仍然会有另一个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主人公就这样从一种境界向另一种境界不断深入,从前的探索足迹不断成为过往的历史记忆:他就此走上了一条精神探索的不归之路。对于人内在精神的这种难以确定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解释得有些似是而非。他说,人作为存在不能被确实地加以定义,就是因为它是可能的存在或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似乎应该就是人那种求新求变求可能的生命本能与对模式化的本质反感所造就的吧。而恰恰正是这种将种种不确定渐次转化为种种可能性的不懈努力,甚至是巨大牺牲(景兰不是就将一条胳膊喂了母狼吗?),成为人开拓生命境界、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保证。
与小说空间结构存在着本质勾连与内在契合的是对小说时间的处理。对于以过去、现在、将来为尺度,主要为叙述故事开展情节提供方便的传统三维时间,作家将其物理性的功能转化成心理性的效果。首先,作品中的时间变成永远关注并强调人物这一时刻状态的“现在时”。也就是说,小说取消了所谓的历史与未来,把对人物的关注永远定位在现在的这一时刻。在这种表述方式下,作品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我”,始终真实鲜明地展示着潜意识状态下的感觉、情绪与意念。“我”的将要成行的激动,走在铁桥上的恐惧,烟雾之中的迷惑,抵达梦境之后的困顿失落,回到景兰住所的惊讶……一切都因为发自内心本然的这一时刻而显得格外生动和富有生气。这种时间的处理方式显然极有深意。因为人生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人活生生的当下时刻构筑而成的,而每一个人又都在以自己的意趣与方式感受生命、思考生命和创造生命。正是每一个人在无数个当下时刻的真正个人化的感受与思考汇成了生命的长河,并至关重要地传达了生命的感觉和智慧如何形成的鲜活过程。所以只要表达清楚了当下的状态,那种被大而化之的传统手段所遮蔽的生活就会显露出激情与亮色,生命就会从“不在场”到“在场”,个体就会从“缺席”“遮蔽”“遗忘”到“出席”“呈现”“记忆”,个体的生命感觉就会得到充分还原。王晓明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注:“如果我们的目光一直专注于单向度时间结构的历史,许多的生存体验就可能被遗忘。”因此,《庭院》中的时间从本质上表现为人物的“心理时间”。
除此之外,经过处理的时间也是区分小说中有限世界与无限时空本质差别的一个关键词。小说的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我”对梦境的长久期待还是景兰的很快衰老,时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限度;而梦境中的时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无穷无尽的永恒,景兰的两个姐姐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永恒性才具有了既不懂事又老成,既有女孩子的声音却又人届中年的矛盾性质。因为处在短暂的时间中,所以人物才驱使自己的内在精神实践着向梦境世界逃遁的功能。景兰一贯以来神出鬼没的行踪就是最好证据。而梦境世界因为时间的永恒性,才能藉此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与确定性担负起人们一次次超越短暂现实,向理想国求索的权利。在这组时间的对比中,由节奏生成的一些因素与特点同样也构成了一种隐喻的功能;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意义传达。
具体而言,整篇小说的节奏生成是基于“我”对梦境访问前后的经历与内心的变化交替表述完成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也就是小说的前半部分,随着离梦境的越来越近,小说的叙述速度也由慢而快,并越来越快。一幕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件展开了:年复一年,“我”总想去一个梦想中的地方——庭院。了解“我”心事的景兰终于在某一天答应带“我”去那个地方。但兴奋的“我”直到半年之后才得以成行。景兰在把“我”带到他家后,在“我”懵懂之际将“我”推上了往梦境去的铁桥。“我”在这个通道上几经挣扎,总算随两个女人来到了梦境中的庭院。叙事节奏的加快显然暗示着主人公就要实现梦想的按捺不住的莫名兴奋。而从梦境的世界回到景兰家时,小说着力表现的是景兰家充斥的一种“紧迫感”。逐渐紧凑的叙述频率预示了从梦境世界回来的人们,其内心世界已不可能回归平静。精神的拷问机制已经开始毫不留情地对初受启蒙的“我”的心灵进行逼问。这种强大的力量正竭力将“我”纳入其中。而景兰则早巳身处其中。总之,对于所有到过庭院的人们而言,问题将永远高悬在他的头顶,他永远失去了思想意义上的自由自在。从此他的内心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平静,心弦只会越绷越紧,与看不见的敌人搏斗。而在梦境中的世界,这个原本让“我”殷切向往的美好所在,却是这样一个雨濛濛、灰暗的,嘈杂的世界,小说对“我”视线所及的画面的描述显示出一种因情感的陌生带来的凝滞感与沉重感。迷恋于此的景兰不仅衰老得很快,并且丢失了一条胳膊;“我”因为在其中受到一连串的刺激而感到“这是一个让人发狂的地方”,尤其是“我”莫名其妙地丧失了作为人类基本特征的外在形体时,“我”的失落与沮丧、不满与后悔更是以一种被强凋的近乎定格似的慎重与缓慢的速度释放,从而使“我”在梦境中的历练具有了浓重的悲剧意味。
帕克曾经在《美学原理》中说道:“每一种情绪(爱、恨、恐惧、忧郁和欢乐)都有一种具体的运动神经表现形式与之相适应。因此,有节奏的声音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这种联系的基础是一种共同的运动神经结构。节奏唤起运动神经‘装置——情绪的物质基础,使之立即活动起来,因而也就听见唤起相应的情绪本身。”小说中对应于不同世界所形成的节奏的疾徐与频率的疏密,实际表现的都是处于强大的理想世界与同样强大的现实世界间形成的矛盾、冲突中的主人公精神上所受到的撕扯与折磨的状况。无论是哪一个世界,对人都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难以避免的销蚀力量。这种矛盾与冲突带给人不祥的预感:人物走向的是虚无与幻灭。如同所有关于接近理想又对抗理想、逃避现实又回归现实的神话作品,《庭院》揭示的是一种人类身上永远存在并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由于人最终不能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的限度,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将以悖论终结。
《庭院》中存在的这种意义的张力,源自作品内在的诗性品格。当年新批评派理论家阿仑·退特首先将“张力”这个词从物理学领域引入文艺学领域并使用这个概念时,主要是针对语言的本义和隐喻义的同时并存,并且由于两者关系使得诗歌具有一种鲜明生动的品质而提出的。由此可知的是:《庭院》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本义之外的隐喻义,没有了隐喻义及其与本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力也就不复存在。残雪通过这种时空的隐喻,对身处复合时空集中的人们在现实世界所经受的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与精神诱惑的危险性,在精神世界中所经受的存在的痛苦煎熬,以及在两重世界中浮浮沉沉的挣扎中的人格与人性,进行了一场现代意义的思辩与勾勒。